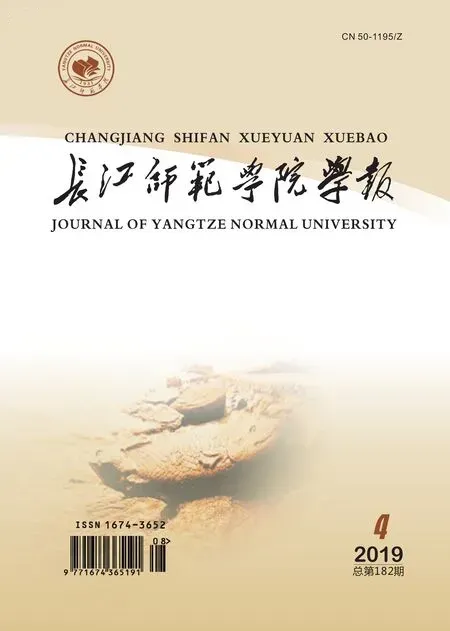哈尼族婚姻關系維系方式變遷
——以子雄下寨為例
張 宇,黃建生
(云南民族大學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昆明 650504)
云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綠春縣是哈尼族人口聚居大縣,截至2017年底,常住人口達23.46萬人,其中哈尼族人口21.48萬,占總人口的87.6%[1]。當地哈尼族有哈尼、哈歐、白宏、臘咪、期第、白那等多種自稱,其中以哈尼自稱的人數最多,子雄哈尼族屬于臘咪支系。哈尼族語言屬漢藏語系臧緬語族彝語支,分為哈雅、碧卡、豪白三個方言。哈雅方言中又有哈尼次方言和雅尼次方言,戈奎鄉子雄下寨流行哈雅方言中的哈尼次方言[2]。下寨距離子雄村委會7公里,轄區國土面積4.15平方公里,海拔1 100米,有耕地464.4畝,共有農戶114戶559人。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當地哈尼族在不同時期分別用婚姻成本、空間限制和婚姻模擬等方式來維持婚姻的穩定性。
一、當地哈尼族的婚姻特點
子雄下寨哈尼族婚配以一夫一妻的氏族外婚為主,近親之間極少結婚,目前村內僅有一戶人家是近親結婚。同姓內婚配至少須隔四代以上,同時嚴格遵守“血不倒流”的姑舅表優先婚。正如村民李某某(男,45歲)所言:“如果你是我的姐姐,那么我的兒子、女兒就不能和你的孩子在一起①在當地方言中,“在一起”的意思是“結婚”或者“婚配”。。”子雄下寨哈尼族中,離婚現象較少。據初步統計,目前村里共有114戶,離婚的只有5對夫婦,離婚率為4%。
在結婚儀式方面,當地哈尼族締結婚姻關系需舉行兩個儀式,即簡單儀式與復雜儀式[3]。所謂簡單儀式,指男方將女方領進家門時舉行的儀式,即女方開始在男方家長期居住時舉行的儀式,從內容和形式上類似于漢族的“定親”;復雜儀式是指男女在生育孩子之后舉行的正式婚禮儀式,等同于漢族的結婚儀式。不管婚配幾次,當地哈尼族男女終其一生只能舉行一次復雜儀式。
從儀式內容上看,簡單儀式主要是行磕頭禮,當地人稱為“wu du tong”。男方家先請莫批①“莫批”是哈尼族儀式專家,在儀式中用哈尼語所說的大意是:“兩人從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女方不能再任意回娘家,男方家要讓女方吃飽,男女雙方以后要相親相愛,同心同德,不能有異心。”選定一個良辰吉日,再邀請女方來到男方家中。當天男方家會宰殺一公一母兩只雞,待雞煮熟后便開始獻飯,由男方家母親端著竹篾桌,桌上放著鹽、花椒、酒、米飯、雞肉,面向家中墻上不同地方的兩個祖先祭臺②兩個祭臺分別是男方男主人與女主人各自的祖先祭臺。,男方和女方分別下跪磕頭兩次。磕頭后,家中最長者先吃竹篾上的米飯與雞肉,然后男方爸媽吃,最后再端到桌上大家一起吃。所謂復雜儀式,當地人稱為“lao bei ba de”,即“擺酒席”的意思,擺酒席是復雜儀式的核心內容。男女雙方分別在同一天宴請本族親人和本村村民,上午先在新娘家擺酒席,一對新人給在座的親朋好友磕頭行禮,男方將彩禮錢全數交給女方父親,意思是將女方“買”走,這時女方家長輩便開始哭泣,意思是自己養大的女兒從今往后再也不是自家的了;下午在男方家擺酒席,男女雙方從女方家去男方家的途中以及跨進男方家門時都要由莫批舉行一系列的儀式。在辦酒席期間,男女雙方的親朋好友不能互串,即男方親友不能去女方家做客,女方親友也不能去男方家做客。此外在擺酒席當天新人的子女是不能參加婚禮的,須被送至親友家照顧,并且不能吃酒席上的任何食物③哈尼族最初是不允許未婚先孕的,而現在的先育后婚是與最初傳統相悖的,所以為了盡大可能地還原未婚先孕的傳統,故而在新人結婚當天是不允許其子女出現的。。
從表征意義上來看,簡單儀式實際上是向家庭(包括已經離世的祖先)公布男女雙方確定戀愛關系的一個程序。通過儀式中的獻飯祭祖活動,告知祖先及家人男方已經將女方領進家門,女方今后可能成為這個家庭的媳婦。一方面,主人想借此祈禱祖先保佑兩人之間的關系穩定,希望他們能夠走到談婚論嫁的地步;另一方面,祈求祖先保佑整個家庭安康。復雜儀式主要是向社會(即整個村子甚至周圍村子的人)公開夫妻關系,同時將女人的魂引進家門,使女性的整體身心都正式歸屬夫家,自此以后女性必須自覺接受夫家的約束,兩人成為當地社會認可的正式夫妻。簡單儀式后兩人間的男女朋友(或戀愛)關系獲得了祖靈、家人、親朋好友和鄰里的認可,雙方父母將不再干預雙方的關系和行為。從此,女子開始公開居住在男友家,同男友家人共同生活。雖然簡單儀式后雙方開始同居,但在當地人的觀念中,這一階段仍屬于戀愛階段,兩人間的關系仍然充滿可變性,需靠雙方自覺維護。
在當地哈尼族的婚姻生活中,離婚的程序比結婚簡單得多。如果離婚由男方提出,則女方不用退還彩禮錢;如果離婚由女方提出,則女方需要退還雙倍彩禮錢。現代社會還存在財產分割問題。如果分家了,無論哪方提出離婚,男方家產均要被平分。此外,雙方都要選擇一個合適的日子進行“su la gu”(叫魂),離婚后女方的魂不能留在男方家,需要被叫回娘家;男方的魂也不能留在女方的身上,否則男方將會生病。在從簡單儀式到復雜儀式的期間,如女方未懷孕,男女雙方可根據自己的意愿選擇分開或繼續在一起生活;如果女方已經懷孕,但不超過3個月,女方可以選擇墮胎,男方一般不會干預;如果女方懷孕超過3個月,男方家一般會要求女方將孩子生下來,當然,如果女方執意不肯,男方亦不會過分強求。假如在從簡單儀式到復雜儀式的期間兩個年輕人生了不止一個孩子,那么女方選擇離開的時候可帶走其中一個孩子,其余歸男方家。
二、從“婚姻成本”到“空間限制”[4]
大致以20世紀70年代末為分界線,子雄下寨哈尼族的婚姻維系方式經歷了從“婚姻成本”向“空間限制”的轉變,這一轉變背后體現的是現代化進程影響之下當地社會環境和思想觀念的轉變。下文將以這兩個時期為例分別予以說明。
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締結的婚姻多為父母包辦,即由父母給孩子安排婚事,并不考慮孩子自身的意愿。有意思的是,這種包辦婚姻并沒有導致較高的離婚率。據當地老人說,在那個年代,村內離婚的只有3對夫婦,現在那些當事人都已經不在人世了。那時,當男孩差不多十五六歲的時候父母便開始為他們操辦婚事。男方父母會提前找人打聽哪家有合適的姑娘,對象多半是本寨或周邊寨子的。接著便請姑娘那邊的熟人上門說媒,該過程通常要進行3~4次,姑娘家才會答應。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一是對男方家庭進行一定的了解;二是將所有上門提親的人進行對比,選出最合女方父母心意的。然后雙方定親,由媒人出面商量結婚日期,男方要交付部分的彩禮錢。彩禮錢包括兩部分:一是用于將婚事定下來的禮錢;二是作為姑娘置辦嫁妝的部分錢財。到了婚禮前一天,新郎在“巴里”(舅舅)及媒人的陪同下來到新娘家,將剩余的彩禮錢交付完,這時女方家中的長輩便會“哭嫁”。第二天女方家殺豬擺酒席,飯后,媒人帶走一條豬腿,新娘在許多未婚姑娘的陪同下前往男方家。次日早晨,男方家擺酒席。酒席辦完后,新娘立刻就要回門。回門的時候,新娘只帶糯米粑粑回去,分發給跟她同姓的人。
老一輩離婚率很低,主要和家庭經濟有關。如今已70歲的張某說,他15歲左右就在家長的包辦下結了婚。女方家離他家大約七八里路,婚前雙方都沒見過面。村子里有不成文的規定,一旦建立婚姻關系,如果男人先提出離婚,那么女方家就不退還男方家送給的彩禮;如果女方先提出離婚,那么必須翻倍退還當初男方家送給的彩禮。由于他家的經濟狀況比較好,而他妻子家的經濟條件不是很好,所以,即便他毆打妻子,妻子也從不提出離婚。值得注意的是,老一輩人重男輕女觀念較為嚴重,他們認為,“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父母不會再管她們婚后的生活。在當時并不寬松的物質條件下,女方家愿意退還彩禮的并不多,甚至有些人家是將彩禮錢作為今后兒子娶媳婦用的。因此女方提出離婚的少之又少。雖然那時的婚姻都是包辦婚姻,但即便對女方不滿意,男方也很少提出離婚,原因是擔心損失彩禮。
當地通婚圈較小也是離婚率低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筆者調查的3對夫妻中,相互間最遠也只隔步行大半天的距離,其中有一對是本村的,有兩對是鄰村的。大家都沾親帶故,或者是朋友的子女,或者是遠房親戚的子女,再或者是托親戚朋友提親的。如果結合的新人鬧離婚,親友關系不免會受到影響。比如,李某(女,80歲)說,她很小的時候父母便給她包辦了婚姻,兩家算是有點親戚關系,婚后她與婆婆的關系不好,丈夫和她的脾氣也都很暴躁,經常吵架。當時雙方家庭條件一般,周圍又都是親戚朋友,離了婚雙方家人面子上都掛不住,后來家庭條件好了,兒子長大了,分了家,她就直接搬過去和二兒子住了。有時候,婚姻關系的維系也有出于對勞動力需求的考慮。1950年實行的土地改革廢除了土司制度,按家庭人口劃分土地。正如李某(男,41歲)所說,媳婦進了門就算自家人了,也會分到一份耕地。1958年后實行并社,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按工分分糧食,媳婦就成為家里掙工分的重要勞動力。
“廣義上的婚姻成本是指完成婚姻形式的過程中所付出的時間、情感、金錢、機會等一系列物質與精神的總和。通常所說的婚姻成本是指狹義的婚姻成本,指完成婚姻形式過程中所付出的經濟成本總和。”[5]從中可以看出,子雄下寨哈尼族這一時期的婚姻維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與狹義的婚姻成本相吻合。子雄下寨哈尼族建寨至今有近200年的歷史,地處山區,交通封閉,人員流動性小,農耕是唯一的生計方式。1958—1979年,在子雄下寨人們的生活特別困難,張某(男,55歲)回憶說:“那時候娶得晚的到處都是,家里沒錢啊,有的人40多歲才結婚。”由于婚姻關系是在父母包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婚姻關系的維系不僅是個人的事,還是兩個家庭之間的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認為:“婚姻是禮品交換最基本的一種形式,女人是最珍貴的禮物。以女人為禮品的結果遠比其他禮品交換意味深長,因為這樣建立起來的不僅僅是互惠關系,還有親屬關系。”[6]因此,在當時生產力低下、經濟落后的情況下,姻親關系能夠使大家互幫互助,共同渡過難關。而離婚會造成雙方(特別是女方)經濟上的損失,女方往往因為考慮要雙倍返還彩禮而不得不在婚姻關系中采取隱忍的態度,即便受到丈夫的虐待,也盡量不先提出離婚。而對于多數男方家庭而言,他們亦無力支付第二次娶妻的錢財,所以即便不喜歡女方,也會盡可能地將就著過一輩子。
1979年以后,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教育、醫療、交通等各方面開始得到較大的發展,人們的生活逐漸出現好轉,經濟因素在婚姻選擇中逐漸退居次要地位。村內開始出現自由戀愛現象,村民李某(男,45歲)說道:“那時候我們談戀愛都是在樹林子里。”在這一階段中,出現兩次儀式①這里的兩次儀式與1990年后的兩次儀式不同,主要原因是因為男方無力支付全額彩禮,或雙方或某一方無法直接湊齊婚宴所需的錢財,需要一段緩沖期,一旦錢的問題得到解決,第二次儀式便會提上日程。1990年后的兩次儀式主要是給予先婚后孕一定的“合法性”,兩次儀式的間隔在3~5年。現象,與此同時婚姻形式也由單一的包辦婚姻轉變為包辦婚姻與自由戀愛共存。在當地部分家庭,男孩不讀書后父母便會張羅給他們包辦第一次婚姻。村民張某(男,41歲)說道:“我的第一個媳婦是我爸介紹的,才半年就離婚了,已經辦過酒席了。后面娶的是自愿的,自己認識的。”如果老人主導的婚姻失敗了,那么他們將不再干涉孩子的第二段婚姻,讓他們自由戀愛。在這一輩中,離婚率也僅有4%。
這輩人離婚率低主要是因為文化教育水平低,人們的社會資本不足。對于女性而言,由于缺乏教育,她們的婚戀觀常常是在老一輩的教導下形成的,其中最為突出的思想便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故而在婚后多數女性存在認命的想法,即便老公出軌、家暴,兩人感情不和,只要沒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她們往往會選擇隱忍。就如村民張某(女,40歲)說道:“我老公在外面找了個女人,不過他不敢帶回家,村里人會說,嫁都嫁了,唉,就這樣過一天算一天吧。”由于文化水平低,她們沒有選擇的余地,只能退而求其次,守住現有的生活方式。郭某(女,45歲)說道:“我最遠也只到過綠春縣城。”村子里像郭某這樣的婦女占據了絕大部分。較低的文化教育水平讓她們沒有外出謀生的技能,沒有外出交談的語言能力,無法跨出這狹小的地域限制,只能以家庭為主,依靠家中的“一畝三分地”過活,從而家庭成為了她們的全部,故而她們不會輕易提出離婚。對于男性而言,由于高昂的生活成本和較低的職業技能,他們在外地只能從事最底層的抑或最基礎的活計,所賺取的錢遠遠不足以負擔其遠在外地的生活所需,例如買不起房、娶不起妻子、養不活孩子等。如張某(男,20歲),曾經有過一個妻子,妻子生孩子后就與他分手了。外出打工的時候他遇到過一個心動的女人,聽說女人是河南的,他直接就放棄了。他苦笑道:“他們那里彩禮錢要10萬元左右,我哪里拿得出來?”因而即便是成家也只會選擇在家鄉或家鄉周邊。費孝通曾說,有限的地理空間令人們處在熟人社會中,社會輿論對他們的影響特別大。在當地,婚姻是一件很神圣的事,一生只能締結一次,所以如果男女雙方離婚,就會受到當地人們的指指點點,也會對自己的下一段婚姻產生影響。李某(女,20歲)說,她前男友是結過婚的,由于他凡事都聽父母的,沒有主見,而父母又與兒媳關系不好,所以兩人離婚了。她不清楚情況才與他在一起,時間久了了解他的具體情況后,她也選擇了離開。不久該男子又找了一個附近村子的女人,結果對方父母一聽說男人的情況,當即不允許兩人交往。因此,男性選擇離婚的也很少。
綜上所述,社會資本的不足導致了社會空間的局限,間接促進了婚姻關系的穩定。福柯認為,空間不僅“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礎,也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7],他通過對權力關系的分析為空間生產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在當地,社會空間上的局限導致男性和女性的權利無法實現,這一“枷鎖”有效地維系了當地哈尼族男女之間的婚姻關系。
三、從“空間限制”到“婚姻模擬”
20世紀90年代以后,人們基本上都是先生育后結婚。在當地,雖然人們比較看重男孩,但并沒有嚴重的重男輕女思想,在他們的觀念中男孩可以傳宗接代,但姑娘更孝順。正如村民李某某(男,45歲)所說:“沒有兒子后面就沒有傳承了,家里有多少錢都沒人繼承,就成了別人的了。姑娘全部嫁出去了,自己的家都管不了,爸爸媽媽這邊更顧不上了,人老了,就沒有人能照顧我們了。平時姑娘對父母親要好一些,現在我的姑娘嫁出去了,每隔一兩個月她都會問我是否有酒錢。”因此,當地人在生了兒子之后,必須再生一個姑娘,認為這樣才叫做好事成雙,家里才會多祿多福,人生才圓滿。等到兒女雙全時,男女雙方才會舉行復雜儀式,正式締結夫妻關系。由于教育的普及,原先因資源不足導致的婚姻維系方式已然失效。農業的現代化減少了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因而有更多的人口開始流向城市。在筆者調查的子雄下寨,當地16~25歲適婚年齡的男性女性均在外務工。隨著男女平等觀念深入人心,許多偏遠少數民族地區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明顯的提升。她們越來越多地選擇外出務工,這樣的行為既增長了她們的見識,也擴寬了她們的接觸面;更多的女性開始選擇嫁到外地。根據擇偶梯度理論,女性擇偶是偏向比自己家庭條件優越的,而男性則相反,這樣就出現了“男高女低”的婚戀模式[8]。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鄉下女性嫁到城市,卻極少見鄉下男性娶城市中的女性。因此,農村女性開始大量外流,從而導致村子里適婚男性的人口數量多于適婚女性的現象。在男多女少的情況下,為了找到婚戀對象,男性青年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激烈的競爭態勢。女性不愁沒人嫁,男性卻愁沒人可娶。雖然1990年之后,年輕一代的婚姻跨越了地理上的界限,婚姻關系的復雜性遠遠超過了他們的前輩,但離婚率卻非常低。截至2018年8月底,筆者并沒有聽到有離婚的夫妻。根據訪談的20名適婚年齡的村民口述,筆者將離婚率低的原因歸納如下:
首先,從包辦婚姻向自由戀愛的轉變。2013年,當地二級公路修通,這徹底改變了村里與外界隔絕的局面。村里大部分男女最多讀到初中畢業便選擇外出務工,多數前往廣州或深圳的電子廠,在那里男女相互認識,然后談朋友,如果合適便將對方帶回家中,如果不合適便與對方分手。在自由戀愛的婚戀模式下,子雄下寨男女的結婚年齡普遍比老一輩大,思想心智更加成熟,更加有責任意識,這為他們日后的婚姻生活提供了一份保障。村內有一名21歲的男青年,他是在綠春縣城和女朋友認識的,相處了兩三個月后,他便隨女方去了廣州打工,可最終因為性格原因還是選擇了分手。對于另一個20歲的李姓小伙而言,雖然家里一直催婚,可他覺得自己年齡尚小,連立業都難,所以尚無成家打算。他說:“做事情要考慮方方面面,更何況這是婚姻大事。結婚后要有能力讓女方生活好,不然娶她干什么?”
其次,從先婚后孕到先生育后結婚的轉變。最初,在當地未婚先孕是極為丟臉的事,一旦發生,就要請莫批洗寨子。當天男女雙方牽著豬、狗繞寨子轉,未婚先孕的女性被村里的老人像敲狗一樣地打,經過這樣的事情后女性的聲譽嚴重受損,嫁人就必須選擇遠離村子的地方。正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說:“實際上,任何人類社會里,凡未經相宜的社會認可而要度過結婚生活的男女都要多多少少地受到苛罰。”[9]而如今未婚先孕卻成為了一種常態,如果女方被領進家門時已經懷孕則不用進行簡單儀式,如果沒有懷孕則要舉行簡單儀式。從簡單儀式到復雜儀式期間約有3~5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兩人會生活在一起,性關系也得到固定,直到生育兩個或多個孩子后才將復雜儀式提上日程。只有通過復雜儀式,男女雙方才算是真正的夫妻。被調查人白某(女,22歲)坦言道:“在我們這里如果沒有擺酒席,就算不得是夫妻,最多是我男朋友。”兩個儀式中間的時間段則是給男女相處磨合的時間。通過磨合能夠有效地降低婚后離婚的風險。李某(男,45歲)說:“村里的年輕人都是自己選擇婚姻,生了小娃娃以后才辦婚事,生了娃娃后的幾年里看看她的性格,這個家族能不能穩得住。如果早早地辦了喜事他們卻合不成,離婚就不好看了。有了兒子姑娘就很少會離婚了,那個時候才能穩定。沒生娃娃之前我們都不叫兒媳,而是把她當成朋友。”
最后是女性地位的提升。杜杉杉曾以“筷子成雙”理論來闡述拉祜族的性別平等模式,通過兩性合一來展現拉祜族社會中的男女平等。杜杉杉認為:“在一個男女平等的社會中,其主導意識形態、核心社會制度,以及主流生活實踐對兩性作出的價值評判是同等的,而且與性別角色無關。”[10]在筆者調查的子雄下寨,起初男女平等現象并不明顯,而后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男性競爭壓力的加劇,村內男女的相處模式也開始改變。他們開始給予女性更多的自主權,開始考慮女性的想法,開始為女性分擔勞務。村民白某(男,21歲)說道:“現在媳婦之所以難找了,是因為男女平等了,男人會做的事女人也會做,女人會做的事情男人也會做。”村子里打女人的現象基本沒有了。村民李某(男,21歲)說道:“我爸以前經常打我媽,我從來沒有打過我女朋友,打女人的男人不是男人。”張某(女,19歲)說,她爸爸以前也打女人,打跑了幾個,后來娶到她媽之后就沒再打過,并且早上最早起來喂豬、做飯,等東西都弄好了,她媽媽才起床。男女之間相處模式越發趨于平等。李某某(男,47歲)說,以前他只需要在山上犁田耙田,其余的事都歸他媳婦管。現在,他媳婦割谷子,他打谷子,最后兩人一起把谷子背回家;栽秧的時候,他搬秧苗,他媳婦插秧。而他的兒媳婦除了做家務基本不用干其他任何活計。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子女輩之所以婚姻關系穩定,最主要是與自由戀愛背景下的先生育后結婚習俗有關,與包辦婚姻相比,自由戀愛中的男女有更深的感情基礎。模擬是一種仿照的行為,由模擬的主體與客體構成。在子雄下寨,真正的婚姻是客體,先育后婚及簡單儀式是主體。在主體模擬客體的過程中,客體的文化內在與形式并不完全同質地再現,而是介于似與不似之間。先育后婚的習俗實則是在模擬婚姻生活,簡單儀式則是模擬婚姻中的結婚儀式,增強男女雙方生活的儀式感。正如霍米·巴巴所指出的,“殖民主義規劃了為自己的利益而必然實行模擬的策略;這個策略有自己的矛盾之處——它企圖讓被殖民者與殖民者又相同又不完全相同”[11]。在這里可以進行一定類比,復雜儀式處于強勢和具有約束性的地位,而簡單儀式則處于弱勢和協商性的地位,它模擬了婚姻儀式,與真正的婚姻具有相似性,讓男女雙方能提前經歷真正的婚后生活。在這種模擬的婚姻生活中他們“結婚”、生子,過著夫妻的生活,但又不具備婚后生活所有的因素。這種弱勢對強勢的模擬又是符合當下一代人的心理訴求的,即他們并不想過早地結婚,只是想提前感受一下婚姻生活,以便進一步了解雙方是否適合。其次,先生育后結婚的模式通過模擬婚姻建立了穩定的“家庭三角”。費孝通指出,丈夫、妻子、孩子,分別為三角的三個頂點,三者之間的關系組成了一個穩定的三角結構,而婚姻的意義就在于建立這社會結構中的基本三角,夫婦關系以親子關系為前提[12]。村民楊某某(男,41歲)坦言道:“一般生了孩子之后家庭就相對穩定了,我們吵架了,一想到孩子就不想離婚了。”最后,先育后婚的婚姻模擬也是規避無后的重要手段,在“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思想觀念影響下,男性之間的競爭越發激烈,而先生育后結婚便是在該觀念驅動下的產物。兩人磕頭行禮后只是確定了穩定的性關系,并不代表建立了穩定的婚姻關系。而在男多女少、競爭壓力大的年代,男性很有可能在分手后出現長時間找不到女人的現象。因此,先生孩子,即便今后兩人分開了,至少為傳宗接代提供了保障。當然,為了確保香火由男人傳下去,子雄下寨存在入贅的現象,如果家中只有姑娘沒有兒子,那么有一個姑娘便不會出嫁,而是將男性招上門。作為回報,老人過世之后,家中的財產便歸屬兩人所生的孩子,也就是說從孩子生下來后,男人才能被記入家譜。
四、結語
變遷是文化發展的永恒主題,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哈尼族社會生計方式的改變、教育水平的提升、國家政策的引導等各種因素,令當地婚姻關系的穩定性不斷遭受沖擊,而每一次的婚姻關系維系方式的變遷都對由沖擊而帶來的風險起到了一定的調節作用。
婚姻成本高是第一階段哈尼族人離婚率低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高昂的婚姻成本約束了人們的行為自主性,從而降低了婚后離婚率,間接使婚姻關系維持穩定;另一方面,高昂的婚姻成本限制了人們對自由戀愛的追求,違背了人的本性和意愿,為今后婚姻關系維系方式的變遷埋下了伏筆。社會空間的限制在某一段時期內的確對婚姻關系的維系起到了積極作用,將人們限制在一個熟人社會中,從而間接降低了離婚率;但從另一方面而言,與“婚姻成本”一樣,它們都是一種外在性的約束,一旦社會環境改變,該方法就會自然而然地失去效力。先生育后結婚的婚姻模擬,給予了男女雙方一定的選擇緩沖期,降低了離婚的風險。婚前落夫家有助于女方提前了解男方家庭,減少了在結婚之后所帶來的婚姻成本。相較于包辦婚姻,自由戀愛的男女雙方都比較注重自己的意愿,通過自由戀愛能夠增進男女雙方對彼此的了解,有利于結成性情相合、志趣相投的夫妻。然而,當地目前穩定婚姻關系的手段也可能引發新的問題,生育孩子后,如果孩子父母最后并未結婚,那么孩子將會在兒童時期缺失母親的照顧。眾所周知,孩子的健康成長離不開父母的共同陪伴。在這樣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其心理極有可能受到創傷,嚴重者離婚甚至會影響孩子今后的生活。離婚也會給男女雙方帶來一定的創傷,這些創傷既有身體的,也有心理的。當地哈尼族為適應當下的婚姻形勢而選擇的婚姻關系維系方式有其自身的優點,也存在著隱患,在將來的發展中必將經受時間的考驗,但可以預見的是,當地哈尼族深厚的文化積淀和生活智慧應當足夠讓他們面對未來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