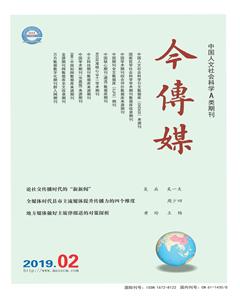從修辭學視角分析文章
楊路
摘要:本文從修辭學的角度,將知乎上回答“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這一提問的影響力最大的文章進行解構分析。主要著眼于對修辭學“五藝”中覓材取材、謀篇布局、文體風格的解讀,并結合三大訴求理論,圖爾明模式解讀文章的論證過程。發現文章傳達了這樣一種價值觀:崇尚和平、正義;愿意犧牲小我成全大我。
關鍵詞:修辭學;南京大屠殺;圖爾明模式;正義
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2-0149-04
一、 修辭學及其重要作用
修辭學Rhetoric,源于希臘語的Rhetor,意為說服。所以修辭學是一門關于有效說服的藝術[1]。西方修辭學的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紀。亞里士多德在《修辭學》中將修辭學定義為“在每一件事上發現可行的說服方式的能力”[2]。亞里士多德的理論經西塞羅和昆體良不斷完善,成就了“古典修辭學”。古典修辭學的主要貢獻一是確定了修辭的“說服”目的;二是建立了“說服”的理論體系。它包括:演講“五藝”說,三大修辭話語類型,三大訴求理論。由此可知,在后世的修辭研究中說服觀是主流觀點。
修辭學在19世紀末衰落,20世紀初開始復興并進入鼎盛時期,從這一階段開始稱為當代西方修辭學[3]。當代西方修辭學研究范圍不斷擴大,今天,修辭已經稱為一個無所不在的概念。正如拉里·羅森菲爾德所指出的“至今,我可以說,修辭現象這個概念涵蓋了浪潮之外的一切”。理查德·馬克肯回應說“浪潮又何嘗例外呢?”[4]這說明,修辭無處不在。因為范圍極廣,所以很難給當代的修辭學找出一個統一完整的概念。經過認真查詢對比,筆者贊同帕特里夏·比賽在1990年對修辭學的定義,總結為第一,修辭學關注語言編織的各種意義背后“人的動機”和對動機的“闡釋”;第二,修辭學的理論建構方式是基于知識產生于論辯之中的觀點;第三,修辭學關注的不再局限在對演講的理論建構,而是對社會行為的關注,即以語言為媒介研究社會問題[5]。
新媒體時代下,個人可以通過網絡以語言的方式對社會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其他人通過點贊、評論的方式對該觀點表示贊同,提出質疑或者反駁。如何組織語言讓自己的觀點更具說服力?通過以上對修辭學的文獻介紹,筆者認為修辭學可以提供諸多借鑒。
二、 《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的背景2016年12月13日第三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這一天,一篇題為《南京大屠殺跟我有什么關系?》的文章刷爆朋友圈,人民日報客戶端、新華社微信平臺相繼轉載。經了解,該文的作者是南京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2014級的學生周昱羽,當時周昱羽同學以“荒土”的網名在知乎上回答另一位網友提出的“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的提問,文章中以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寫作南京大屠殺相關紀實文學的經歷為例,引用魯迅的話語“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表達了作者的愛國熱情和青年人的社會責任,該文曾在“知乎”上被廣泛點贊并引起熱議[6]。
截止2018年12月1日,知乎上關于“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這一提問的回答已有2197個,但唯有周昱羽同學的回答刷爆朋友圈,獲得眾人贊同的同時也被媒體相繼轉載。為什么該回答能獲得大眾的贊同呢?為什么該回答能引發共鳴呢?(下文中的《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均指周昱羽同學的回答)
三、 解構《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
對《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文本的解構,主要著眼于對修辭學“五藝”(覓材取材、謀篇布局、文體風格、演講記憶和現場發揮)的分析,因該文本并非演講,所以這部分重點是對文本的分析,集中對前三部分進行解讀,不涉及演講記憶和現場發揮的解讀。此外還有對修辭學三大訴求理論(情感訴求、理性訴求、人品訴求)的分析。
(一)覓材取材:訴求理論分析
1.情感訴求
為了說服受眾,古典修辭學認為,人們可以通過三種訴求理論中的一種或幾種,覓取文本材料。情感訴求強調情感促發意志的作用,因為意志可以促動人們采取行動或者接受觀點。
首先,《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通過欲抑先揚的方式擴大結局的悲劇色彩,引發受眾的情感認同。文章中以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寫作南京大屠殺相關紀實文學的經歷為例,講述例子的時候并非平白直敘。一開始講述:“(她)很漂亮吧。她是個美國人,華裔。家庭美滿,婚姻幸福。” “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寫作碩士學位。她的第一本書《蠶絲——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廣受好評,贏得了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和平與國際合作計劃獎,前途一片光明。”向受眾塑造了一個幸福美滿,前途光明的精英作家形象。但她研究了南京大屠殺之后,“(她)氣得發抖、失眠噩夢、體重減輕、頭發掉落”“成書后,她又得面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報復和騷擾。她不斷接到威脅信件和電話”“后來她患上憂郁癥。2004年,她在自己的車中開槍自殺。時年36歲。”前后強烈對比,引發了受眾的情感刺激,這些情感包括同情、悲憤,此外還引發思考:她犧牲了自己大好前途去研究與自己“無關”的南京大屠殺,是真的“無關”嗎?從而為下文提出她所做的貢獻做鋪墊。在這里,文章將受眾帶進情感的體驗,讓受眾產生南京大屠殺與我們每個人有關這一情感認同。
其次,《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通過語言視覺修辭激發受眾的悲憤情感。語言視覺修辭指在語言傳播過程中,修辭者把生活中的視覺等形象轉換為語言文字符號,形成話語文本,傳播給受眾,受眾又通過大腦,心理還原為視覺等形象或者再現為實際的畫面。文章引用了四段《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中的原文,這四段文字極具視覺感,沖擊受眾的眼球,例如:“幾乎沒人知道,日本的士兵用刺刀挑起嬰兒,活活把他們扔進開水鍋里,”永富說,“他們結幫奸淫12歲到80歲的婦女,一旦她們不再能滿足他們的性要求,就把她們殺死。我砍過人頭,餓死過人,也燒死過人,還活埋過人,在我手下死去的人有200多。這真可怕,我簡直成了動物并干了那些無人性的事。實在難以用語言來描述我當時的暴行。我真是個魔鬼。”這一段語言文字成為圖像展示出來。悲憤、無奈、同情!眼見這種事發生在自己身邊,又怎能置身事外!南京大屠殺自然和“我”是有關的了。
2.理性訴求
人是有理性的,又不具有完全理性。所以除了用單純的情感打動人心,還需訴求于理性。用歷史事實來作為打動受眾的理性素材。文中列舉的日本軍人的惡劣行徑,有的有目擊證人,有的是士兵的親身經歷,有的是一手資料的記載……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張純如起初生活美滿,寫完《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后,不斷接到威脅信件和電話,后來她患上憂郁癥。2004年,她在自己的車中開槍自殺。作者結局凄慘是事實。日本政府至今沒有道歉,并修改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其參拜的靖國神社中供奉著侵華戰爭中的甲級戰犯。日本沒有悔意亦是事實!擺這些事實會讓受眾產生一種認同:日本做錯了事,“我”是受害者后代,做錯事的該為其行為付出代價。
3.人品訴求
人品訴求主要包括可激起信任和敬意的個人魅力,如人品、判斷力、善意等。亞里士多德認為,在三個訴求中人品訴求最為重要。在文章開始,作者就擺出了客觀的姿態。“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客觀上,沒關系!你是一個獨立的人,獨立的個體。沒有任何人有權力可以把你與這類歷史事件綁架在一起,你完全可以選擇不關注,并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是你的自由。”作者客觀的闡述觀點,這樣開門見山的激起了受眾的信任,并且可以看出其具有一定的判斷力。其次在文章結尾處,作者用了同樣的方式。“我也很喜歡日本文化、日本的動漫、日本的櫻花、日本的壽司、三四月份的北海道……但是對這樣一個國家,我始終抱有一股深深的恐懼。要說和我有什么關系?關系就是,我們這些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一代,現在站的這塊土地上,曾發生過一場大屠殺,迄今為止,只過去了短短的79年。”對日本有贊揚、有恐懼、有反思,表現了作者訴求感情的立體化,容易贏得信任。
(二) 謀篇布局
1.文章大體思路
謀篇布局指將覓取到的材料進行合理的分類和有序布置。開場白很關鍵,給受眾第一印象,也就是是否有讀下去的欲望。文章開始以客觀的姿態激起受眾的信任。在論證說理方面,運用了舉例論證,舉了張純如的例子,表達南京大屠殺看似與“我”無關,但總有人犧牲個人去承擔這一責任;運用了道理論證,“但是張純如選擇去研究這一段歷史,并且以這種方式呈現給世人,直至獻出自己年輕的生命。史學研究應有這樣的擔當。不光是史學,我覺得為人也當有這樣一份擔當。魯迅說過,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就是這般意思了。”用魯迅的話,通過說教的方式講一個道理:“為人當有這樣一份擔當”。增添了文章的說服力。運用了引用論證,大段引用《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中讓人悲憤的段落,且這些描述均來自一手資料,具有權威性,引發受眾情感共鳴,使論證更有力。結尾運用了隱喻這一修辭現象。隱喻具有勸說功能,伯克(Burke 1969a)認為隱喻是一種修辭勸說技巧。隱喻創造意義,改變思維,驅使人們去想像。文章結尾并沒有直接回答“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而是說日本很好,但是“我”很怕,“我”現在所站的地方,79年前發生過一場屠殺!這場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給受眾拋出一個具有想象力的推理。
2.運用圖爾明模式解讀論證過程
修辭學的論辯研究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及其省略形式,這種傳統模式影響了后來的研究。但是,亞里士多德的論辯模式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它強調純粹的形式推理,忽視了論辯參與雙方在論辯中的作用和結論的必然性。當代論辯修辭理論克服了形式邏輯推理中參與對象的單一性和結論的絕對性等缺點,尤其是圖爾明模式,因其展開性、人文性,被稱為論辯向非形式化、實用性、修辭學的認知轉變。圖爾明以綱要略圖的形式將論辯魚片簡化,使我們看清論辯的過程。他認為論辯是以事實(data)出發,通過理由(warrant)等活動(movement),達到主張(claim)的過程。事實、理由、主張三位一體,是論辯的必要部分。“主張”是論辯產生的一種明確的訴諸,是論證的結論。
如圖1所示,用圖爾明模式將《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這篇文章進行簡化。
圖1圖爾明模式該模式圍繞問題: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主要事實(data)貫穿文章主體,問題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事實的性質。筆者將其總結為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在南京屠殺30萬軍民,手段殘忍,且至今沒有道歉。主張(claim)有兩點,第一個主張在文章中間部分提出,借用魯迅的話“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道出:人當有這樣一份擔當,這里的“這樣”狹義指像張純如一樣,個人為了將歷史呈現給世人,不怕犧牲甚至不怕獻出自己的生命。廣義指個人為了民族大義,承擔相應的責任;第二個主張在文章的結尾處,但是表達的并不具體,而是運用隱喻的方式,在這里,筆者仍舊將其進行總結:我們現在站的這塊土地,曾發生過一場大屠殺,迄今為止,罪犯都沒有收到懲罰,我們有責任,去承擔這一歷史,讓做錯事的受到懲罰。兩個主張表達了作者同一個價值取向:崇尚和平、正義;愿意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為了佐證主張,文章列舉了大量史實。理由(warrant)代表了我們從事實出發到達主張的推理過程,而文章列舉的大量史實成為論辯最好的理由。因為對于過去成立的史實,極有可能現在和將來也是如此,這是一個歸納型的概括:日軍留下的屠殺證據眾多,浩瀚如云的史料和卷宗記載了這一事件,但日方至今仍未道歉。對于過去做的錯事,日方不承認不道歉,從歸納方法來講,日本極有可能現在和將來還會這樣做,所以日本文化雖美,但對這個國家,作者“我始終抱有一股深深的恐懼”。最后,修辭論辯是或然事件,其結果不是絕對的,正因如此反駁(refutation)才構成了論辯的必要組成部分。這使得論辯具有互動性。文章開頭就拋出: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客觀上,沒關系!反駁的理由從自由權利角度切入。“你是一個獨立的人,獨立的個體。沒有任何人有權利可以把你與此類歷史事件綁架在一起,你完全可以選擇不關注,并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是你的自由。”之后對反駁理由通過舉例的方式再次進行反駁,進而提出主張,使得論辯更為有力。
(三) 文體風格
修辭以語言文字愉悅靈魂。《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無論是在舉例還是價值觀表達,都很震撼人心,刺激受眾感官,引發共鳴。
文章采用多段落,短句子的形式。基本一句話就是一個段落,這樣的好處是便于閱讀,尤其是互聯網時代,受眾普遍用智能手機閱讀,大段大段相連的文字很難讓人有耐心讀完,而短句子,多段落彌補了這一缺點。
在詞匯運用上的細心突出體現在人稱代詞的選用上。這些人稱代詞有助于建立作者和讀者之間的特定關系。文中第一人稱使用13次,第二人稱4次,第三人稱48次,第三人稱復數16次。大量的使用第三人稱及第三人稱復數,目的是為了客觀性,不是第一人稱“我”在說教,第二人稱“你”在傾聽,而是用客觀的第三人稱說明事實,爭取受眾的信任感和責任感。
四、 結語
《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這篇文章在覓材取材、謀篇布局、文體風格方面都有其優點,但以修辭學理論解讀只是解讀其影響力最大的一個角度,還有其他角度可供研究。對于今后我們在知乎或者相關類似網站發表觀點提供了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1]柴改英,酈青.當代西方修辭批評研究[M].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12:56.
[2]Aristotle. Rhetoric. Trans. B. Jowett. New York: Random House,1954:24.
[3]陳汝東.新興修辭傳播學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2.
[4]Twentieth-Century Roots of Rhetorical Studies, edited by Jim A. Kuypers and Andrew King,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2001,p.1.
[5]Bizzell, Patricia. Bruce Herzberg. The Rhetorical Tradition: Reading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 Bedford Boods of St. Martins Press,1990:899.
[6]龔莉紅,李慕原.南財學子《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被轉載獲十萬多點擊量[N].中國江蘇網,2016-12-15.
[責任編輯: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