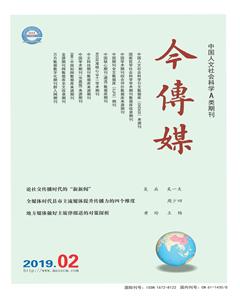“新藝術”運動對近代上海平面設計的影響
張曌玥
摘要:“新藝術”運動起源于法國,它就像是一陣颶風,幾乎席卷了歐洲大陸的各個國家,并滲透到了藝術設計的各個領域。同時,隨著它的快速蔓延,漂洋過海來到了擁有“東方巴黎”美譽的城市——上海。本文通過文獻閱讀和資料整合的方法,就近代上海平面設計領域深入探究“新藝術”運動所產生的具體影響。
關鍵詞:“新藝術”運動;上海;平面設計
中圖分類號:J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2-0153-03
一、引言
“新藝術”運動發生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它反對過度裝飾和工業產品的粗制爛造,提倡傳統手工藝。在思想上深受自然主義美學觀的影響,強調抽象的線條和有機的形態,其中蜿蜒的曲線、簡潔的直線和優雅的女人形象成為了此次運動重要的裝飾元素。而究其本質而言,“新藝術”運動并不單純是一種風格,或一種時尚,它是世紀之交的一次承上啟下的設計運動[1]。
二、影響上海近代平面設計的新藝術運動代表人物
1.阿爾豐斯·穆卡(Alphose Mucha,1860~1939)
阿爾豐斯·穆卡是法國“新藝術”運動中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穆卡的繪畫作品集中夸張地運用了曲線植物紋樣和典雅性感的女性形象作為主要的裝飾元素,畫面中避免采用任何的直線,色彩絢麗、色調溫和,主要用單線平涂的方法繪制。穆卡的設計風格輻射范圍之大,蔓延至歐美各個國家,也傳入了上海這座沿海城市。一些本土設計師靈活巧妙地將這個風格融入到月份牌的設計之中,呈現出了極具特色的中西文化交融后的裝飾樣式。
2.奧伯利·比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1872~1898)
奧伯利·比亞茲萊是“新藝術”運動中影響巨大的藝術家和插畫家之一,他擅長運用曲線及黑白構圖,對性方面的主題描寫更是十分大膽,其為《莎樂美》繪制的插畫出版后甚至遭到了英國政府的禁止。盡管如此,比亞茲萊仍然名聲大振,在 20 世紀初期隨著“新藝術”地擴展也一道傳入了上海。他的裝飾插畫有著曲折流動的線條、明快的黑白色塊、蜿蜒纏繞的植物紋樣,極富浪漫和神秘的氣息。這種風格受到了 20 世紀初上海一些藝術家、文學家、設計師的膜拜和模仿,并運用到了許多雜志和電影的廣告以及插畫設計中。
三、上海近代平面設計中的“新藝術”痕跡
(一)月份牌
自上海開埠以來,西方文明的擁入,商業活動的增加,促使了當時的廣告招貼藝術的板式設計的發展,歐洲的“新藝術”思潮也隨著其影響力的擴大逐漸傳入有“東方巴黎”美譽的上海城市。洋商為了宣傳商品,外國廠商聘請中國畫師設計的“月份牌”畫[1]。其中阿爾豐斯·穆卡風格對上海月份牌的影響較為顯著。兩者的內在基因里有著相似的表達形式——優雅嫵媚的女子形象占據畫面的中心,周圍裝飾上配有豐富多彩的花卉元素。這一共同點,也使得上海的設計師更為主動地借鑒其風格進行月份牌的創作。例如張獲寒為中國華成煙公司所繪制的畫作,左右對稱的裝飾形式,橢圓形的結構框架包裹畫面中心的摩登女子,上方配有兩只對稱的鶴作為裝飾元素,采用了線描平涂的方式,其造型上強調了曲線的動態,夸張的處理手法,加強了觀賞性,也充滿“新藝術”運動的裝飾特點。四周圍繞的紋樣則采用了蜿蜒的植物圖案,流動靈活的枝條纏繞交疊,這種抽象的線條和幾何的形態正是對阿爾豐斯·穆卡風格的借鑒。
(二)包裝設計
自上海開埠以來,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上升,人們對于產品包裝的設計需求也日益增加。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一個古典主義以及折中主義向現代過渡的轉折期,“新藝術”運動作對我國的包裝設計也產生了一定的吸引力。在上海茶葉公司的產品包裝中就能看到明顯的“新藝術”運動的影子,在設計上采用了大量的植物圖案與流暢的曲線[3]。植物裝飾采用左右對稱的構圖形式,在造型處理上仍具有寫實性。其中的裝飾紋樣來自于對自然的提煉。卷曲的曲線與明快的直線處理在畫面中的到了體現。對于標志兩旁的孔雀圖案,設計師采用卷草紋代替了其原本的尾部造型,呈現自然下垂的樣子,這使得孔雀的形象更為抽象、神秘、極富動態。
除此之外,月份牌招貼畫也經常被運用到包裝設計中。例如“華菲牌”女士香煙,從中可以看到設計師對穆卡風格的借鑒與參考。由珍珠與貝殼鑲嵌的圓形裝飾邊框將一位摩登女郎包裹其中,女郎的呈現出較為放松的姿態,但裝扮和眼神中又透露出一絲魅惑。在裝飾邊框的外圍還纏繞著許多流動的線條,這些線條是對植物的一種抽象化處理,也體現出了“新藝術”運動中的裝飾特征。
(三)裝幀設計
說到裝幀設計,不得不提的就是被稱為“東方比亞茲萊”的葉靈鳳,他早期的作品明顯受到亞茲萊的影響[4]。作為一名出色的小說家和裝幀藝術家,他曾在上海美專中學習西方繪畫技術,并通過《黃書》和《莎樂美》了解了那位紅極一時的英國插畫藝術家比亞茲萊。通過對比亞茲萊風格的模仿和借鑒,葉靈鳳的繪畫也充滿了“新藝術”運動的裝飾味道。
《靈鳳小說集》是上海現代書局于1931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這本書的封面就是由葉靈鳳本人親自設計繪制。在左圖的畫面中心是赤身裸體的夏娃,她的姿勢性感,表現出了強烈的肉欲感。叢生的植物與樹上的果實,將夏娃的身體遮掩了一部分,妖嬈的女體呈現忽隱忽現的效果,使得畫面更富有神秘的氣息,整體的繪畫風格采用了線描平涂的方式,靈動自然的線條透漏著相比亞茲萊的插畫風格,在配色上主要采用明度較高的紅、黃、綠等顏色,這也是葉靈鳳最常運用的色彩搭配,充分體現了他的個人特色。1925年由上海光華書局出版的《夢里的微笑》短篇小說集的封面也是葉靈鳳親自提筆設計,圖畫中體現了他對黑白繪畫的熟練運用,無論是對女子輪廓線條的處理,還是對紋樣的抽象化表現,在悠揚纏繞的曲線中都能看出他對比亞茲萊風格的提煉和吸收。
四、結語
隨著上海的開埠,萬國來滬的局面促使了近代工商業的飛速發展,這種開放的局面,使得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在上海這座城市中碰撞融合,并滲透到了上海近代化發展的進程中,促使了近代上海平面設計的大發展。這場設計運動沒有在中國引起進一步深度的探討,而只是作為一種裝飾風格被引進,但是它的創新思想對當時中國近代平面設計從傳統向現代過渡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參考文獻:
[1]王受之.世界現代設計史[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
[2]黃艷華.近代上海平面設計發展研究(1843-1949)[D].上海大學,2014.
[3]李培.建國以來上海食品包裝藝術設計發展歷程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16.
[4]凌夫,葉靈鳳.比亞茲萊的畫風[J].尋根,2011.
[責任編輯: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