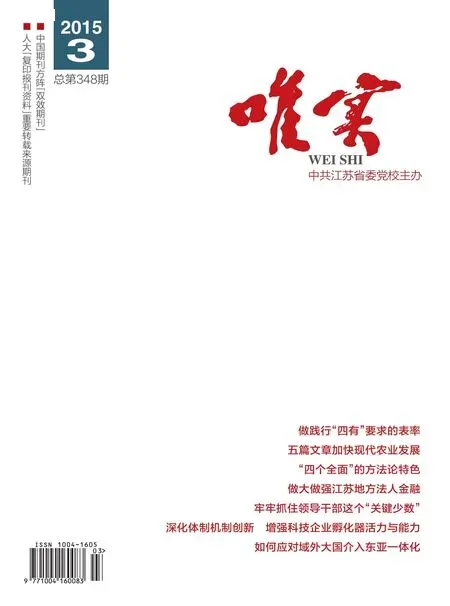長三角經濟近代化史上的政府角色
鄭 忠
一般來說,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常常會被理解為產業結構的優化,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近代化的過程中,造成這種產業結構優化的新的要素就是該地區城市的工業化。作為后西方走上現代化的國家,民族工業的發展,沒有國家和政府的強有力的支持是很難抵御西方資本主義的侵蝕的。這種支持不僅僅是對民族工業政策上的傾斜,還包括一些經濟上的扶持。缺乏政府強有力支持和保障,民族工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必然敗北。
自20世紀初,長江三角洲工商城市企業家力行“實業救國”,推動上海、無錫、常州、南通等城市工業化進程以來,區域內城鄉經濟不斷增長,上海成為東南亞地區重要的經濟中心,長三角及至全國的經濟中心城市,南通成長為“近代第一模范城”,無錫由常州府治下的人口規模僅5萬人的小縣城一躍成為蘇南地區的經濟中心,有“小上海”的美譽。然而,產生這種現象的因素更多的是依靠張謇、榮宗敬、榮德生、劉國鈞等民族企業家們發揮個人能力努力提高企業發展水平以及以上海為中心的自由商業市場發生著作用,政府作為協調主體的主導作用僅僅停留在口頭上的支持,具體落實到地方還得看地方官員的眼界和能力。
就晚清末期而言,當時清政府實行“新政”,采取鼓勵工商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兩江總督張之洞、劉坤一發揮個人能力對長三角民族工業給予了積極的倡導和幫助,對長江三角洲地區民族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并形成該地區工業發展的第一個高潮是起到積極推動作用的。然而,新政的推動僅僅開了個頭。畢竟喪失了獨立主權的中國政府面臨的是異常空前的政治危機,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無法有效地領導地方工業化運動了。因為面臨著西方列強的不斷打擊,它投降、逃亡、簽約、賠款、割地,不要說回應西方列強的挑釁,就連自身的財政收支平衡也要看地方督撫的臉色。如1909年,清廷原打算清理各省捐稅,停鑄地方貨幣,實行統一的中央財政預算制度,后因地方督撫的消極抵制不了了之。這樣一個權威喪失殆盡而又虛弱不堪的中央政府根本不可能為城市工業化提供強有力的支持,除了做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帶有良好愿望的計劃和許諾,基本無任何推動工業發展的實質性內容。
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能力也不待言。由于能力有限,統轄地方政府的官僚,基本上沒有盡多大努力去幫助民族工業與西方資本競爭高下。盡管他們中個別人對統轄地區的民族工業在態度上表示過支持,但在組織、管理、決策、資金支持等多方面似乎無動于衷,如近代統轄長江三角洲地區長達13年之久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才能平平,只會講求中庸之道,在其兩江總督任內,轄區內社會的發展沒有多大起色。然而官府對區域內民族工業的盤剝卻有增無減,如南通大生集團為了籌集必需的資金,不得不普遍實行“官利制度”,無論企業盈利否,官利股權一律每年付息8厘。這樣一來,大生背上了沉重的官方高利貸包袱,嚴重影響了企業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能力,成為后來大生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些地方官府對地區民族工業非但不予以支持,還變本加厲地加以破壞,如1890年蕪湖章維藩籌建益新面粉廠,蕪湖地方鄉紳以機器破壞風水為名堅決反對,廠址一再遷移,后來蕪湖道尹又以影響“本地礱坊生計”為由,反對從外國進口鋼磨。可以說,創辦民族工業如果沒有地方官支持的政治背景,就會寸步難行。
在長江三角洲城市化發展初期,官僚、買辦乃是投資工業的主力。如無錫創辦業勤紗廠的楊宗濂、楊宗瀚的背景是李鴻章,而且他們本身也曾是洋務派官員。創辦上海永泰四廠及無錫錦記絲廠的薛南溟,是薛福成的兒子,亦曾入過李鴻章幕,任天津道府三署法審委員專理華洋訟事。更不用說創辦大生紗廠的張謇,大生紗廠基本上就是在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的支持下,奏派張謇在南通創辦起來的。這些官僚和官辦之所以愿意冒險投資近代工業,除了他們具有開闊的視野和眼光,或認為投資工業是當時中國所必需,或看到投資工業能獲得優厚利潤,更重要的是他們與當時官府有緊密聯系,能獲得政治上、經濟上的支持。有些創業者本來不是官員,但為了克服投資實業時遇到的各種阻力,甚至通過捐納買得官衙。最典型的就是無錫的周舜卿和祝大椿等。因此,在近代長江三角洲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特別在20世紀20年代以前,不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盡管有一些支持城市工業化的政策和支持態度,個別官員甚至投資近代工業,但在領導整體區域工業化運動方面,還未能發揮其基本的職能和作用。

民國初年的北洋政府時期,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受中央和地方雙重作用的影響發生了新的變化。就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言,當時北洋政府任用張謇等一批具有改革創新精神的人士擔任政府經濟部門的首腦,出臺了一系列經濟法規和政治措施,如《公司條例》《礦業條例》和《注冊細則》等以法律形式保障了企業投資者的利益,明確和便利了公司呈請注冊和手續,減少了封建習俗勢力的勒索和阻撓,有利于興辦實業活動的展開,它主張商業自由經營,廢除了有利官紳開辦企業所取得的封建性排他權,使一般商人得以在各業從事各種事業活動。它倡導和推動銀行的大量興辦,促進了資本主義在金融業的發展,為工礦等實業融資提供了條件。這些政策和措施的實行,為這一時期推動中國經濟的近代化進程創造了一定的社會經濟環境,同樣也為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環境。因此,雖然當時政局動蕩不已,軍閥混戰不休,但長江三角洲地區近代城市工業還是保持著持續發展的勢頭。根據統計,截至戰后的1919年,在北洋政府工商部注冊的全國375家新建工廠中,江蘇省有155家,居全國各省之首位,浙江省有42家工廠,居各省的第二位。蘇浙兩省注冊工廠197家,占全國注冊工廠總數的52.53%。原來工業基礎較差的安徽省,在1914—1918年間也先后新建了60家工廠。然而由于北洋政府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依附于各帝國主義勢力,北洋政府不可避免地受到地主階級和帝國主義的掣肘。此外,軍閥之間為了爭奪政權和擴大勢力范圍,兵爭不息,形成長期混戰的局面。這些都阻礙了國家經濟政策的貫徹和落實。因此,對于北洋政府經濟政策促進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近代化的作用,也不宜過高估計。
這一狀況在城市近代工業化地方政府的資金層面和投入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地方財政環境方面,由于北洋政府時期軍閥割據混戰,軍費支出浩繁,而財政收入的主要稅源,或被地方軍閥截留,或作為抵償外債或賠款,收入所剩無幾,赤字連年上升,財政收入幾度枯竭,北洋政府為維持其統治,對外不惜用主權換取巨款外債,對內則對人民橫征暴斂,以債抵債,飲鴆止渴,形成財政的惡性循環。根據檔案資料,江蘇省在1914—1915年間,軍費開支達480萬元,而到十年之后的1924—1925年間軍費猛增到1800萬元。當時江蘇省的附加稅也多達105種,個別地方的附加稅超過正稅30倍以上。相形之下,工商投資更加無法保障,據《江蘇省財政報告書》資料,1912—1924年,在金陵道的財政支出項目中,農商費僅有10.93萬元,占總支出的2.49%,相比較而言,由市場主導的民間投資環境則為之一變,北洋政府新經濟政策與法規的推行,大大激發了資產階級投資建廠,振興實業的熱情,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迎來“黃金時代”,政府和市場的交互作用是相輔相成的原因。
顯然在近代長江三角洲的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晚清與民國兩任中央及地方政府在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發展進程中,都未發揮出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主導作用。其中,主要是市場、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在起著不可或缺的推動作用,而且僅僅停留在局部地區,比如張謇在協調發展南通地區的經濟發展方面就做過不少努力,有過獎勵墾牧、推進交通運輸發展等舉措。
政府的主體作用沒有很好發揮,遲滯了長三角地區經濟近代化的進程,這是長三角經濟近代化的一個十分深刻的教訓。
事實上,在百年后的今天,撇開政府的推動作用,僅僅依靠市場、企業和非政府組織,要想推進一個地區經濟的整體發展,也是根本無法實現的。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越來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政府承擔著區域發展的責任,掌握著政權的力量與行政資源,相對于市場它更具理性,相對于企業和中介組織更具有權威性,是運籌帷幄、掌握統籌兼顧權能的主體。因此,政府應該是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最主要協調主體。當然,政府決策具有人為的特征,存在著“政府失靈”問題,但是,這不妨礙政府居于區域協調三種主體中的中心地位,并發揮主導作用。
經濟發展常常被理解為產業結構的優化加上經濟的增長,于是從終極目標的角度來理解,經濟發展實質上就是一個問題的解決過程,實現這一過程的目的就是持續改善人們的生活條件或防止生活條件惡化。或者說,從結果的角度來理解,經濟發展就是社會成員自發的、動機明確的個體或集體努力的結果。因此,作者認為,政府在發動、促進與支持經濟發展、改善人們生活條件的過程中的主要任務包括以下幾方面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是為人們的區域經濟活動提供良性的環境保證,如法治環境、安全保障等,這在近代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中是無法做到的。第二個作用是提供公共產品,即那些為社會大眾所利用的不具有排他性的產品(如城鎮間道路)或排他性不能為社會所接受的產品等(如基礎性教育),這是南通張謇在南通工業化進程中試圖完善的方面,不過這本該是政府的職責。第三個作用是負責處理社會認為是必要的(如鐵路網)或對私人投資者而言缺乏短期獲利能力(如環境保護)而私人部門不可能介入的領域,但近代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決定了各屆政府同樣無法做到。第四個作用是解決或避免由于私人活動所引起的種種問題,如企業惡性競爭、資源過度利用以及環境嚴重污染等,近代上海、無錫等地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無序競爭等問題,而政府在這一方面卻基本上少有作為。
除了以上這四個方面的一般性作用以外,中央政府還需要從全國整體的全局的角度來考慮其對各個領域的影響,而地方政府則主要考慮如何提高轄區內經濟發展水平與人民生活水平。
不論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在面對區域經濟發展這一利國利民的發展大計的時候,都應該從全國經濟發展的整體利益出發,從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發展目標出發,做好各區域經濟發展的協調與保障工作,既有政府的推進,又有市場的整合,還有企業和非政府的中介組織的努力,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將一個地區的經濟提高到較高的發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