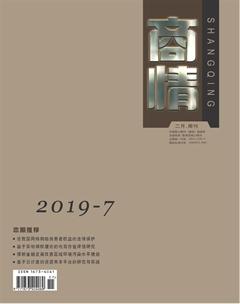中國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構建狀況研究
王敏超
【摘要】工資是衡量勞動力價格的指標,工資分配合不合理,會直接影響到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從而提高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降低企業的利潤和行業競爭力,如何制定工人的工資,成為了每一個雇主需要重視的問題,有的企業會調研當地同類企業工資的情況,有的企業會采取工作分析的方式確定職位工資標準,在這里,筆者要探討的是當前中國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發展現狀及其完善措施。
【關鍵詞】集體談判;工資制定;完善措施
對于在勞動關系中處于弱勢的勞動者來說,集體協商制度能讓他們和企業或是工廠的老板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作為維護勞動者權益的有效途徑,該項制度在國外被廣為應用,尤其是以工會力量之強聞名的美國,幾乎所有的工廠和企業都會設立集體協商制度來探討運營上的大事小事或是與員工利益相關的事情。而筆者今天要探討的是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該項制度的出現一方面能保證基層員工的基本利益,讓員工能共享企業的發展成果,另一方面,如果不讓員工和企業高層能實時溝通,領導不知道基層工人的想法,必然會影響和諧穩定勞動關系的構建,換句話說,構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能提高企業的凝聚力,同時調動所有職工的積極性。
在西方經濟學與工資決定和形成機制相關的理論中,“工資”問題一直是學界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同時也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熱門問題。早期對工資決定因素的研究有亞當·斯密的勞動工資理論、魁奈的生存費用理論、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工資基金理論、約翰·克拉克的邊際生產率工資理論,而約翰·克拉克的邊際生產率工資理論系統地講述了工資的決定因素,也對學界對于相關問題的研究影響最大。隨著之后工會逐漸發揮著自己的力量,學者們開始關注市場影響工資的力量,以集體談判為背景的工資理論產生了,1990年,合作議價理論出現在工資研究的領域,它為轉軌時期的工資和就業決定研究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這些研究在工資水平決定的影響因素上水平頗深。比如有的理論提出,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有工資高低這一決定因素。在讓企業接受來自工人的工資集體協商談判上,這些會成為我們的助力。
在中國,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也并不深入,1999年,楊先明學者在《勞動力市場運行研究》一書中闡明,中國的工資制度最早是計劃體制,國家決定工資,當時全行業的員工都分等級,比如三級木工,四級零售員,他們的工資由自己的職業等級決定,隨著時代變遷,傳統落后的工資制度逐漸演變成工資機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二元工資制度和工資機制。現行市場經濟體制下,準市場化工資形成機制與市場化工資形成機制并存國有企業是在工資總額控制框架下的工資分配自主,市場在工資水平的決定力量不強。當然,部分小型國企和民營企業的工資是有市場完全決定的。同時,學界有學者對集體談判制度進行了相當系統的研究,將西方的集體談判制度互相比較,學者們發現,這些制度有兩個特點,在價值取向上,由于工會之引導,取向多元化;此外,由于對罷工權立法導致罷工法定化,而這些與我國現有制度是不符合的,所以,中國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在構建上不能參照國外的體制機制,應當結合我國國情和相關法律進行深入研究。
一、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撐
中國實行集體協商制度立法是一項新的工作,也是建立社會主市場經濟過程中保持和諧穩定勞動關系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因此,需要在法的高度上明確集體談判的地位和在工作中注意發揮集體協商的法律效力。雖然我國近年來在集體協商立法上動作頻發,但是集體合同制度的推行將立法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不斷地暴露出來,例如:規章的立法存在漏洞,法律的權威性缺失。比如《勞動法》第33條指出:“工會可以代表職工與企業簽訂集體合同”,這里用的詞是“可以”而不是“必須”,這種給了企業主選擇權的規定反而在《勞動法》施行后成為集體協商談判制度推行的阻力,完全沒能幫忙推動集體協商在中國的普及。而之后的《工會法》顯然想到了這一問題,在修改中,將原本法條中的“可以”修改為“工會代表職工與企業簽訂集體合同”,似乎與之前的法規相比確有進步,但是表達上的模糊含混,讓集體協商制度在實踐中漏洞頻出。
沒有明確集體協商和簽訂集體合同的責任。《勞動法》、《集體合同規定》中都沒有明確規定法律制度的責任。雖然規定了企業在收到集體協商要求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但并未明確何種理由為正當或不正當,更未規定拒絕協商的法律責任,以至于一些企業以此為借口,拒不簽訂工資集體協議,特別是一些跨國公司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更難。以上立法現狀,造成一些企業中特別是一些非國有企業中的職工代表和工會成員不能充分發揮代表和維護職工利益的作用,直接影響了集體協商和集體合l司制度的實行。
二、企業對工資集體協商機制認識不夠
這里的企業分為兩種,一種是完全不知道有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存在的,一種是知道該機制存在,但是對這個制度理解不夠從而做出抵制行為的。先說說第一種企業,筆者前段時間對一家企業的總經理做過訪談,該企業屬于飲食業,企業人數規模在50人左右,并沒有成立工會。該企業的薪酬制定標準是參照市場定價,銷售等業務人員工資由大比例的績效薪酬和小部分的基礎工資組成,其他行政人員工資由小部分獎金和大比例的基礎工資構成,可以看到,該企業在制定工資標準是并沒有采用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在對該企業的員工工資滿意度調查中,筆者發現,員工的滿意度并不低,每名員工的工資標準都根據自身的工作類型有所不同,而且該企業采取的工資標準是領先于市場的。在之后的訪談過程中,筆者向訪談對象介紹了工資集體協商機制,但該經理認為,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加重了企業的負擔,無論是組織成立工會,還是進行集體談判,反而以市場勞動力定價作為參考反而輕松有效率的多。
而對于了解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存在的企業來說,他們不認可的原因也有很多。首先,民營企業的老板一直對工會以及工會執行的派生措施持抵觸情緒,他們認為工會的存在會影響到企業的運營,而集體協商機制的出現會讓工人們分走本屬于自己的一杯羹,集體協商會減少他們的利潤是他們的抵觸原因之一;其次,生產活動是企業經營的主要手段,很多企業主認為,企業要生存,要擴大再生產,努力接訂單,提升技術,擴大市場,努力生產,這么多的事情需要處理,又何來時間和精力去做什么所謂的集體協商,甚至還要簽訂合同;最后,有些企業主認為集體合同是“雞肋”,對于那些賺錢多,經濟效益好的大企業,他們根本都不用簽集體合同,給工人漲工資就能解決雙方的矛盾,而對于那些經濟效益下滑,生產經營可能有風險的企業來說,企業主擔心簽了集體合同會很難兌現,不簽合同反而會讓自己沒有任何經營負擔,減少自己的麻煩。筆者在這里所說的一切,其實都是企業主對于集體協商機制的態度和認識,他們對機制的畏懼,抵觸和避之而不及成為集體協商機制在中國推進的最大障礙。
三、工會和員工對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的不理解
從工會方面看,存在的問題也不少。很多工會干部認為,現在還不是開展集體協商談判制度的時機,并且開展條件也不成熟,現如今企業都有定期召開的職工代表大會,干部群眾懇談會以及其他各種暢通的民主渠道來讓領導職工關系融洽,是否有必要人為的制造對立面,值得商榷。還有的認為,工資協商應由勞動部門管,工會不應插手,同時擔心與經營者談判工資容易產生對立,以后工作不好做。還存在這樣一種情況,一些工會干部一方面為了保住飯碗,不敢或不能理直氣壯地推動工會工作,而是看老板臉色行事;還擔心協商結果達不到職工要求,職工會不滿意,因此對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存在畏難情緒。
在勞動者方面,主要問題是參與性不高,自我保護意識不強。很多工人認為集體協商協議是花架子,大家只是走走過場,搞搞形式,工資該由誰決定還是由誰決定。還有的勞動者對自己的勞方力量不自信,現如今的勞動力用工上,企業處于主導地位,在大批廉價農村勞動涌入城市,大量下崗職工等待就業的情況下,能有一份工作就不錯了,將工人組織起來派代表與廠長、經理協商,簡直是天方夜譚。也正是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勞動者大多對侵害自身合法權益的現象聽之任之,很少有勞動者會想著去自我維權或是找勞動部門維權。
四、結論
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出現能夠有效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企業的運營發展,有效化解勞資矛盾,構建和諧勞動關系,該制度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施行該項制度能夠逐步規范我國的勞動力市場,讓勞動力合理流動。隨著工資集體協商主體的逐步凸現和社會政治條件的日漸成熟,工資集體協商在我國有了初步的發展。但是,我國的市場經濟體系正在不斷完善,勞動力市場不健全,工會的性質、職能不盡人意,協商主體力量不均衡,統一的勞動力供求信息系統仍未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模式還處于摸索當中。所以,應當盡快完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的立法,不斷孵化和發展多層次的工資集體協商主體,普及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在其中發揮政府的調控職能。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勞動力市場化的不斷提高、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政治環境的不斷開放,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必將成為我國企業工資決定的主要模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