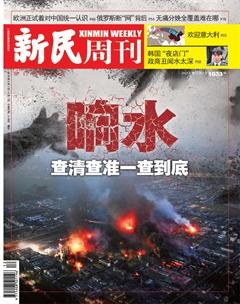葉永青藝術事件聯想
中國當代藝術家葉永青先生被比利時藝術家指控抄襲,當這一則指控聲明透過媒體傳出,再經由社交媒體不停地加料助寫與散播之后,所引發的關注和人們討論的風向等等,都讓我有了不同的角度看這個因為網絡而改變的世界。
我深有感觸的是在社交媒體指責高過于討論的網媒特質,正反映著這個時代對于新聞閱讀和理解能力的檢驗。
這則抄襲指控聲明充滿了引誘社交媒體人有瓜可吃的重要元素,例如:先指出后者的畫價高漲對比前者的畫作一直處于冷門與低價,透過金錢的比較往往是最容易吸引關注的手法之一;也表述因為藝術家在二手市場拍出高價成績,造成后者對于前者擁有強權。無論這則聲明是來自藝術家的口述或委托媒體所寫,其實也是有相當程度反映了勢弱者,在表象之下對于中國當代藝術圈的解讀,而這樣解讀基本上也算是誠實的。
當下的藝術圈以銷售為王,作品價格多少代表一個創作者與其經營者的bargain power和影響力,順勢在這網絡造就平滑無界的世界里,最終,藝術價格成為其他慕名而來的許多采買藝術品人群的一個指標,如網上小潮牌般,“成交數據與網紅流量”變成唯一標準參考。在我們所見的藝術媒體社交平臺上,似乎驚人的數據才是名氣的代表,而作品本身的內在和時代對照之關系,這種費勁的討論似乎已經少有人有興趣了。“以流量換算金錢”這套商業標準放在如今的藝術上似乎也很少有人懷疑,這不單是因為數字興起所造成新的價值評估方法,更重要的原因是,近年來藝術收藏者眾,有更多收藏是因為慕名而投資。
君不見年年都有幾大收藏家之排名,都是以這一年來之交易數據和造就社交平臺流量為標準,錢與流量已經是權力共生。自然而然,這些高金額造就出來的大收藏家們,幾乎都聚焦于拍賣會所制造出來的明星藝術家,因為他們一件作品就可以抵上一個不熱門的藝術家千萬件價格。特別是在全世界的當代藝術里,有許多精于社交媒體運作、并與拍賣公司合作的大型畫廊,形成一個不用看清藝術內在的藝術世界。回到這個新聞事件里,如果葉永青先生的作品依舊默默無名,是否這樣的指控就顯得軟弱無力,不會引人議論?
抄襲與否更多時候需要對照時代背景,和兩位藝術家整個創作對比方可斷定;這種對照需要更多學術界客觀的觀察和討論,不應該先設結論再來討論,也可能不是只有一個結論。只是事發至今從社交媒體的角度來說,我看到更多的謾罵與指責、要求道歉等等叫囂,幾乎淹沒一切、幾乎沒有太多討論和辯述的空間,這正是這個時代特有的狀態。社交平臺如同一只容易饑渴的野獸,只要有任何值得引起群眾關注的新聞,更多時候人們不署名地留下各種聲討與謾罵,這樣的案例在娛樂圈更是盛行。然而,所有的指責與謾罵其最終目的能促成什么呢?人們似乎都有權當審判者,審判別人似乎是一種能得到一時生物性宣泄暢快的行為,但往往也會混淆視聽、阻礙了求真相的可能。
最后,我還是要說,藝術的進展里面,臨摹與抄襲應該是兩回事,抄襲最不恰當之處是,沒有把這創意之榮耀明白地表述出來而占為己有,這是絕對不恰當的事。我之所以提出這個討論,從另外一個角度是讓藝術圈正視抄襲,但是也要客觀了解:在時代進展經過臨摹而進步的真實存在。當然,當代藝術之模仿與抄襲已經是一件泛濫的事了,借由眾人的關注,的確對于藝術圈的健康是有幫助的,這點也必須歸功于社交媒體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