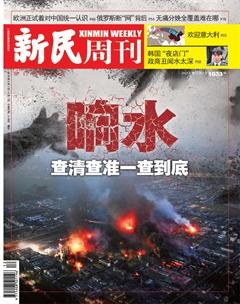尊重自然規(guī)律還是膜拜自然本身
前些年,聽“大煉鋼鐵”的故事,我一度以為大凡山上光禿禿,一定是“大煉鋼鐵”的后遺癥,后來才知道情況并非如此。例如武漢市內(nèi)有一些小山,現(xiàn)在都是林木蔥蘢,但看舊照片,無論上世紀(jì)三十年代的東湖、珞珈山,還是五十年代初的龜山蛇山,都樹木稀疏,那時(shí)并沒有“鋼鐵元帥升帳”。
去年參觀井岡山黃洋界,已不可見當(dāng)年哨口雄險(xiǎn)之狀,現(xiàn)在黃洋界樹高參天,不見豁口,而黃洋界保衛(wèi)戰(zhàn)時(shí),正是因?yàn)闃渖倭窒。诺靡砸谎弁h,滾石可退敵,那小炮也才打得出去。
上面說的都是對(duì)于較近的歷史的認(rèn)知。按說,較近的歷史,應(yīng)該看得更清楚。但有些事情,正因?yàn)槿r(shí)不遠(yuǎn),就復(fù)雜起來,不全是歷史認(rèn)識(shí),不全是社會(huì)認(rèn)識(shí),而是社會(huì)認(rèn)識(shí)與歷史認(rèn)識(shí)的夾雜,缺的往往不是資料,而是看待事實(shí)的客觀態(tài)度或者說社會(huì)認(rèn)知的共識(shí),情感、好惡、一時(shí)之論等成分較重,認(rèn)識(shí)先驗(yàn)地被某種刻板印象框定。
這些天,武漢在長江漢江邊拆除清理一些碼頭,一些一百多年的碼頭就此告別,長江大保護(hù),在見真章。但事情并不是孤立的,就像第三個(gè)饅頭吃飽了肚子,不是前面兩個(gè)饅頭浪費(fèi)了。雖然今天這樣做,也要破除利益壁壘,但根本來說,今天城市過江橋隧暢通,長途客船早已不是交通方式,貨運(yùn)已升級(jí)為集裝箱運(yùn)輸,這才可以拆除老舊碼頭,過去這些碼頭的存在卻不是沒道理的,人們畢竟要向自然討要生活,靠水吃水就是一種必然的選擇,而不是說那時(shí)人們就是要破壞環(huán)境,而是發(fā)展還處在需要向環(huán)境索取,而且尚在環(huán)境承載力之內(nèi)。
如同“大煉鋼鐵”,你可以說它不科學(xué),但不能無視人們?yōu)榻鉀Q“工業(yè)糧食”問題而百般設(shè)法的焦慮之情、無奈之情,今天“去產(chǎn)能”的時(shí)代背景與當(dāng)時(shí)不可同日而語。人們確曾改天換地,不只是進(jìn)行政治和社會(huì)的改換,而且延伸到對(duì)改變自然天地抱以巨大的熱情,因而有不少環(huán)境破壞的事情。重新安排山河的行動(dòng)中,固然有圍湖造田,有河水上山,有土地沙化,有大砍大伐,但其中也有不少是求生存的壯舉。河南林縣的紅旗渠,山西昔陽的大寨梯田,不是一句“不尊重自然”可以定性。
尊重自然,是尊重自然規(guī)律,還是尊重自然狀態(tài)本身,這可能也是個(gè)問題。如果說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然本身,認(rèn)為自然有“主體性”,原生態(tài)有至上性,那么人類一誕生就必須有目的地對(duì)自然加以改變,那人類就要像極端者所說的那樣被視為“一種疾病”。能夠說得起“人類就是自然的一種疾病”,那也一定是人類已經(jīng)活得相當(dāng)牢靠以后才可以。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一定是在人已不再會(huì)出門就遇到猛獸的時(shí)候才行得通。
尊重自然不應(yīng)當(dāng)是尊重自然的本然狀態(tài),而是尊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規(guī)律,尊重人與自然的永續(xù)發(fā)展。人只能從自然獲得生存,你得播種、采礦、生產(chǎn)、建起村莊和城市,才能活下去。倘若人一開始就奉行自然至上,只把自己當(dāng)成自然環(huán)境的一分子而不是從自然界掙脫出來,人類就還在與猛獸拼體力,而不會(huì)有強(qiáng)大的文明依托,使他沒有本錢可以產(chǎn)生“生物多樣性”“生態(tài)友好”等想法。
把事情放在歷史中去理解,而不是放在穩(wěn)穩(wěn)吃到“第三個(gè)饅頭”的現(xiàn)實(shí)中去苛責(zé),既是對(duì)歷史以及歷史中的人的同情,也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一種準(zhǔn)確認(rèn)知。
自然和生態(tài)的主題浮現(xiàn)出來,不是證明發(fā)展史的錯(cuò)誤,而是證明發(fā)展過程的升華。以今日苛求昨日,與發(fā)達(dá)國家要求后發(fā)國家放棄發(fā)展權(quán)而達(dá)成其認(rèn)為理想的氣候公約,只不過前者是否定自己的歷史,后者是剝奪他人的權(quán)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