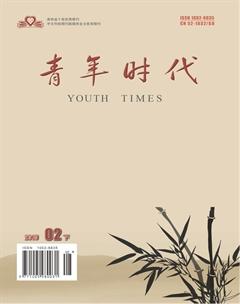全景敞視與“規訓社會”
羅家枝
摘 要:由對刑罰變遷的解剖來探究權力運行和變更的軌跡,并以此展示權力實現方式由顯性向隱性轉變的過程是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的重要創造。福柯指出全景敞視建筑的發明是權力——技術學的創造,權力運用全景敞視的機制,使懲罰趨于“合理性”,在理想的能見度中使置身其中之人變得靈巧、配合和服從。當社會建立起一整套規訓體系,對權力運行方式的轉變開辟了一個“懲罰的自我節制的新時代”,而在福柯看來,這只是權力運作技術的高明之處而非社會性質的實質之變。
關鍵詞:全景敞視主義;規訓社會;權力-技術學
一、取消酷刑——肉體的解放
福柯權力技術學的高明之處在于:認識到刑罰并不是減少犯罪的最佳手段,也不應以追究責任為最終任務,刑罰有其積極層面的內容,即關注罪犯的更好發展。在18世紀晚期,西方社會存在三種并存的權力形式,“君主時代作為公共景觀的酷刑;啟蒙思想家和法律改革家提出的注重法律程序和人性化的懲罰;監獄監禁和教養。”酷刑作為公共景觀淡出民眾的視野,在歐洲歷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標志作用。在《規訓與懲罰》的開篇,達米安——企圖謀刺國王者,應“乘坐囚車,身穿囚衣,用燒紅的鐵鉗撕開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燒焦他持著弒君兇器的右手,然后四馬分肢,最后焚尸揚灰。”這是一場類似屠宰的酷刑場面,正是君主至高無上權力的彰顯。人類在19世紀之前,國家法律對囚犯施以酷刑和儀式化的處決,以顯示囚犯確有罪行,以此證明君主權力的至高無上和不可侵犯性。但諸如肢解、車裂等血腥的酷刑及其殘暴的處決方式,在展示統治者權力神圣的同時,也在參觀展示的民眾心中煽動了強烈的仇恨和不安情緒,使處決一類的場所演變為“非法活動的中心”,誘使打架斗毆,酗酒鬧事等暴力事件頻頻發生。
在這場劊子手、罪犯、民眾的博弈中,其實質是君主權力的顯露。公開懲處有其獨特的政治作用,但其內里同樣潛伏著巨大的不安因子:公開景觀式的懲罰,一方面展示了君主權力的不可侵犯性;另一方面,在這種刑罰執行過程中,劊子手復制和再現了犯罪過程,并力圖將更多的痛苦施加于犯罪者的肉體。犯罪者的哀嚎和懺悔以及在施刑過程中的痛苦模樣和寧死不屈的頑強精神,甚至會引起一部分民眾的同情、憐憫和欽佩等情緒。此時,正義和非正義的角色被顛倒,罪犯變成英雄,施刑者則變得面目可憎,而這顯然是上層統治者所最不愿看到的情形。酷刑作為公共景觀在歐洲歷史上存留了很長一段時間,并隨著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興起逐步宣告終結。但作為公共景觀的酷刑的終結,并非由于觀者對酷刑所提供的視覺體驗失去觀賞興趣,而在于人類的理性進步逐漸難以容忍這些盛大而殘酷的懲罰儀式。19世紀中期,歐洲刑罰還未完全摒棄對肉體的擺布,只不過此時肉體已不再是制造罪犯痛苦的載體,其主要目的是剝奪由肉體所產生的財富或權利。究其實質,這一轉變是刑罰對象由犯人的肉體轉向靈魂的一種手段,是權力對肉體另一種形式的隱秘征服。
二、全景敞視——懲罰的“人道主義”
相對于公開景觀式的酷刑,全景敞視建筑的發明是規訓權力由公開變為隱秘的轉折點,它通過建筑設計的巧妙,來表達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通過高效率的空間組織,部分的實現對其肉體的規訓。在這里,高聳的瞭望塔是整個“透明監獄”的中心;在這里,監督者(總管)居高臨下、暗中俯視和觀察著一切被監督者,而任何一個人都有權利來進入瞭望塔的頂層,監視所有人的一舉一動,這使得每個人彼此之間關系透明。從監督者的角度看,嚴密的監督被一種可以計算和監視的繁復狀態所取代;從被囚禁者的角度看,嚴苛的酷刑被一種被隔絕和被觀察的孤立狀態所取代。在這里,權力的行使不再以沉重鐐銬和殘酷刑罰為標志,而是以一種在監禁者身上的有意識的、可持續的監督狀態取而代之。“擠作一團的的人群、多重交流的場所、混在一起的個性、集體效應被消除了,被一種隔離的個性所取代。”由于被監督者的有意識和監督狀態的持續性,使得權力可以自動的發揮作用,這無疑是權力運作天才般的發明!
全景敞視主義是一種使權力自動化和非個性化的重要的機制,權力不再體現在某個人身上,而是體現在對于肉體、表面、光線、目光的某種統一分配上,體現在一種安排上。“懲罰被一種看似更加溫和、可接受的方式取而代之,資產階級將現代社會控制方式演化成為一種支配的藝術,而這種隱性奴役的本質就是規訓,即形成以一種自覺被遵守的紀律為生存原則的自拘性。”在這里,被大肆鼓吹和贊揚的統治權力開始變得悄無聲息,在這種設計巧妙的社會權力關系網之下,權力的沖突變得不再明顯,很多直接的沖突轉為更加隱秘的征服與被征服關系。無論人們出于何種目的來使用全景敞視模式,都毋庸置疑的產生同樣的權力效應,它使“一種虛構的關系自動地產生出一種真實的征服。”福柯認為這種刑罰的溫和方式并非出于“人道”情感或者慈善意識的初衷,而是統治者權力運作方式和刑罰由顯性的野蠻向隱性的馴服發展的取向,是權力運作朝更高明的方式轉變的標志。
全景敞視建筑不僅具備全方位的監視功能,它還是一個對人進行特定“改造”的實驗室。“它可以被當做一個進行試驗、改造行為、規訓個人的機構;可以用來試驗藥品,監視其效果,可以進行教學試驗,尤其是可以利用孤兒重新采用有重大爭議的隔絕教育。”細致入微的規則,將人的個性分解得支離破碎,一切活動和言行必須遵照既定程序和規則來完成,全景敞視的權力運行技術變成社會需要的、培養馴順公民的“練馬場”。在福柯看來,全景敞視主義的權力運作機制是“規訓社會”權力運行的縮影,這種日益社會化與寬松的懲罰程序背后,萌生了一個新的對象領域,一個新的事實真理體系以及一大批在刑事司法活動中一直不為人們所知的角色,進而形成一整套社會運行機制。
三、“規訓社會”——“懲罰的自我節制的新時代”
全景敞視模式是資本主義權力運行的新發明,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這一模式注定要傳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機體,生成一種全景敞視主義,并創造全新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規訓社會”。福柯指出刑滿釋放者在自由和回歸正常生活之間存在巨大的難以跨越的鴻溝,與社會和正常生活秩序的格格不入,迫使他們不得不或者是只有承擔起規訓——監視機構代理人角色,這是權力運作的藝術,是權力行使者將權力無限擴大化的杰作。規訓機構不再僅僅限于全景敞視模式之下的嚴密監視,而是在全社會范圍內加以擴散,并且搖身一變成為一種讓人毫無察覺但卻能夠無限循環地在全社會范圍內運轉的新模式。福柯認為,全面普及的教育和嚴格的懲罰及監獄系統,是對民眾進行“規訓”的最“合理”和最“科學”的方法。對社會公民的“規訓”不再以一種體制或者一種機構的形式出現,而是成為一種虛擬卻真實有效的權力行使機制,一個規訓的社會在這種悄無聲息的運作中得以形成并堅不可摧。
在全景敞視主義之下,權力的效應能夠抵達最微小、最偏僻的角落,權力關系真正實現了社會范圍內的、細致入微的散布。社會上的個人被安置在統治者精心編制的權力網絡之中,形成無形的鐐銬,人們無從反抗,更難以掙脫。他們只能心甘情愿被打上印記,被區別對待,被監視記錄,被評估審判,其最終目標是將社會公眾變為能夠控制的群體,使充滿個性的個體變為統一模式之下的“馴順”公民。當紀律被無形地滲透進全社會,便使得權力的運行變得易于接受和隱秘化,同時使權力的行使以及對肉體自由的限制變得理所當然。雖然在福柯看來,肉體的解放和懲罰的“人道主義”并非是出于資本主義人道主義的初衷,而是權力運作方式更精密設計的結果。隨著文明時代的到來,懲戒權力的行使方式在演變過程中變得越來越溫和,越來越強調對個人精神層面的治理和規訓,而不是對肉體的直接折磨與苦痛。通過一系列的權力技術,個人被無休止地編織進一種社會秩序中,為的是恢復人格,即重新生產出個體被削弱的力量、被取消的技能以及被遺忘的道德。
全景敞視主義形成了一整套知識、技術和科學話語,并且與懲罰權力的實踐日益糾纏在一起,使得整個懲罰機制都發生重要變化:法律的懲罰機制不再限于酷刑、暴力和“鎮壓”,懲罰行為變成一種復雜的社會工程;懲罰行為變為一種依靠多種知識和技術領域相互合作的權力方式和政治策略;權力——技術學變為刑罰體系人道化和對人的認識這兩者的共同原則;在使靈魂進入刑事司法舞臺和一套科學知識進入法律實踐之后,權力關系干預肉體的方式真正地較以前發生改變。全景敞視主義在整個社會的運用以及法律合理性的深入人心,是紀律和規訓的勝利。野蠻酷刑和對肉體的擺布作為一種時代節點退出歷史舞臺,開始了一種用精心設計的懲罰政治學、懲罰經濟學和權力意識形態來控制犯罪的自拘性、現代國家培養“馴順公民”的“懲罰的自我節制的新時代”。
參考文獻:
[1](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等譯,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2]胡水軍.懲罰的合理性——福柯對人道主義的批判分析[J].環球法律評論,2006(2):133-143.
[3]張一兵.遵守紀律:自拘性規訓社會的建構秘密[J].社會科學研究,2015(5):145-151.
[4]汪民安.福柯的界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203.
[5]高宣揚.當代法國思想五十年(上)[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6]張一兵.資本主義:全景敞視主義的治安—規訓社會[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3:20-29.
[7]張之滄.論福柯的“規訓與懲罰”[J].江蘇社會科學,2004(4):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