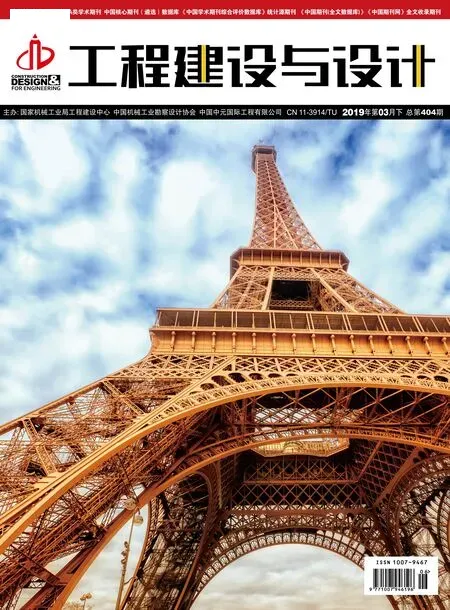上海浦東國際機場衛星廳鋼屋面風壓分布研究
周亞萍
(上海機場建設指揮部,上海201207)
1 引言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衛星廳是一座超大型大跨屋蓋結構,平面東西長約933m,南北寬約960m,由2座相連的衛星廳“S1”和“S2”組成,形成“工”字型的整體構型。衛星廳總建筑面積6.22×105m2,可以提供83座登機橋125個近機位,是全世界單體規模最大的衛星廳。
上海位于臺風多發地區,僅2018年,就有“安比”“云雀”和“溫比亞”3個臺風先后正面登陸上海。而浦東國際機場衛星廳位于上海東部,周邊地勢開闊,東部面朝海面,受臺風影響嚴重。而該結構高度較低(頂部標高39m),處于剪切風速較大且湍流度高的大氣邊界層底層,因此,風荷載為其主要控制荷載之一。而浦東國際機場衛星廳為大型異型結構,從現行規范中無法得到可供設計使用的壓力系數,目前,國內外大多采用剛性模型測壓試驗獲取相關設計數據[1~3]。
本文通過對浦東國際機場衛星廳結構開展剛性模型測壓試驗,獲取了平均、脈動和極值風壓系數,以及規范規定的體型系數。S1和S2衛星廳最上層屋蓋均為鋼結構屋蓋,而鋼結構屋面自重較輕,柔性大,阻尼小,結構更易發生大幅風致破壞。限于篇幅,本文側重分析衛星廳鋼結構屋面的風壓分布特性。通過分析給出了全風向角下最不利風壓發生的區域,并結合上海地區歷年風速風向統計資料,給出鋼屋面最可能發生風致破壞的區域,對工程設計及結構的后期檢修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2 風洞試驗介紹
風洞試驗在同濟大學TJ-3大氣邊界層風洞中開展,該風洞為豎向回流式低速風洞,試驗段長14m,橫截面尺寸為2m×15m(高×寬),試驗風速范圍為 0.2~17.6m/s,連續可調,流場性能良好,試驗區流場的速度不均勻性小于2%,湍流度小于2%,平均氣流偏角小于0.2°。
2.1 試驗模型和風向角定義
浦東國際機場衛星廳剛性測壓模型采用有機玻璃板和ABS板制成,具有足夠的強度和剛度,在試驗風速下不發生變形,并且不出現明顯的振動現象,以保證壓力測量的精度。考慮實際建筑物和周邊建筑情況,選擇模型的幾何縮尺比為1∶250,試驗模型與實際結構保持幾何相似。試驗時,將測試模型放置在轉盤中心,通過旋轉轉盤模擬不同風向,圖1為安裝在風洞內的試驗模型。
定義風從西北偏北方向吹向模型時為0°風向角,風向角按順時針方向增加。試驗風向角間隔取為15°,共24個試驗工況,方位及風向角定義如圖2所示。
在剛體模型上布置了1495個測點,分塊編號為1~24,其中,S1、S2鋼屋面挑檐上均為雙面測點,其最后結果為外、內雙面壓力的凈風壓。圖3給出了S1、S2鋼屋面測點布置圖。

圖1 放置在風洞中的剛性試驗模型

圖2 鋼屋蓋位置示意 圖及風向角定義

圖3 鋼屋面測點布置圖
2.2 邊界層風場模擬
根據浦東國際機場衛星廳項目數公里范圍內的建筑環境,確定本試驗的大氣邊界層流場模擬為A類地貌風場(A類風場定義見我國GB 50009—2012《建筑結構荷載規范》[4])。試驗中采用被動風場模擬技術,利用尖塔和粗糙元等產生湍流,模擬得到了A類風場。大氣邊界層模擬風場風速采用丹麥DANTEC公司的streamline熱線/熱膜風速儀測量。圖4給出了平均風速和順風向湍流剖面。由圖可知,模擬邊界層流場風剖面與A類規范風場(風剖面指數,α=0.12)吻合得非常好;湍流剖面整體與規范值吻合較好,150m以下湍流強度略高于規范值。圖5給出了模擬邊界層風場中模型頂部高度處脈動風速譜,并與常用的經驗譜進行了比較,包括Davenport譜、Karman譜和Kaimal譜。由圖5可知,高頻部分譜值與Davenport譜吻合較好。低頻部分譜能量低于3種經驗譜,這主要是受風洞尺寸和現有湍流模擬技術的限制,導致大尺度湍流不足。目前,在不增大模型縮尺比的情況下,還沒有比較好的辦法解決。但是,一般認為在湍流積分尺度不小于實際湍流積分尺度1/2的情況下,對局部風壓影響較小。

圖4 風剖面和湍流剖面

圖5 建筑頂部高度處脈動 風功率譜
2.3 參數設置及數據處理
風洞測壓試驗的參考點風速為12.0m/s,對應50年重現期基本風速的風速比為1∶1.42。壓力測量和數據采集使用美國Scanivalue掃描閥公司的DSM3400電子式壓力掃描閥系統。測壓信號采樣頻率為312.5Hz,每個測壓孔采樣樣本總長度為6000個數據,采樣時長約為19.2s,根據相似比,對應于實際采樣時間約為1145s(50年重現期)。為消除風壓信號經過測壓系統后的畸變影響,利用測壓管路系統的傳遞函數對試驗采集的風壓數據進行了修正。
本文中的風壓系數以梯度風高度處的動壓為參考,由式(1)計算得到:

式中,Cpi為i測點處參考梯度風高度處動壓的風壓系數;Pi為作用在測點i處的壓力;P0和P∞為試驗時參考高度處的總壓和靜壓,由放置在參考高度處的皮托管測得;S為將風洞測得的風壓系數換算得到以梯度風高度處動壓為參考風壓的換算因子,對于 A 類風場S=(1×100/300)0.24=0.7682。
根據測得的各測點風壓系數時程可得到統計量平均風壓系數(Cpmean)和脈動風壓系數(Cprms)。通過平均風壓系數和脈動風壓系數可計算得到用于圍護結構設計使用的極值風壓系數(極大值風壓系數和極小值風壓系數):

式中,g為峰值因子,一般取2.5~4,本文取g=3.5。
GB 50009—2012《建筑結構荷載規范》定義的體型系數μsi可由各測點平均風壓系數轉換得到:

式中,Cpmean,i為測點處平均風壓系數;zG為A類風場梯度風高度;z為測點i處高度;α為風剖面指數。
3 結果分析
3.1 風壓分布
圖6~圖8給出了全風向下體型系數、平均風壓系數和極小風壓系數最小值。由圖可知:
1)由于衛星廳為對稱結構,在不考慮周邊建筑影響的情況下,S1和S2鋼屋面全風向下風壓系數最小值大致呈對稱分布,與預想的結果一致,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測量結果的可靠性;
2)S1、S2鋼屋蓋上表面風壓及挑檐處的凈風壓主要呈現為負壓(即升力);鋼屋蓋上各測點體型系數全風向下最小值在-1.8~-0.2,平均風壓系數全風向下最小值在-1.0~-0.2,極小值風壓系數全風向下最小值在-1.8~-0.2;
3)雖然S1和S2鋼屋面標高不同(S1鋼屋面頂部標高39m,S2鋼屋面頂部標高34m),但平均風壓系數和極值風壓系數沒有明顯不同,表明對該建筑而言,S1和S2鋼屋面的結構高度不同對屋面風壓結果沒有顯著影響;
4)最不利風壓出現在鋼屋蓋挑檐區域,體型系數大部分在-1.8~-1.2,且等壓線分布密集,表明風壓變化梯度較大。這一方面是由于,當挑檐迎風時,鋼屋面挑檐上表面迎風前緣氣流分離距離,會在上表面產生較強的負壓;另一方面,當挑檐迎風時,挑檐下表面為正壓(升力),會與上表面吸力疊加。在結構設計及后期檢修時需特別注意挑檐區域;
5)鋼屋面中部區域風壓同樣受負壓控制,但風壓相對較小,體型系數為-1.0~-0.2。另外,屋面中部區域風壓梯度變化不大。這主要是由于鋼屋面坡度較小且走勢平緩。

圖6 全風向下最小體型系數

圖7 全風向下最小平均風壓系數
3.2 體型系數隨風向變化規律
圖9給出了S1鋼屋面挑檐邊緣區域典型測點19-1~19-18的體型系數隨風向角的變化規律。由圖可知,體型系數隨風向的變化而變化。在所有風向下,圖中所給測點體型系數幾乎全部呈現負值,當風向角在90°~180°(東南風)之間時,體型系數絕對值最大。圖9同時給出了上海市歷年風向風速玫瑰圖,圖中實線為風向概率,虛線為風速大小。由圖可知,東南風為流行風向,且該風向風速一般較大。而這恰好與S1鋼屋面下翼緣測點19-1~19-18的最不利風向角一致。可見,S1鋼屋面下翼緣挑檐區域為最易發生風致破壞的地方,檢修時需特別關注。

圖8 全風向下最小極值風壓系數

圖9 典型測點體型系數隨風向角變化規律
4 結語
本文基于浦東國際機場衛星廳1∶250剛性模型測壓試驗,討論了S1、S2鋼結構屋面體型系數、平均風壓系數和極值風壓系數分布規律,發現最不利風壓出現在鋼結構屋面挑檐區域,需引起設計人員的注意。另外,本文還討論了挑檐區域典型測點體型系數隨風向角的變化規律。結合上海歷年風速風向玫瑰圖,發現S1鋼屋面下翼緣南面挑檐區域為最易發生風致破壞的區域,檢修時需特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