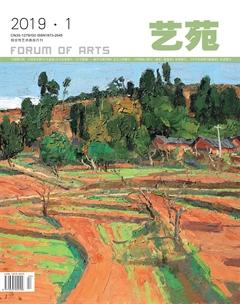后現代語境下的社會困境趙瑞君
趙瑞君
【摘要】 臺灣著名舞臺劇導演賴聲川創作的“相聲劇”系列頗受好評,其中,《這一夜,woman說相聲》更是顛覆以男性為主導的相聲界傳統,大膽地將女性話題呈現于舞臺之上。這部作品顯示出了鮮明的實驗性和后現代主義的色彩,并通過掃描女性群體,對社會弊病完成了一次把脈。
【關鍵詞】 賴聲川相聲劇;藝術特征;后現代;社會困境
[中圖分類號]J80? [文獻標識碼]A
1978年,賴聲川進入伯克利大學戲劇藝術研究所攻讀戲劇專業。1983年,他回到臺灣,第二年就成立了“表演工作坊”,并在三十多年間持續推出佳作,其中以《那一夜,我們說相聲》(1985,以下簡稱《woman說相聲》)為起點的相聲劇系列用強烈的創意性吸引觀眾涌入劇場,“相聲系列”也成為了表演工作坊的金字招牌之一。
2005年,賴聲川執導的相聲劇《Women說相聲》在臺北“城市舞臺”上演,這部作品保持了他1985年以來5部相聲劇的形式,也延續了賴氏相聲劇的輝煌。通過這部作品,我們大致可領略賴氏相聲劇的藝術特征,同時,借這部“由女人說相聲”的作品,我們也可看到導演對社會弊病、女性話題的探討。
一、賴氏相聲劇的藝術特征
(一)相聲與戲劇結合的魔力
賴聲川在創作相聲劇系列作品時曾在筆記中寫道:“相聲是幽默,是痛快,是我們苦澀的中國人唯一純粹喜劇形式的表演藝術形態”,將相聲揉入戲劇,不但體現出了極大的實驗性,而且能讓作品在更大程度上迎合普通受眾的審美情趣。20世紀末期,臺灣的社會現實紛繁怪誕,矛盾叢生,政治、經濟、文化種種問題困擾著人們,讓民眾疲憊不堪,生活的趣味無處可尋,此時,喜劇無疑迎合了人們釋放壓力、治愈心靈的需求,這也使賴聲川將相聲的表達方式融入戲劇。
相聲是依托于語言的,相聲藝術所引發的笑聲,大多源自語言這個要素。[1]161從舞臺效果來看,相聲需要在短時間內引爆笑聲,這與直接的、以形體表演為手段的喜劇相比,制造笑料的方式顯得更為間接、迂回,因此,通過語言調動觀眾的想象力就顯得尤為重要。為了保證普通觀眾在短時間內體會到其喜劇性,相聲便經常選取普通群眾生活中的事物、現象,或者容易激發起群眾共鳴的某種集體記憶為創作素材,用一個個段子,拉近舞臺與生活的距離。
在《woman說相聲》中,導演將場景設定在“total woman”公司的年終晚會上,由安妮、貝蒂兩位女性業務員主持,會中邀請“女相聲”祖師爺周方氏老太太教業務員們“說話的藝術”,而老太太缺席,只能由孫女芳妮代替。芳妮來到現場后,導演為其安排了七個段子,這些段子大都娛樂性很強,能帶來較好的舞臺效果。以“段子一”為例,整部戲進入正題便是以“罵街”為起始,由芳妮講述奶奶周方氏以罵街起家的傳奇故事,在芳妮的還原下,周方氏對社會的犀利思考便躍然臺上:
只要你敢,什么都能干!這年頭在臺灣啊,沒嗓子的當歌星,沒身材的當模特,沒表情的當演員,沒劇情的當連續劇,有劇情的竟然是新聞![2]13
除了拿流行文化開涮,周方氏老太太還直接對“挖路”“媒體”“強權人物”大批特批,通過通俗的語言將角色對社會的看法吐露,一個個段子圍繞不同主題對周遭的現實進行評判,這讓相聲劇成為臺灣現實與民眾心態的最佳注腳,也使得賴聲川一直以來所倡導的讓戲劇成為“公共論壇”的理念得到了貫徹。
當然,也有不少評論指出賴氏相聲劇的“缺點”,認為賴聲川的相聲劇比起內地相聲,在“包袱的組織、捧逗的默契”等方面都顯得遜色,但事實上,這樣的評論忽略了賴氏相聲劇的本質:它并不是讓作品完全“相聲化”;與傳統內地相聲相比,賴氏相聲劇之所以內容和形式都顯不同,是因為它生發于臺灣小劇場運動,這是一場關于話劇的實驗性改良活動,相聲劇系列呈現的遠不止“相聲”,賴氏相聲劇雖采用了傳統相聲的基本體裁,但這些作品也在西方現代戲劇美學的導引下產生了強烈的形式自覺,開發出一種多元時空的藝術,這使相聲劇突破了傳統相聲的單向度敘事模式,在時空形式的多維對比中表達出深廣的歷史文化內涵。正是這種時空藝術的成功運用,使相聲劇能夠超越傳統相聲,成為一種更加高級的藝術形態。在《woman說相聲》中,這一特點也顯得尤為突出,“罵街”“我姨媽”“練口才”等幾個段子節奏較快,一是在于語言的排布,二是為了展現演員單口、群口相聲的功底,但整部作品并不是將這一套路由始至終貫穿的,在段子四“旅途”中,舞臺上只剩下芳妮,之前在各個段子中極為活躍的芳妮突然“自我沉淀”,不同于之前單口炫技般的演出,在這一段中,芳妮的表演是戲劇化的,她對著一面鏡子開始內心獨白,展現了一位被拋棄的中年婦女的心路歷程:為挽回前夫而去整容、通過購物宣泄憤怒、最后重歸平靜,相約最初相戀時去的淡水,才發現早已物是人非,翩翩少年和婉約少女都已不復存在,棄婦看著光陰靜靜流過,幽怨中又夾雜著時不我待的嘆息和對“失去了自我”的憤恨,顯得十分動人。
由此來看,賴氏的相聲劇并非生硬照搬,而是將戲劇、相聲有機結合了起來:相聲的骨架和對語言的玩味,戲劇的情節、舞臺氛圍、表演張力……結合產生的多重美感使得相聲劇系列不但展現出了實驗性,也增強了觀賞性。
(二)后現代色彩——解構與拼貼
當然,賴聲川相聲劇獲得觀眾的青睞和較好的反響并不僅僅由于這是“相聲與戲劇的結合”,《woman說相聲》給觀眾帶來的沖擊不只是由演出形式帶來的,而是因為其中蘊含的極強的后現代色彩為作品附上了多重的審美趣味。在后現代主義的語境中審視《woman說相聲》,便會發現,這部作品的創作內含著“解構→重構”的邏輯。
后現代主義之父哈桑對后現代文化藝術的第一個概括就是解構性,這是一種否定、顛覆既定模式或秩序的特征。[3]后現代主義通過解構的方式達到對中心性、統一性、權威性與神圣性的消解,顯示出一種狂歡精神與游戲意識。這樣的觀念在《woman說相聲》中得到了彰顯,這部相聲劇從“外在”到“內在”,都被解構性貫穿。
從外在來講,選取女性演員說相聲,無疑是對相聲界男性話語權的一次沖擊。方芳、蕭艾、鄧程惠三位女性憑借這部戲取得“票房滿貫,加演連連”的成績后,“女相聲”的說法才突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關注史料不難發現,女人說相聲并不是近年來才有的,早年間,江湖撂地賣藝的藝人很多是全家上陣,女性多少也會說上幾段,但這大多是用作幫襯的;20世紀30年代后期大陸出現了說相聲的女職人,可考的有來小如等;40年代以后,女性說相聲更趨于專業化;再后來,1988年舉辦的星海杯專業相聲電視邀請賽里的“五朵金花”也引人注目;放眼大陸之外,臺灣地區的“臺北曲藝團”里也有極具表演資歷的女性相聲演員。但遺憾的是,女性相聲演員只占極少數,兩岸女相聲的發展其實并不盡人意。這其中有許多傳統因素,相聲這一表演樣式要求演員制造夸張、滑稽等演出效果,這與傳統所崇尚的女性溫婉之美具有相悖的特點,因此,女人演相聲往往只能通過自我丑化或去性別的方式去表演,這無疑有一種矮化女性的嫌疑;而且相聲藝術本身也更多地顯示著單一的男性中心化的特點,女人更多地出現在相聲里男人們的談論、調侃中,沒有自己的話語權。以這樣的行業現狀為底色,便會發現《woman說相聲》所具備的魄力——女性角色并不是男性的陪襯,三個女演員在舞臺上探討的是美容產品、生理期、婚戀、身材等女性關注的話題,比較真實地映射了當代社會女性的處境,這部戲選用女性演員、女性話題、女性表達,具備著一種解構傳統的勇氣。
從“內在”來講,解構的特征也表現在對傳統敘事的質疑。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利奧塔將后現代一詞定義為“對元敘事的懷疑”,利奧塔認為:“元敘事或大敘事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敘事。”后現代的根本特征是一種對元敘事的消解,對宏大敘事的霸權予以批判,在普遍適用的宏大敘事失去效用后,具有有限性的“小敘事”將會繁榮,賦予人類新的意義價值。自戲劇發源以來,不論是觀眾還是創作者都體現出一種重視宏大敘事的自覺,許多經典名劇尤其是悲劇慣以英雄、命運、家族作為其描寫對象,體現出了極大的濟世情懷和極高的藝術價值,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小人物的喜怒哀樂、片段式的生活情境或許更該搬上舞臺,一是可以豐富戲劇的敘事內容,二是可以更好地貫通戲劇與現實,引起人們的共鳴和思考。不難發現,《woman說相聲》不是從宏大敘事的視角出發的,劇中未出場的周方氏老太太名頭雖是“相聲表演藝術家”,但看完作品我們便會發現,她只是一個由罵街起家的老太太;周老太太和劇中的其他角色雖然總是在表達自己對生活、社會的看法,但都只是與相關情境掛鉤的只言片語,而不是按照傳統敘事方式由時間和沖突串聯起來的,因此,《woman說相聲》從“外在”到“內在”都表現出了對傳統的解構。
當然,解構之后就會有新的構建方式,在擯棄了許多傳統規則之后,《woman說相聲》的重構方式也是遵循后現代主義的規律的,這部作品顯示出了很強的狂歡意識,這種意識通過片段式的拼貼發揮出了效果。首先,這部相聲劇由七個段子拼貼而成,分別為:第一段,罵街;第二段,我姨媽;第三段,練口才;第四段,旅程;第五段,立可肥;第六段,戀愛病;第七段,瓶中信。
通過羅列不難看出,七個段子有的講述老太太的趣事,有的表達女性對生理期、身材的思考……內容之間并無嚴格的邏輯、時間聯系,而是自由地貫穿了女性生活的多個方面,所有段落的表演并不拘泥于同一風格,這種片段式的拼貼顯示出的多重趣味更容易讓觀眾拍手稱快。深入這些片段的內部,我們依舊可以看到極強的拼貼意識,在第一段中,芳妮模仿奶奶“智斗”偷懶車夫時,一人重現了潑辣的周方氏和畏手畏腳的王媽媽的表現,展現時,芳妮采用了京劇、黃梅戲、歌仔戲等不同劇種唱腔;除傳統戲曲外,芳妮的表演還借鑒了“急智歌王”張帝的風格,以通俗的表達和即興填詞的方式為舞臺增添了新的風景線。
由此看來,《woman說相聲》貫徹了后現代主義的原則,通過解構和拼貼,打破了傳統的束縛,模糊了高雅與通俗、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界限,體現出了極強的實驗性;同時,其中隱含的娛樂性和狂歡性更是讓這部作品在當今的消費社會中體現出了更高的商業價值。
二、《woman說相聲》主題開掘——女性私語與社會弊病的變奏曲
《woman說相聲》雖具有極強的喜劇性和狂歡性,但并不意味著這部作品全然是為了迎合觀眾、逗人發笑;碎片式的拼貼雖然消解了為宏大主題所服務的指向,但我們也應看到,這些碎片中也夾雜著對女性群體生存現狀的審視和對社會問題的思考。
這部戲是從女性話題入手的,極具女性意識,劇中人物的設定就有其深意。這部作品最先登場的是total woman公司的銷售高手安妮和貝蒂,如果按照相聲的講究,這兩人是應該有捧逗之分的,但我們看到的是,安妮和貝蒂的人物設定是非常雷同的,她們同時作為“現代職場女性”這一符號存在于舞臺之上,并展現出這類女性面臨的困境。安妮和貝蒂作為total woman公司的南北兩區銷售冠軍,不停以“隨心所欲做自己”為公司理念進行宣傳,但拋開這句看似支持女性獨立的宣言觀其內核我們便會發現,這家公司的產品要么以美容減肥、提臀豐胸為賣點,要么就是推出以“勾人”“甩人”“抓奸”為主題的“心靈課程”,由此可見,所謂的“total woman”根本沒有體現出真正的女性特質,也沒有給女性提供一條“做自己”的出路;回到安妮和貝蒂兩人,第五個段子展現了她們后臺閑聊的場景,兩位事業有成、身材窈窕的女性竟抱怨自己不夠瘦,于是氣急敗壞地撕壞衣服、幻想以胖為美的風潮來臨時的天下大同,但幻想終究只是幻想,當短暫的“夢”結束后,她們也只能把自己塞進窄小的衣服,繼續回到臺上,虛偽地鼓吹減肥和整容,繼續去迎合以男性為主體的審美觀。與她們相比,芳妮顯得自由了許多,她作為周方氏老太太的孫女,學起奶奶“罵街”可謂是高度還原,她在臺上批判戀愛、批判政客、批判當時臺灣的亂象,但模仿終究是模仿,在段子四“旅程”中,我們才看到了一個真實的芳妮——被丈夫拋棄、無法走出泥潭的怨婦,芳妮在本段開場時有這樣一段獨白:
女人,你是誰?你為什么那么難找?很多女人都是因為婚姻碰到狀況就毀滅掉了,完全失去信心,必須重新找到自己,好像除了婚姻就沒有別的。
怎么會這樣呢?
【停頓】我就是。
一哭二鬧三上吊,多蠢!
【停頓】我就是。[2]36
在這里,芳妮上演了將重心全部放在婚姻上卻落得悲慘結局的女性的內心變化,她雖然懂得許多道理,卻依舊走不出種種怪圈。可以說,以芳妮為代表的回歸家庭的女人和以安妮、貝蒂為代表的職場女性,前者沒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和人格,后者受社會觀念的裹挾無法踐行自己的生活方式,雖各有各的煩惱,卻殊途同歸——不論是哪種女性,都在不斷迎合中失去了自己,無法做到“隨心所欲”。如此看來,劇中唯一給人希望的女性只有周方氏老太太,她雖然出生于清朝,卻性格直率、敢說敢做,她的“罵街”針砭時弊,被人們當做“街頭藝術”;她認為當潑婦沒什么不好,只有成為潑婦,才能讓“在男人的世界里發揮不了作用”的女性擁有發聲的權利;她甚至具有獨當一面的氣概,靠罵街賺錢養活全家。周老太太并不和男性對立,也不因自己是女性而自憐自艾,這一人物雖看起來沒什么文化,卻隱含著一種最原始的女性獨立觀,但比較可惜的是,在舞臺上,老太太本人是缺席的,這或許也意味著,在由男性掌握話語權的世界里,真正能夠像周方氏老太太那樣隨性做自己的女人少之又少。
當然,這部相聲劇并沒有局限于女性私語,導演透過“女人的話題”,還折射出了許多社會問題。從第一段開始,就有社會弊病不斷被提及,芳妮說,奶奶罵街,自然從“街”先罵起:
臺灣的街是很欠罵的!喲呵,睡一覺起來怎么又多一個坑啊?昨天早上不是才鋪好的嘛?什么?電信局又來挖了?我們的日子過不過啊?……我說這前后六個單位,你們彼此之間到底是認識不認識啊?就算不認識,你們彼此之間能不能聯系聯系,選個黃道吉日一塊來挖![2]16
批判了各個單位的工作方式后,奶奶還對媒體不嚴謹、政府不負責、男女不平等的現狀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可謂十分犀利。當然,對社會問題的揭露并不都是由周方氏老太太的“罵”來展現的,有些社會弊病隱藏在其他人不經意的討論中。比如,段子五“立可肥”看似只是展現了安妮和貝蒂的暢想,但事實上卻完成了一次對于審美和當代生活的探討:許多女性追求極致的瘦,為穿上一件好看的衣服寧愿兩天不吃飯;胖和丑都成了原罪,抽脂、整容成了常態;安妮和貝蒂都希望回到胖才是美的時代,卻驚異地發現,充斥在我們生活中的各種宣傳、廣告、產品都是以“瘦”為導向的,一切向“瘦”看的審美標準雖然不正確,卻有著強大的資本和無數的商機去推動、去維持,單一的取向已經成為了一股潮流,無法輕易打破,當代生活看起來如同晚會燈光般絢麗多彩,但其背后卻隱藏著資本的推動和個人的盲目與無奈。由此可見,《woman說相聲》中的一個個片段里,都隱含著對社會問題的探討。
三、結語
誠然,這部相聲劇并不是滿分佳作。從表演上來看,劇中只有具備脫口秀經驗且演技老道的方芳的表現可圈可點,其他兩位雖擅長戲劇表演,但對相聲表演技巧的拿捏有點力不從心;從內容來看,這部劇作與《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千禧夜,我們說相聲》等相比,在文化的厚重感和主題余韻上遜色了幾分。盡管如此,它依然是一部值得關注的作品,其中包含的對女性話題的關注、對戲劇表現形式的創新都作為一種創作策略,以其離經叛道的風采吸引著我們細細品味。
參考文獻:
[1]劉梓鈺.相聲藝術的奧秘[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0.
[2]賴聲川.賴聲川劇場第二輯——這一夜,woman說相聲[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
[3]伊哈布·哈桑.后現代轉向[M].劉象愚,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