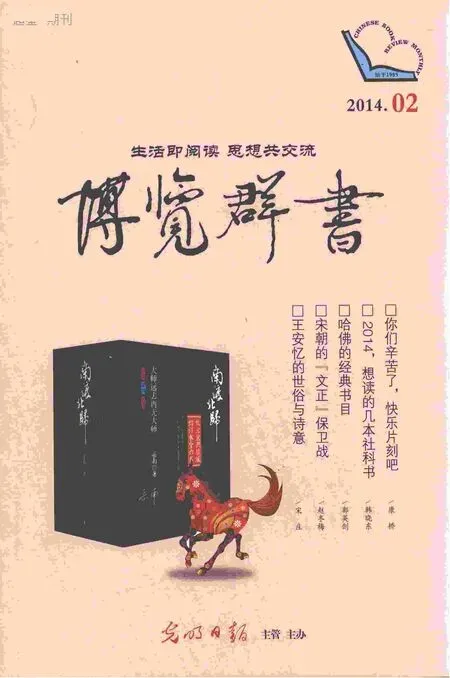嘆!一千八百年前的文藝理論
石英
有時我很難想象,一個公元2世紀后期至3世紀初距今近1800百年前的“中青年”,不僅寫出了流暢自然,富有民歌色彩的歌行體詩,特別是竟能作出五卷本的言簡意賅、貼近創作實踐,直至今天仍有啟示價值的文藝理論文章;而且其人還并非單純的“專業作家與評論家”。你道怪也不怪?
但這確有其事,確有其人。此人就是曹操的次子、史稱“三曹”之一的曹丕(字子植)。此人從一個方面講,在表面平凡甚至憨厚之態的遮掩下,承繼乃父威權霸業志在必得,而且得力于司馬懿、華歆等權謀家暗點或明唆的有效支持,在相搏爭奪中逐漸占得先機,居于不可比擬的優勢; 其弟曹植被排擠出局,丕仍然步步進逼,所謂“七步詩”的故事就是其弟幾被擠向懸崖的象征性一幕。與之同時,在乃父曹操死后,丕終于徹底廢掉了傀儡皇帝劉協,成為曹魏的第一代皇帝。從這一方面來看,好像此君日日夜夜都在與心腹權臣竭盡陰謀以實現“大業”。
這些先不說它,因為許多事情都是統治者及其家族子弟間為獲取極權所必然,還能指望他們一個個都是謙謙君子,如故事傳說中那樣“孔融讓梨”般地溫良恭讓嗎?顯然是不可能的。我還要說的是:自丕登基到去世的七年間,由他獨當一面自領大魏的軍政勛業似乎并無多大起色,能夠“守成”就算不錯,對照先王孟德公,他在手扼軍政大軸轉動寰宇的能力上顯見不足; 真正的實權還有向極擅隱忍的權謀家司馬父子暗轉之勢,而丕似乎淡化了乃父生前的提示,臨終前還將懿公作為托孤大臣而倚重。部分原因也許是出于無奈,誰叫自己早于年長近十歲的“老師”匆匆地“走”了呢?悲夫?
不過,且慢,客觀公正的后世人千萬莫要忽略了此公的另一面,那就是在文學創作尤其是文藝理論方面的獨特造詣和成就。他的著述很多,現存詩歌四十余首,形式多樣,自成風格,抒情意味中極富人生況味世事滄桑。僅以許多人所熟悉的“燕歌行”為例,它不唯是我們今日所能見到的最古的七言詩,也是幅制較長的“中篇抒情詩”。全詩句句押韻,明麗卻又深沉,無疑是一首思、情、音韻俱佳的力作。如果說以詩歌創作而言他在“三曹”中尚不為奇(因其父曹操古樸蒼勁的四言詩之老到,其弟曹植風雅瑰麗的大量詩賦,各領風騷),而他的詩文評論乃至文藝理論方面的成就,不僅在魏晉時期即使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也占有相當突出的地位。今天的《典論·論文》只是他五卷《典論》中的一篇。此篇在我大學的古代文藝理論課中,除《文心雕龍》《詩品》等著作外,單篇文章中最重點的就是曹丕的《典論·論文》和陸機的《文賦》。足見其被重視之程度。“論文”中最搶眼之說則是將文學的精神價值作為“軟實力”提升至空前高度,所謂“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強調文學作品“以氣為主”。此處的“氣”,不少人解釋為“氣勢”,不能說不對,卻不夠全面,亦未觸及到內質之深度。“氣”,含有氣格、氣質、氣韻等深層感覺。氣度、氣勢的風神和儀態。他還主張作品忌呆板與單調,認為“文非一體,各有專長”,實際上已接觸到作品的不同風格問題; 而且認為對不同的風格應予以尊重,不可強力致之。為此,他對建安時期的一些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作了深入淺出的評判、分析。如說“徐幹有齊氣”。“齊氣”,應作何理解?土味兒?地方特點?有人以為此說有貶意,實則從本質上說是:有獨具的地方色彩和本土氣息。
最可貴的是,一篇近1800年前的文藝理論文章,讀之半點也無遙不可及之虞,而且不乏現代感。你道怪也不怪?從這一方面看,這位魏文帝并非終日只是玩弄權機、一味過皇帝癮的角色。他的詩作特別是他的文藝理論文章,都不是偶一為之唾手可得的小擺設,肯定都是些很用心、很吃功夫的成品。試看當時三國的文士,更遑論當時其他帝王將相們,哪一位在文藝理論上能“玩”得過他?所以僅以“論文”為代表的五卷“典論”而言,便使我本來從小說和影視中獲得的對此公的欠佳印象,應回歸于較全面的理性為宜。一篇對后世產生了如此重要影響的文章,其價值較之生前多奪下蜀、吳的幾個城池又當何如?盡管不便比擬,至少也耐人尋味。
(作者系人民日報社編審,中國散文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詩歌學會理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