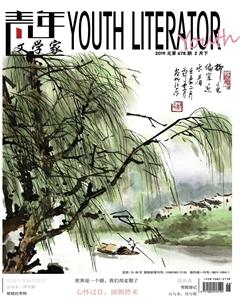淺論全面抗戰時期蕭紅小說中的苦難書寫
摘 要:戰爭給人們帶來了深深的災難,全面抗戰時期的蕭紅在創作小說時結合自身的流亡體驗,通過自己細致的觀察,把戰爭給人們帶來的苦難呈現于小說中。她小說中書寫戰爭的苦難側重于對戰時人們心態生活的書寫、戰爭帶來的家破人亡、生離死別的敘述和對戰時人們國民劣根性的揭露,進一步揭示了戰爭對于人們的戕害。
關鍵詞:全面抗戰時期;蕭紅小說;苦難
作者簡介:陳加林(1992-),重慶人,漢族,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6-0-02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的大地到處彌漫著硝煙。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提出的口號是“文章下鄉,文章入伍”[1],鼓勵著作家們深入現實生活,文學在此時充當了時代的號角,英雄主義的調子貫穿大多數作家創作的始終。蕭紅這一時期創作沒有跟隨文壇的主流,她創作的小說,是通過對身處于戰爭中人們的日常生活、心理活動的描述來表現戰爭對人們身體上和精神上造成的創傷,從側面反映戰爭的無情與殘酷。
一、戰爭苦難的生活化
蕭紅的戰時苦難書寫體現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她在戰爭書寫的小說中沒有轟轟烈烈地戰爭場面的描繪,有的只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戰時的日常生活寫照,凸顯他們在戰爭苦難中心理創傷和肉體摧殘。蕭紅的小說中出現了一系列悲苦的、受迫害的人物形象,父母念子失子幾乎瘋癲的程度,兒童在戰爭中天真童心的喪失和生命的被剝奪,戰爭中戀人的生離死別的情景,戰爭中人性的揭露。
《汾河的圓月》《曠野的呼喊》從父母對其子的思念,揭示了戰爭給人們造成家庭的分崩離析。《汾河的圓月》中母親失去兒子,孩子小玉失去了在兵營中的父親,而后小玉的母親又改嫁,家中只剩下孤苦的祖孫女二人,失去兒子后的母親瘋癲,一直念叨著,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是日寇的入侵,此文雖沒有正面戰場的出現,可是戰爭的硝煙卻依舊在。《曠野的呼喊》里父母思念兒子,在日常生活中顛三倒四,“兒子走了兩夜,第一夜還算安安靜靜地過來了,第二夜忽然就可怕起來。他通夜坐著,抽著煙,拉著衣襟,掃著炕沿。上半夜嘴里任意叨叨著,隨便想起什么來就說什么。”[2]陳姑媽也同樣是時時刻刻念著兒子,她在做飯時候的神游,把豆油和棉花籽油搞混淆,直至吃了棉花籽油的陳公公也依舊未能發現。蕭紅從日常生活、人物之間的對話、環境的描寫把戰爭造成日常生活的苦難充分地展現了出來,簡直是此時無硝煙更甚于硝煙的境界。
《孩子的講演》中的王根只是一個小孩子,在戰爭中他的家鄉被日本侵略者占領了,他離開了家人去服務團當了勤務,他的父親讓他回家,他堅決不回,“打鬼子不分男女老幼,”[3]他的講演贏得了大眾的認可,可在一瞬之間,他成長了,變成了一個小大人,其實他只是一個九歲的孩子,在夜里他依舊害怕著。戰爭剝奪了孩子童真、害怕、膽怯的天性。同樣,在《蓮花池》中對孩子的敘述,亦是在戰爭的背景當中,老人和孩子的生活本就十分的艱難,而日本人卻硬生生地剝奪了祖孫二人的生活,甚至是孩子的生命。本已是清貧的祖孫二人相依為命,可是戰爭卻將二人天人永隔。蕭紅憑借自己細致的觀察和敏銳的思維,將戰爭的苦難充分的揭露了出來,側重表現戰爭給人們日常生活帶來的苦難,形成了蕭紅抗戰文學獨特的風格。
二、戰時國民性問題的揭露
1902年,以梁啟超的《新民說》為起點,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逐漸對中國國民性的反思。1907年,魯迅在他的《摩羅詩力說》中提出“國民性”的概念,他對“國民性”進行了探索。魯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四卷五號上發表《狂人日記》開始,他始終抓住國民劣根性進行批判。魯迅為蕭紅的《生死場》作序,二蕭與魯迅結下了不解之緣,二蕭曾向魯迅請教應該怎樣創作,魯迅對其二人的回答是:“不必問現在要什么,只要問自己能做什么,現在需要的是斗爭的文學,如果作者是一個斗爭者,那么無論他寫什么,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斗爭的。”[4]蕭紅在與魯迅的交往中,深受其思想的影響,她創作出來的作品也是深深地抓住國民劣根性的部分進行暴露。在全面抗戰這一時期,蕭紅創作的作品不僅直接表現了在戰爭中人們生存的苦難,而且繼承了魯迅國民劣根性書寫的蕭紅,通過自己流亡的生命體驗,對戰爭中人們生活的細致觀察,抓住了國民劣根性的特點加以描述,在戰爭中暴露出來的國民劣根性從而又加重了人們的苦難。
蕭紅1939年7月創作的小說《山下》的主人公林姑娘在下江人家里干活,林姑娘家生活的起起落落源自于下江人對林姑娘的雇用與否。林姑娘家里的好日子終結于林姑娘的生病。此時,王丫頭不愿意幫林姑娘的忙的原因在于之前林姑娘在她面前風光過,心里妒忌。此外,林姑娘的母親在林姑娘生病之際趁機想在下江人家里撈到更多的好處,與下江人討價還價的過程,也進一步揭示了人性自私的一面。
《呼蘭河傳》是蕭紅在戰爭的背景下通過自身的流亡體驗,遙望故土之思,為呼蘭河這座小城所作的傳記。蕭紅對呼蘭河這座小城里的人物的生活狀態以及人物處理問題的方式進行描述,充分地將人物麻木的思想以及愚蠢的行為等國民劣根性呈現在讀者眼前。《呼蘭河傳》雖然沒有對戰爭的描述,但是它是在戰時寫成的,蕭紅親身經歷著戰爭,對于苦難有著深刻的體味。蕭紅回望故土呼蘭河,對呼蘭城里人們麻木、封建、保守的國民劣根性生動形象的刻畫于紙上。在《呼蘭河傳》里對“大泥坑”情節的敘述,對大泥坑的基本情況作了介紹之后,接著圍繞大泥坑敘述人們在大泥坑周邊發生的一些“瑣事”:抬車抬馬、淹雞淹鴨、下雨天過泥坑的謹慎、瘟豬變淹豬等。通過這些事件的表現,把人們處理問題的方式以及思想充分地展現出來了。蕭紅給讀者呈現的是呼蘭河這座小城里人們的思想的封建與精神的麻木。同樣,在呼蘭城這座小城的風俗習慣里,“跳大神”、“唱秧歌”深刻地體現了小城人們的群體性的愚昧與無知。
蕭紅的長篇小說《馬伯樂》中的馬伯樂在一個無處安寧的亂世之中,他愚昧、虛偽、懶惰、消極且又自私自利。馬伯樂的愚昧表現在自己生病時多吸幾支煙,孩子生病給他們吃餅干,而不是去看醫生吃藥,蕭紅將馬伯樂的封建愚昧充分地揭露了出來。馬伯樂在上海逃難期間把他的懶惰發揮到了極致,馬伯樂燒飯的小白鍋,永久不洗,他的筷子也越用越細,因為他不洗,每次都是刮。同時馬伯樂也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小說中寫到有一次車夫把馬伯樂的父親送到家之后,自己倒下了,于是馬伯樂主張把車夫送到附近的醫院去,馬伯樂的父親說是外國人的醫院,花費很高,馬伯樂卻這樣說,“不是去給他醫治,是那醫院有停尸室。”[5]在這件事情上深刻地刻畫出了馬伯樂的自私自利,他在對待自己家人的時候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之處,在火車站逃難的關鍵時刻,馬伯樂拋下了太太和孩子,自己一個人先跑的沒了蹤影。馬伯樂還是一個消極悲觀、遇事舉起不定的一個人,他的消極悲觀體現在那句“到那時候可怎么辦?”[6]蕭紅在小說《馬伯樂》中將馬伯樂的形象惟妙惟肖的刻畫于紙上,戰時的蕭紅對于國民劣根性的暴露通過馬伯樂這一人物形象充分地體現出來。通過對馬伯樂形象的塑造,蕭紅對當時部分民眾根深蒂固的國民劣根性進行了深刻揭露,戰時這種國民劣根性的存在更加加深了人們的苦難。
全面抗戰時期蕭紅小說創作,對于人們戰時生活的描述和關于國民性的暴露中涵蓋著深深的苦難。因此,人們的麻木、愚鈍、封建、保守的傳統思維和處事方式,在日本侵略者發動戰爭的年代里更是雪上加霜了。蕭紅以一種冷靜的筆調對戰爭進行著深刻的揭露。
注釋:
[1]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第344頁。
[2]蕭紅:《蕭紅全集》(上),第372頁。
[3]蕭紅:《蕭紅全集》(上),第358頁。
[4]魯迅《魯迅全集》(卷十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224頁。
[5]蕭紅:《蕭紅全集》(上),黑龍江:哈爾濱出版社,第444頁。
[6]蕭紅:《蕭紅全集》(上),黑龍江:哈爾濱出版社,第423頁。
參考文獻:
[2]蕭紅:《蕭紅全集》(上、下),黑龍江: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
[2]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
[3]魯迅《魯迅全集》(卷十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