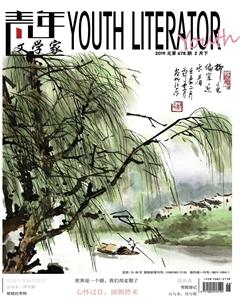活與如何活:生存困境中的方式選擇
徐小雅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6-0-02
在余華的創作中,對苦難的關注與描寫一直是重要的一部分。其代表作《活著》就是對死亡與苦難的見證。小說講述的是福貴苦難的生命歷程。主人公福貴因嗜賭而輸掉全部家產,父親被活活氣死,很快母親也不治而亡。十余年后,年幼的兒子在為縣長夫人獻血時被抽血過量,喪失性命;女兒鳳霞好不容易結婚,卻因難產身亡;妻子積勞成疾而撒手人寰,女婿意外被水泥板壓死,最終外孫也死于非命。親人的不幸交織于福貴的一生,苦難與艱辛貫穿了他的整個生命。面對這樣的生存困境,福貴選擇了承受苦難。在苦難的夾縫中尋求生存,成為了福貴生命的意義。
作者在《活著》的韓文版自序中寫道:“‘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里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于喊叫,也不是來自于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可見,福貴在面臨生存困境中的承受,是個人甚至一個民族能夠經歷眾多苦難卻又順利存活的條件。
承受與忍耐是福貴在面對苦難中表現出來的最突出特征。福貴的一生經歷了一連串的生離死別,最終只有福貴孤獨于世。福貴孤身一人后,他仍然從屠刀下救下一頭力衰的老牛,并與之相依為命。福貴一生命運多舛,最終對苦難與死亡表現出了坦然、平靜、超然的態度。忍耐已經成為了福貴內心的一種寶貴品質。正是忍耐,可以使其在生存困境面前能夠使他免于生活困境的危害。苦難作為永恒的生命狀態不斷出現于福貴的生命中,從其賭博導致親家當場開始,福貴已認識到了生命在苦難面前的脆弱。在苦難面前,反抗也顯得異常無力。以堅韌與頑強來承受苦難,反而能夠使苦難的程度在生命過程中淡化。福貴與苦難已不可分離,這樣的關系如同余華所說的“一個人和他命運之劍的友情,這是最為感人的友情,因為他們互相感激,同時也互相仇恨,他們誰也無法拋棄對方,同時也沒有理由埋怨對方”。在承受了苦難之后,福貴已不要再以積極的形式來反抗命運,因為他以尊重生命的姿態,僅為“活著”而活,并最終能釋然死亡,承受起“生命之輕”。
面臨生存困境時福貴式的承受,是否是生活于鄉土的人們面臨生存困境時的普遍選擇呢?在楊爭光的中篇小說《老旦是一棵樹》中,我們看到了另外一種選擇。小說的主人公老旦認定同村的趙鎮是自己的仇人,并以此為動力,時時與趙鎮作對,甚至不惜以兒媳為工具來制造與趙鎮的沖突。最終,老旦在趙鎮家門前的糞堆上,變成了一棵樹。
與福貴的承受苦難不同的是,老旦通過臆想仇人并由此尋求報復來給予自我生命動力。對比余華所熟悉的江南鄉村,楊爭光所熟悉鄉土的陜北高原山地。相比之下,楊爭光筆下的鄉土更突顯荒野氣息。生活于荒野的人民所面臨的生活困境,一方面是物質匱乏,另一方面是由物質匱乏而引發的精神匱乏。在陜北高原山地地區,由于交通運輸條件低下,當地的生活環境封閉而停滯,物質極度匱乏。在此環境生活下的人們往往“將芝麻看成大象,給平淡的日子制造波瀾,在這種死水微波中獲得精神的滿足”[1]。正因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匱乏,人民內心中出現了巨大空洞。面對這樣的空洞,精神匱乏的人們也就會以制造波瀾、尋找無所謂有無的事件來進行填充。在《老旦是一棵樹》中,老旦死了女人后的一個難熬的夜晚,“突然想人一輩子應該有個仇人,不然活著還有個球意思”,很快,趙鎮便成為了老旦臆想中的仇人。老旦之所以選擇趙鎮做仇人,追根究底,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趙鎮靠拐騙婦女賣給同村人做媳婦為生,在老旦眼里,趙鎮的生活是“過得去”的。趙鎮拐騙婦女能夠從中盈利,對于老旦而言,趙鎮不存在物質上匱乏的狀況。另一方面,老旦是在成為鰥夫以后,才萌生了要找個仇人的想法。而趙鎮靠拐賣婦女而活,并且村里有傳言說,每個女人都被趙鎮“過了一遍水”。這也成為老旦將趙鎮作為臆想中的仇人的原因之一。在鄉村荒野的生活環境中,食與性是貧瘠土地上人們生活的基本需求。“保暖思淫欲”,在如此環境中生活著的人們,在保持生存的前提下,才進一步對性做出要求。老旦眼中的趙鎮,無論是“食”還是“性”都很充足。老旦在于趙鎮進行對比的過程中,發現自己在“食”與“性”兩個方面都處于匱乏水平,也就對趙鎮產生了不滿。在將趙鎮選定了仇人之后,老旦的物質匱乏與性匱乏的狀態,都在心理上得到了滿足,因此也激動得“渾身肉打著顫”。在給自己的生活制造波瀾的過程中,老旦在精神上得到了屬于自己的滿足。我們可以看到,在文本中,老旦不斷滋生出與趙鎮對著干的勁頭,不惜以自己兒媳環環作為工具,只為換來捉趙鎮的一場奸。最后,老旦帶著與趙鎮“斗爭”到底的想法,變成了趙鎮門前糞堆上的一棵樹。可見,老旦“自己的匱乏永遠成為了排斥他人滿足的動力”。[2]
楊爭光筆下的老旦,在面臨著生存困境——物質與精神雙重匱乏的同時,選擇的生存方式便是以自我匱乏作為排斥他人滿足的動力,并以該動力作為滿足自我雙重匱乏在心理上的需求。在這樣的生存理念下,老旦表現出了一種近乎瘋狂的偏執。因為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匱乏,老旦需要尋找一個仇人來填補內心空洞。老旦面對生存困境所選擇的生活方式,實際上是一種“無事的悲劇”,“這些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于沒有事情的悲劇,正如無聲的言語一樣,非由詩人畫出它的形象來,是很不容易覺察的。然而人們滅亡于英雄的特別的悲劇者少,消磨與極平常的,或者簡直邁于沒有事情的悲劇者多”。[3]老旦“無事悲劇”的形式是“沒事找事”。從老旦的臆想開始,復仇就逐漸升級,捉奸、打架、殺對方的狗,甚至刨挖祖墳。在老旦偏執的假想敵斗爭中,無法遮蓋的是他的悲劇性格。面對著生活的荒誕,老旦心理與行為也透出了一種荒誕。老旦的悲劇是一種“無事的悲劇”,在物質精神雙重匱乏的生存困境下,老旦的“無事找事”體現出其精神的虛無。面對著生存的荒謬,老旦們因精神虛無而不斷制造波瀾,從而給予自我心理滿足,也就意味著被生存的荒謬反利用,被荒謬腐蝕,直到被死亡的漩渦吞噬。
與老旦的生存選擇相反的是,《活著》中的福貴,以強韌的生命承受力、毫不奢求的生活態度面對著生存困境。面對著生命中遭遇的一連串苦難,福貴活了下來,并且,“活著”就是他的理想。福貴對自己能夠一直活下來,也表示滿意:“看看身邊的人,龍二和春生,他們只是風光了一陣子,到頭來連命都丟了。做人還是平常點好,爭這個爭那個,爭來爭去賠了自己的名。像我這樣,說起來是越活越沒出息,可壽命長,我認識的人一個接著一個死去,我還活著”。可能有人會認為,福貴的“活著”是微不足道的茍活,但我們必須看到的是,“活著”首先是對立“死亡”而存在的,能活下來,便是生所表現的一種偉大。福貴們雖然只是以忍耐與承受苦難的方式活著,但是,他們已經在承受的過程中獲得了生命的尊嚴。面對著生命的無常與脆弱,福貴們沒有因為遭遇的生存困境而拒絕“活著”,而是以忍耐與樂觀的方式承受苦難,并且在苦難中獲得了釋然。在面對生活的荒謬時,受難成為了最根本的出路。這實際上是對生活荒謬性的一種反抗,而反抗的形式是“承受”。正是這樣的承受正視了生命中的生存困境與生活的荒謬性。人在承受的過程中,已經獲得了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余華的《活著》和楊爭光的《老旦是一棵樹》從不同的角度對生存困境進行了嚴肅的思考,提供了人在面對生存困境時兩種選擇方式。無論是福貴的承受還是老旦的“無事悲劇”,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指引人們認識生存困境、正視生存困境。面對生存困境時需要我們以韌性與堅強的態度正視,才能最終承受起“生命之輕”。
參考文獻:
[1]魯迅:《幾乎無事的悲劇》,《魯迅全集》,第6卷,P371,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康正果:《徐培蘭變形記——讀<黃塵>》三部曲,《老旦是一棵樹·楊爭光小說近作集》,P30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3]朱大可:《后尋根:鄉村敘事中的暴力美學》,《南方文壇》,2002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