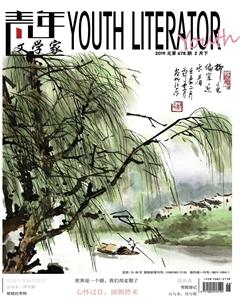《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分類標準及出土情況淺析
摘 要:《漢志》詩賦略中賦的分類標準問題一直未有定論,這主要是因為詩賦略后未附小序,沒有實證就難免令人生疑,通過分析更認同詩賦略本身就無小序,品級論的解釋更為合理。近年來也出土了一些有關詩賦略的簡帛文獻,有必要對其中較為重要的進行梳理和探究。
關鍵詞:詩賦略;分類標準;出土情況
作者簡介:宋琪(1995-),女,漢族,黑龍江綏化市人,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先秦漢魏六朝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6--01
一、《漢志》詩賦略分類標準研究概述
詩賦略下分屈原賦類、陸賈賦類、荀卿賦類、雜賦類、歌詩類五種,傳世的版本五種之后無小序,《漢志》共六略三十八種,其余五略三十三種均有小序,唯獨詩賦略所屬五類沒有小序,對于這一現象,學界持有兩種觀點。清人章學誠說:“不知劉班之所遺耶?抑流傳之脫簡耶?[1]”章學誠猜疑不是詩賦略本身沒有小序,而是詩賦略的小序在流傳過程中亡佚了。但此種說法似乎不足以令人信服,為什么內容完好無損,單單小序那一部分亡佚了呢?我們今天看到的版本都是無小序的,章學誠的這種猜測有待于后續的考古工作來驗證。姚振宗云:“按詩賦各分以體,無大義例,故錄略不為小序,而班氏因之,不盡由于疏漏也”。[2]第二種觀點認為是劉歆作《七略》時并未給詩賦略作小序,班固因襲下來未作改動。但由于劉歆《七略》已失傳,現階段無法考證。
詩賦略后沒有小序,故分類標準不明,學者們提出了諸多看法,概括起來主要有四種。一是風格論,認為詩賦略是按照風格來分類。持有這種觀點的有姚振宗、劉師培、章太炎等,姚振宗認為,屈原賦之屬“大抵皆楚騷之體”,陸賈賦之屬“大抵不盡為騷體”,孫卿賦之屬“大抵皆賦之纖小者”,雜賦“大抵尤其纖小者”。二是品級論,認為詩賦略是按照作品的品級來分類。章必功、汪祚民等人持有這種觀點,章必功認為將賦分為三類是按照它們品第的優劣,屈原賦一種最上,陸賈賦一類次之,孫卿賦一類又次之。三是漢代詩學論,認為詩賦略的分類是受到《詩經》的影響。熊良智、伏俊璉支持此種看法,熊良智認為,屈原賦之屬為風體賦,陸賈賦之屬為雅體賦,孫卿賦之屬則可視為頌體賦。四是工作次序論,認為詩賦略分類與劉向校書、收書、藏書的次序、位置有關。吳光興持有此論,吳光興認為《詩賦略》屈原賦之屬大致以漢武帝時最早收集的藏書為主,輔以部分宣帝時期的收藏,陸賈賦之屬是稍后的收藏,孫卿賦是最后一批收藏品。班固在詩賦略中把屈原賦之屬列為第一類,又將屈原賦放在第一位,我們可以看出屈原的形象及作品都是為班固所肯定的。從這個角度說,品級論的解釋更為合理。
二、《漢志》詩賦略的出土情況
《漢志》著錄古書約600部、13000卷,而近年來陸續出土的簡帛文獻,許多都沒有收錄在《漢志》中,即使是《漢志》著錄的書籍,出土文本與傳世文本也存在很大差異。所以,這里我對《漢志》詩賦略的出土情況進行了簡單梳理。
(一)銀雀山漢簡《唐勒》
1972年4月山東臨沂市郊銀雀山出土了4900余枚竹簡,其中有二十余枚賦的殘簡,因為首簡背面上端有“唐革勒”二字,因而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唐勒》賦殘簡,對于這篇殘賦的篇題和作者,學界有不同的聲音。羅福頤認為出土的賦殘簡確是“唐勒”簡,只不過題作“唐革”。湯漳平則根據殘賦的內容和辭賦命名的規律,認為《唐勒》殘賦簡稱為“御賦”最為合理,故定之為“唐勒賦·御賦”。趙奎夫則以為“論義御”三字才是本篇篇名。以上諸家在篇名上說法不一,但均認為殘賦的作者是唐勒。唯有李學勤、朱碧蓮認為這篇殘賦的作者不是唐勒,而是宋玉。李學勤說:“銀雀山竹簡《唐勒》,原有‘唐革勒二字篇題,因而很容易想到《唐勒賦》,篇中也確實有唐勒所說的話,不過,仔細考察,我認為這并不是《唐勒賦》而是《宋玉賦》的佚篇。”[3]朱碧蓮則說:“將唐勒殘賦與宋玉諸賦,其寫作體例幾乎別無二,只能說明其作者是宋玉而并非唐勒”。[4]
(二)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蘭賦”、“鵩鳥賦”
1994年初,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市場購得一批竹簡,現存二殘篇,一篇是詠蘭的,另一篇是詠鵩的,本無標題,整理者根據內容主題為其命名,一名為《蘭賦》,一名為《鵩鳥賦》。《蘭賦》存簡5支,除第五簡外,其余均有殘損,完簡長度約53厘米,除末簡下段抄寫較密者外,一般書寫字數約為58字,首章及中間部分均有殘佚,篇尾完整,全篇現存160字。內容是以“蘭”起興,托物言志,作者借蘭高潔的品德抒發情感與志向。兩篇賦不見著錄,但從內容和簡文字體來看,應與楚國有關,當為楚國的文學作品。
三、結語
有關《漢志》的研究經久不衰,一方面源于它的重要性,一方面也源于它的不確定性。年代久遠,存世的作品不多且真偽難辨,隨著相關文物的出土,人們對《漢志》的研究成果在持續更新。與最新的出土文獻相結合,才是當代學者正確的研究方向,才能在《漢志》研究方面取得更多實質性的進展,將中國古代文化之精華一點點的挖掘出來。
注釋:
[1]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064頁。
[2]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載《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1529頁。
[3]李學勤,《<唐勒>、<小言賦>和<易傳>》,載《齊魯學刊》,1990(4)。
[4]朱碧蓮,《唐勒殘簡作者考》,載《中州學刊》,1992(1)。
參考文獻:
[1]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7。
[2]王先謙.漢書補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3]傅榮賢.歷代《漢書·藝文志》研究源流考略[D].重慶:西南師范大學,2004。
[4]王曉慶.《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文獻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9:73~81。
[5]陳艷.出土文獻分類整理對《漢書·藝文志》的補輯[D].曲阜:曲阜師范大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