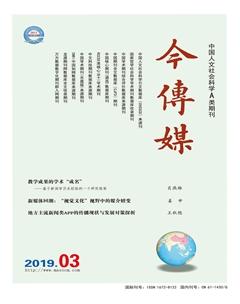熱點事件的網絡輿論傳播研究
喬春霖
摘要:隨著新媒體技術的不斷發展,特別是自媒體的高度活躍,社會熱點事件的網絡輿論層出不窮,在輿論形成與傳播中極大地影響著輿論走向。本文通過百度指數、清博數據分析“江歌案”在網絡上引起的廣泛關注、引發的輿情和后續發展,對其輿情特點、傳播特性等方面進行解析,了解傳統主流媒體、新媒體特別是自媒體在輿論傳播過程中如何影響輿論發展,從而更好地了解熱點事件中網絡輿論形成和傳播機制。
關鍵詞:網絡輿論;江歌案;熱點事件
中圖分類號:?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3-0000-04
一、 熱點事件的網絡輿論研究綜述
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發布了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止2018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高達8.02億,其中手機網民規模達到7.88億。數據表明手機網民的規模越來越大,而手機網民中幾乎都離不開手機社交媒體,社交媒體已成為互聯網媒體中最流行媒體類型之一,其傳播影響力也快速提升。近幾年來,網絡熱點事件的不斷發生也引起學者們對網絡輿論傳播研究的熱潮。學者的研究主要有微博對社會熱點事件的再傳播研究、社會熱點民生事件的微博輿論傳播等以新媒體微博為主的研究;網絡輿論場中“道德綁架”現象研究、網絡傳播中的輿論引導策略研究、網絡“熱點事件”的傳播分析與輿論引導研究等以輿論引導為重點的研究等。
二、 “江歌案”的網絡輿情傳播分析
輿論是公眾關于現實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各種現象、問題所表達的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表現的總和,具有相對的一致性、強烈程度和持久性,對社會發展及其有關事態的進程產生影響。其中混雜著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1]。有學者認為網絡輿論即是通過網絡表達出的社會輿論,并將網絡輿論從廣義和狹義進行闡述,廣義上的網絡輿論囊括了所有的社會輿論形式,既有精心選擇之后借助傳統新聞媒體表達出來的輿論,也有未經任何處理的公眾言論;狹義上的網絡輿論則特指網民通過網絡表達的輿論,也即通常情況下的網絡輿論[2]。網絡輿情是指在互聯網上流行的對社會問題不同看法的網絡輿論,是社會輿論的一種表現形式,是通過互聯網傳播的公眾對現實生活中某些熱點、焦點問題所持的有較強影響力、傾向性的言論和觀點。
在“江歌案”形成網絡輿論的整個過程中,從《局面》欄目公布江歌母親與劉鑫見面的視頻至陳世峰在日本受審判刑并公布審判結果,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中有明顯的三次輿論高峰:一是事件再度被公布出來的時候,二是“江歌案”開庭的時候,三是江歌案審判結果公布的時候。
(一)網絡輿論形成期和第一次輿論高峰(2017年11月12日至2017 年11月19日)
網絡輿論形成開始于2017年11月9日,新京報《局面》陸續發布促成江歌媽媽與劉鑫的見面的視頻,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11月11日,微信公眾號“東七門”發布文章《劉鑫,江歌帶血的餛飩,好不好吃?》引發部分網民指責劉鑫,此案件成為熱點并形成輿論是在擁有粉絲千萬的自媒體公號“咪蒙”2017年 11 月 13 日發表評論性質的文章《劉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兇手,但誰來制裁人性?》,而事件發生日期是2016年11月3日,中國留學生江歌被閨蜜劉鑫的前男友陳世峰用匕首殺害,雖然距案發已經歷時一年,新聞的時效性已過,按常規,在這瞬息萬變的時代,這件事早該被遺忘了,可是就在短短的幾天時間,這個事件在網上重新成為熱點。這是因為此篇文章以 “人性”為核心爭議點進行情緒渲染,一下激起了網民的情緒,加上許多媒體陸續地一系列報道而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大量網民不斷轉發、評論,形成網絡輿論并出現一邊倒的情況,出現輿論聚焦劉鑫而原本是重點的陳世峰被略有忽視。
從百度指數來看,從11月9日開始,江歌案的相關媒體發布量不斷上升,到11月14日達到第一次輿論頂峰38196條。
(二)網絡輿論第二次高潮期(2017年12月10日至2017年12月17日)
網絡輿論第二次高潮期正是“江歌案”開庭的當天,從百度指數看,在12月11日開庭當天達到第二次峰值85881條。網民們期盼了許久的江歌案終于開庭了,由于該事件已經在前期形成網絡輿論一邊倒的現象,人民網、新京報等官方主流媒體在開庭當天紛紛發布新聞和評論性文章《“江歌案”今日開庭 謎團即將解開》、《江歌案開庭,讓爭議回歸事實》等,表明理性的觀點:江歌引發的輿論討論,終究要在法庭上來解決;口水代替不了法律,沖動代替不了事實。以引導廣大網民回歸理性、直面事實。隨著客觀主流文章的不斷轉發與討論,百度指數顯示,從12月11日到12月17日,網民對該事件的熱度慢慢降溫,更多的態度是等待法院的審判結果。
(三)網絡輿論消退期(2017年12月20日至2017年12月26日)
從百度指數看,“江歌案”的消退期始于12月下旬,在12月20日審判結果公布的當天達到第三次峰值110759條后,輿論由高點漸漸滑落低處,公眾對輿論事件慢慢趨于理性,公眾的關注熱點開始向其他事件轉移。在 12 月26 日之后,公眾對于“江歌案”關鍵詞的搜索關注開始冷淡。
三、 江歌案的網絡輿情傳播特點分析
百度指數顯示,以“江歌案”為關鍵詞的文章出現的三次輿論高峰分別在2017年11月14日的38196條、12月11日的85881條、12月20日的峰值110759條。在清博數據中,三次輿論高峰與百度指數一致。在此次事件的輿論形成——爆發——消退的這段時期,網絡輿情傳播特點主要有:
(一)新媒體節點傳播占主流
節點傳播是指信息在節點之間以互動共享為特征進行的傳播行為,節點與網絡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它使得每一個網民以自我或者“群”的直接參與方式,被編織進傳播網絡中,每個人都是一個傳播節點[3]。節點傳播中每一個節點即是傳者又是受眾,人人都可以分享信息、表達觀點,正好促使普通網民進行意見的表達,由于節點數量的龐大,其傳播的影響力隨傳播節點幾何式擴散,可在極短的時間內引起巨大的關注度和熱議。
據清博數據統計分析,在此次事件的整個網絡輿論期間,從“江歌案”在媒體平臺的傳播熱度可以看出,微博排在第一達到62.74%,相關信息超過30萬條;其次是微信排在第二位超過8萬條,網頁和論壇均以超過4萬條的熱度排在第三和第四位,客戶端和今日頭條的熱度只有5千和4千余條,而報刊的數量最少只有200余條;從輿情走勢來看,微博的輿情也遠大于其它媒體;從情感走勢來看,負面情緒占主要領地,但負面情緒、正面情緒和中性情緒的波動變化情況是一致的。其傳播熱度、輿情走勢和情感走勢三者均成正相關關系。從以上數據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網民在微博、微信針對此次事件發聲的數量龐大,節點傳播的巨大傳播力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而客戶端和今日頭條由于受用戶數量等因素的影響,其傳播力遠不及微信和微博。
(二)標簽化傳播與情緒化傳播相互促進
在新媒體傳播中,常出現通過“貼標簽”來表達對事件及人物的認知和態度,標簽可以幫助人們對客體進行歸類,簡化認知過程,簡單省力也不用過多的思考,利于聚焦、擴大傳播。在該事件第一次網絡輿論熱潮中,關于人性善良的討論非常熱烈,在相關的關鍵詞中關于法律的文章最多,其次是關于政治與教育的文章,綜觀善良、法律、政治與教育,這四個標簽幾乎與大多數網民息息相關,因此可以引發廣大網民激烈地討論與互動。
從此次事件關鍵詞的傳播來看,以三個當事人為關鍵詞搜索時發現,他們在網絡的熱度排名為“江歌”第一、“劉鑫”第二、“陳世峰”第三。而從常理來看,在此次事件中,最重要的事情或最該盡快解決的事情是陳世峰的法律制裁,然而,網絡輿論表現出更多的是情緒化的觀點與討論,顯然不夠理性,同時,從相關話題的情感屬性來看,不論是微信、微博、還是網頁等網絡媒體中關于“江歌案”的負面情緒總是遠遠高于正面情緒和中性情緒。由此可以看出,網絡熱點事件中情緒化的傳播力大于事實本身的傳播力,而情緒化與標簽化的傳播合力更遠遠大于事實本身的傳播力。
(三)微傳播匯聚大力量
從傳播主體來看,本次事件中網絡輿論的傳播主體主要有兩方面,分別是以人民日報和新京報等為代表的官方主流媒體和以微博大 V 和廣大網民為主體的網絡新媒體、自媒體。在輿論形成的前期,大部分官方傳統媒體陷入沉默的時候,新京報在輿情爆發之初發布相關文章,成功地吸引了網民的注意。隨著網絡輿論愈演愈烈,新京報在 11 月 13 日連續刊發了三篇文章《江歌被害劉鑫無罪,法律無責下的道義追責》《劉鑫為懦弱和愚蠢付出了代價,但并非萬惡不赦》《江歌案 :殺氣騰騰的咪蒙制造了網絡暴力的新高潮》,但是,這一次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議程設置效果,反而使自身處于輿論漩渦的中心[4]。由于在當時的輿論下,廣大網民的態度呈現對劉鑫道德討伐的一邊倒、對受害者的同情和對兇手的譴責,而這三篇文章的基調與廣大網民對該事件的態度似乎相反或與網民的關注點相關性不高。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持某種觀點的人在一定范圍內達到 61.8%,就已經可以控制全局[5]。而根據清博數據,針對劉鑫的負面觀點比例,不少平臺已經接近甚至遠遠超過了這一數值,造成傳統主流媒體被倒逼的尷尬現象。
從微博、微信傳播中,綜觀整個過程,發聲最多的是從粉絲數為0~1000的自媒體和綜合影響力WCI為0~500的微信公眾平臺,而擁有超過1萬人粉絲數的大V和綜合影響力WCI越高的微信公眾平臺發聲的數量并不多,雖然普通網民的一次簡單關注、點擊、回帖等傳播效果都微乎其乎可忽略不計,但一旦在數量上快速聚集,就成為網民共同關注、參與、傳播并產生共鳴,小眾就擴張為大眾,在單位時間內信息發布量就越來越大,傳播速度越來越快,將對主流媒體及輿論走向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可以看出,當自媒體對同一件事件發聲積累到一定的數量后,將會引起大V的關注和更廣泛的網民關注,同時形成的互動趨勢會促使熱點事件的形成,從而影響輿情的走勢。
四、 關于熱點事件網絡輿論傳播的反思
大多數熱點事件可以總結出以下特征,微傳播匯聚大力量:即首先由普通網民在網上發聲引起關注,隨著關注數量的不斷快速增加,其很快形成網絡輿論。其次,標簽化傳播與情緒化傳播相互促進:即事件被貼標簽,用關鍵詞來傳播更能快速聚攏相同觀點的網民。再次,負面性的或帶有偏激情緒的評論性文章更能激起網民的共鳴。格蘭諾維特認為,強關系可以讓個體群聚起來升級為一個更強的群體,但是弱關系能使不同的群體匯集變成一個更大的群體。自媒體可以看作是兩者的結合體,其發布的內容能使信息廣泛到達,內容被轉發讓具有同一個話語的群體凝聚得更加穩固[6]。因此,網絡輿論的監測與引導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同時,媒體平臺特別是微博大V和綜合影響力WCI強大的公眾號平臺以及廣大網民的責任感與理性的態度成為影響網絡輿論的關鍵;最后,官方主流媒體應更及時、客觀的將事實公布于眾是防止輿論一邊倒的良藥。
參考文獻:
[1]陳力丹.輿論學——輿論導向與研究[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11.
[2]薛可,許桂蘋,趙袁軍.熱點事件中的網絡輿論:緣起、產生、內涵與層次研究[J].情報雜志, 2018(8).
[3]趙前衛,汪興和.微媒體輿情傳播特點[J].今傳媒,2017(12).
[4]陳力丹.關于輿論的基本理念[J].新聞大學,2012(5).
[5]章留斌,陳天明.從5W視角看“江歌案”中的網絡輿論[J].青年記者,2018(12).
[6]韋俞妃.自媒體環境下熱點事件的引爆與輿論導向分析[J].視聽,20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