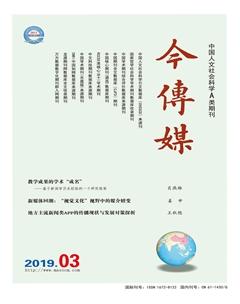試析蒲劇電影《棗兒謠》的敘事形態及鏡頭語言
馬澤
摘? 要:蒲劇作品《棗兒謠》,根據山西省運城市稷山縣吳城村村民吳伯宗的真實事跡改編。其于近年來逐漸開始登上戲劇舞臺,廣大觀眾均被劇中吳氏尋弟事跡所打動,使此劇一度廣受贊譽。2017年11月開機的蒲劇電影《棗兒謠》,融合了戲劇與電影兩種藝術形式的多種表達元素,最大限度地彰顯了戲劇電影獨有的藝術魅力和文化內涵。其中較值得觀眾注意的便是片中設置的敘事形態和運用的鏡頭語言。因此,該文將從電影語言學的相關理論出發,探析電影《棗兒謠》中獨具意味的敘事形態及鏡頭語言。
關鍵詞:電影《棗兒謠》;敘事形態;鏡頭語言
中圖分類號:J905?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3-0000-03
一.影片《棗兒謠》的敘事形態分析
戲劇電影《棗兒謠》是由沈聰執導,著名蒲劇表演藝術家王藝華、賈菊蘭領銜主演的戲劇電影。其與一般電影作品的不同之處在于:它是由蒲劇作品《棗兒謠》改編而來。該片將新型的電影表意手法與傳統的戲劇舞臺表演形式相結合,使影片結構更合理、人物形象更豐滿、矛盾沖突更集中、進而達到升華主題,以情感人的目的。片中講述了老大吳伯宗謹記母親臨終囑托,為尋找被人販子拐走的兩個兄弟,拋家舍妻,途徑十七省,歷時十八年,克服重重困難,憑著“棗兒”這一信物和《紅棗棗》這首童謠找到了兩個胞弟,但因一路歷盡艱險,身體受損,最終在全家團圓之時離開人世的故事。吳伯宗此舉感動了全村老小和大清皇帝,因而被封為“大清義民”,并賜其“兄弟孔懷”的御匾。
以下筆者將從賈磊磊的《電影語言學》對影片進行分析。我們應明確作者在書中根據敘事形態劃分出的常規電影與新電影,并非是嚴格意義上的,而是從宏觀維度對影片進行分類。諸如我們無法絕對地判斷某些影片究竟屬于哪種類型,只能從某些具體方面認為其更偏向于哪一類型。
在劇情體裁上,是否具有完整的故事、絲絲入扣的情節作為區分常規電影與新電影的重要特征。
影片講述了吳城村村民吳伯宗銘記母親臨終遺言,照顧兩個兄弟。后因弟弟伯祧逃學惹得先生生氣,嫂子棗香責打了他,兩個孩子因此跑遠,被人販子拐走。伯宗因此拋家棄業,歷時十八年,跑遍十七個省,一路沿街乞討,受盡風霜雨雪,惹得疾病纏身,終以付出生命為代價找到了兩個被拐胞弟。因伯宗深刻演繹了“弟子規,圣人訓。首孝悌,次謹信。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這一亙古不變的主題,死后被康熙帝封為“大清義民”,并被賜予“兄弟孔懷”的金匾的故事。可見,該片呈現了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且其是由同名蒲劇《棗兒謠》改編而來,在敘述內容上未經過多改動,只是將一些細節濃縮歸整,更適宜于當下觀眾接受和認可。這便奠定了影片敘事體裁與戲劇作品具有特定同構性的基礎,二者均具有起承轉合、環環相扣的敘事模式和曲折新奇、出乎意料的故事情節。因此,影片在劇情體裁上更近于常規電影類型。
在敘事結構上,環形(循環)封閉式與遞進開放式是區分常規電影與新電影的典型規律。
影片擁有一個起先是雙重線索、最終雙線融合的敘事結構。片子前半部分以伯宗和棗香各自的生活為兩條敘事線索,平行遞進,交叉敘述,在刻畫伯宗一路艱辛尋弟的同時,穿插了棗香養家帶孩子的不易境況。而后伯宗與棗香和歸來相遇,敘事線索由此合二為一。此外,劇中人物最初的生存狀態與最終的生活境遇相去甚遠,他們在復雜的社會歷史進程中處于一種變幻莫測、榮辱難卜的變數中:開片母親離世,五年后全家生活步入正軌,突然兩個胞弟的丟失為家庭帶來了巨變,片尾雖然一家人得以團圓,但伯宗的逝世又是這種“家庭大團圓”的一種缺失。此點可謂新電影敘事結構的重要特征。綜上,該片在敘事結構上更偏向于新電影類型。
在人物性格上,單一化、類型化與雙重化是區別常規電影與新電影人物性格應依循的普遍法則。
片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既有呈“圓型化”的,也有呈“扁平化”的。如:在筆者看來,伯宗的性格是呈“圓型化”的,因為我們既為他謹記母親遺言,照顧兄弟,失弟后歷經險阻尋找十八年而感動,又為他不聽妻子解釋,斷然認為兩個胞弟的丟失應歸咎于妻子而無奈。伯宗無疑是一個忠孝之人,但從他對家妻的態度上來說,并不能將其視作一個“忠孝之人”。且兒子歸來的出生和成長,他也未盡到一個父親應承擔的責任。也許劇作家對伯宗這個形象的設置受到了當時社會大環境的影響。此外,筆者認為棗香的性格屬于“扁平化”類型。她始終詮釋著一個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女性形象,家妻、大嫂、母親,三重身份映射下的賢良淑德、慈愛嚴格、無微不至。她忍辱生下吳門骨肉,完成了一個女人為家族傳宗接代的使命;又像男人一樣上山擔柴,養育孩子,盡到了母親的責任;還在得知伯祧在漠黑嶺后,無畏困難,毅然決然地領著歸來踏上尋弟之路。正可謂典型的賢妻良母之形象,卻又不失剛毅頑強之精神。除主要人物外,伯宗半路遇到的劫匪、漠黑嶺大人等次要人物形象均屬于“扁平化”性格。綜上,片中此種既有“圓型化”性格、又有“扁平化”性格的刻畫人物的手法,在展現新電影與常規電影兩種電影類型人物性格的完美結合的同時,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觀眾由片中一系列人物而引發的對現實人生的觀照和思考。
外在的、單向度沖突與內在的、多向度沖突是區分常規電影與新電影在矛盾設置方面的主要特征。人物群像與社會形態的兩極化描寫構成了前者矛盾沖突的性格和“社會基礎”;而人物內心本我與自我的對立沖突則使后者類型的矛盾得以表露。
影片在對矛盾沖突的設置上融合了外在的、單向度與內在的、多向度于一體。如片中的吳伯宗,演繹出了一個十八年一心尋弟的兄長角色,雖然途中多人勸他放棄尋找,他卻毫不動搖,這便在一定程度上與當時的社會和他人的思想觀念形成了一種“沖突”;他在自己幾近崩潰之時,眼前出現了母親的幻影,這也可作為該人物自身內在多向度沖突的力證,自我責怪與失望并存,殘酷現實與美好理想并存,筆者認為伯宗在心中實現了“本我”與“自我”的對立,“本我”指他內心尋弟的本能和無意識范疇的總和,“自我”則指控制和壓抑尋弟不成的這種與現實情況相悖的沖動。棗香,一個不折不扣的賢惠妻母形象,因遭他人挑唆,使伯宗認為兩個胞弟丟失的主要過錯在于棗香,這也可看作棗香與他人之間形成了一種“沖突”;她在伯宗離家舍妻后決定投河自盡,卻發現自己已懷有身孕,經過再三思想斗爭,為了使吳門血脈傳承下來,最終選擇放棄自盡,生下歸來。此處便完成了棗香“本我”與“自我”的對立。“本我”即為她想要投河自盡的本能和欲望在無意識范疇中的總和,“自我”則負責控制和壓抑她自盡的想法與懷有吳門血脈的現實相悖的本能沖動。以上兩個主要人物,兼具外在的、單向度沖突和內在的、多向度沖突的性格特點。
二.影片《棗兒謠》的鏡頭語言分析
影像是影片最基本、最核心的構成要素,是電影藝術存在的基石[1]。分析電影影像是電影藝術理論的第一要素。影像語言表述機制必須通過攝影機來完成,且由其產生的“鏡頭”是前者表達過程中的重中之重。
片中對鏡頭語言的使用,使影片整體的藝術感染力得到有力提升。下文將對片中出現的人物腳部特寫鏡頭和使用的疊化手法進行分析。
在筆者看來,片中四處特寫腳步鏡頭的場景均對影片的劇情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處特寫、移拍胞弟匆匆腳步的鏡頭,焦急地跑去告訴哥娘要去世了,這為接下來伯宗謹記母親遺言、之后義無反顧地尋弟作了伏筆;第二處特寫人販子拐走兩個胞弟后在莊稼地里匆忙奔跑的腳步鏡頭,直接交待了兩個弟弟被背走時的情節,也是片中故事發展的“原動力”;第三處是伯宗剛開始尋弟的場景,從他匆匆的步伐中既可看出尋弟心切的焦急之感,又能讀出渴望見弟的期待之情。且此時導演配以“尋弟……走晉,走陜,走冀,走甘。”的音樂,進一步渲染了伯宗尋弟之路的艱辛與困苦、堅定與無悔;第四處是在伯宗遭人敲詐踢打后,陷入絕望與掙扎中的他行走在大山里,此時導演從伯宗的腳部特寫移拍至他爬山時的大全景,鏡頭在展現伯宗瘦小身軀的同時,盡顯前路漫漫、孤獨無援。并配樂“尋弟,尋弟,尋弟……”,更將他堅毅的尋弟之心展現得淋漓盡致。
一般來說,影片后期制作中使用的疊化效果具有多種表意功能,如:表現明顯的空間轉換和時間過渡,強調前后段落或內容的的關聯性和自然過渡;表現時間的流逝;表現特殊視覺效果,營造氛圍,深化情緒等。且疊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加深作品戲劇化效果之功用,本片是一部戲劇電影,這便加深了影片使用疊化效果的合理性。以下我們將從片中四處場景分析其使用的疊化手法。
第一處:伯宗在尋找兩個胞弟的途中被敲詐踢打。這時大全景俯拍伯宗仰面躺在地上,落葉紛飛,后推拍至近景,展露其落魄之態。后疊化出兒時母親給他們兄弟三個唱“紅棗棗,甜棗棗,甜甜的棗兒哄寶寶。”的場景,又疊化回近景仰面躺在地上的伯宗,慢慢拉拍后疊化出村里人告訴他看到了外地大漢拐走了兩個孩子,繼續拉拍至伯宗起身,嘴里喊著:“伯祧,伯樂。兄弟。”此處疊化手法的作用是刻畫了伯宗當時的內心世界,使其憶起童年光景,想象胞弟被人拐走時的場景。也有表現伯宗在經歷敲詐后身心孤獨,神情渙散,由此憶起幼時生活,尋找慰藉之感的功用。
第二處:十五年后的伯宗容貌大變,攝像機俯拍伯宗大全景后疊化出其全景站在荒涼的舊屋前,道出自己十五年來走南闖北、向人討飯、睡牛羊圈的尋弟生活。伯宗越說越覺得凄慘,他拿起身上戴著的紅棗,剎那間母親出現。簡短的幾句對話后,娘消失,伯宗唱道:“娘臨終盼三棗長聚不散……”此處的疊化手法除表現了十五年時間的流逝、伯宗尋弟的不易外,更為接下來母親出現在眼前做了合理鋪墊。于筆者看來,母親的出現,實則為伯宗當時內心情感的外化表現。可見,疊化手法為此處母親出現的“虛幻化處理”奠定了基礎,使伯宗更加堅定了繼續尋弟的決心,劇情也得以順理成章地向前推進。
第三處:影片在接近尾聲時,全村人為伯宗的尋弟事跡而感動,攝像機俯拍加移拍大全景人們跪下悼念吳伯宗,后疊化出小時候伯宗打棗的那顆棗樹。此處的疊化手法可謂畫龍點睛之筆,同時也有著該棗樹見證了伯宗的一生、最終一切回到原點的意味。
第四處:片尾解說詞說道:“大清康熙帝封伯宗為大清義民。”,鏡頭俯拍大全景,全村人送別伯宗,疊化出康熙賜予其“兄弟孔懷”牌匾的全景。此處疊化出的牌匾具有總結全片、升華主題的功效。這四個字既是對兄弟情懷的歌頌,也是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
三.結語
沈聰導演將《棗兒謠》這部情真意切的蒲劇搬下了舞臺,搬上了熒幕。其塑造的敘事形態,使用的鏡頭語言均對日后戲劇電影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創作者在開創新型戲劇電影表達方式的同時,將當下觀眾的關注點重新拉回到優秀的戲劇藝術作品之中,對弘揚我國傳統藝術起到了不可小覷的作用。片中除使用了專業的藝術表現手法外,其滲透出的感人至深的兄弟情誼,緊扣觀眾心弦,令人久久難以忘懷。
參考文獻:
[1] 賈磊磊.電影語言學導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44.
[2] 李顯杰.電影敘事學理論和實例[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
[3] 張昆昆.一曲“棗兒謠”撼心扉——論蒲劇《棗兒謠》的成功之處[J].戰友,20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