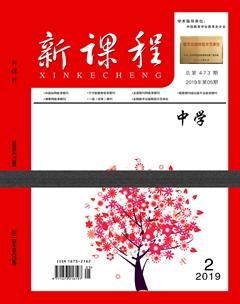大地的光澤
潘藤月
摘 要:從生命和存在之光;思想和時間之光;飛行的光和大海的光;世界的血和世界的光;哀傷和美麗之光;使命和自我之光;故鄉和原鄉之光七個方面論述駱一禾的詩集《世界的血》。并將其升華為“大地的光澤”。充分肯定了駱一禾詩集《世界的血》在當代詩歌史上的獨特地位。突顯了詩人將自己的身體乃至靈魂,融入大地,并用詩歌擁抱光明的情懷。
關鍵詞:大地;折射;靈魂;光亮
駱一禾的詩集《世界的血》,歷經歲月磨礪而愈顯璀璨。詩歌評論家西渡在其詩評專著《壯烈風景》中說:“博大生命是駱一禾的生命理想。長詩《世界的血》是駱一禾向博大生命發起的集中沖擊”。詩人陳東東在其專論中更是給予《世界的血》群山之高峰的評價,認為“是中國自有新詩運動以來的第一部真正的抒情史詩”。
《世界的血》是大地光澤的深層映射。其中許多詩行讓生命、讓存在、讓思想、讓時間都具有光澤。
一、生命和存在之光
請看《世界的血》里面的一些詩行:
“在古城上空/青天巨藍/豐碩/像是一種神明/一種切開的肉體/一種平靜的門/蘊含著我眺望它時/所寄寓的痛苦/我所敬愛的人在勞作/在婚娶/在溺水/在創作/埋入溫熱的灰燼/只需一場暴雨/他們遙遠的路程就消失了”(見靈魂)
詩人用一幅幅立體的畫面展現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歡怡與痛苦。
大海、人民、天堂、麥地滾動,這看似孤立但又相連的意象組合透出了詩人的大愛情愫。
“我的血漿在熱烈的絲帕上向外噴射/我的心房在河面上激流滾滾/在天上的光芒四射/在地上的熱烈可親”(久唱)。
這里的我既是詩人也是大地河流,也是所有生命。大地、河流、生命和詩人自己都已溶解于光芒中。
二、思想和時間之光
請看詩章《黑豹》:風中/我看到一副爪子/是/黑豹長在土中/站在土里/一副爪子/摁著飛走的泥土/是樹根是/黑豹/泥土濕潤/是最后一種觸覺/是潛在烏木上的黑豹/是/一路平安的玄子/捆綁在暴力身上/是它的眼睛諦視著晶瑩的武器/邪惡的反光/將它暴露在中心地帶/無數裝備的目的在于黑豹/我們無辜的平安/沒有根據/是/黑豹/是泥土埋在黑豹的影子/然后/影饒著影子/天空是一座苦役場/四個方向/里我撞入雷霆/咽下真空/吞噬著真空/是真空里的煤礦/是凜冽/是背上插滿寒光/是曬干的陽光/是曬透的陽光/是大地的復仇/像野獸一樣動人/是黑豹/是我堆滿糧食血泊的豹子內部/是我寂靜的/肺腑。
黑色是宗教和思想的顏色,西方傳教士服飾的顏色,東方哲學中的“玄之又玄”與“天地玄黃”,史蒂文斯的“觀察黑鳥的十三種方式”,都賦予了黑色極高的地位。黑色閃耀著思想之光。而駱一禾捕捉的黑色是一匹靈動的豹子。是空中的一副爪子。是曬干的陽光。是撞入雷霆和咽下真空。而時間顯示的力量卻像一場雨,沖刷著莊稼和鋼。卻是大隊的猛獸踏遍水兩岸的平原和五千年明亮的文字。
三、飛行的光和大海的光
駱一禾的詩集《世界的血》主要由“飛行”“大海”和“屋宇”三個部分組成。它們是駱一禾詩歌的精華。“飛行”隱含自由。“大海”隱含遼闊。“屋宇”隱含蒼涼。
我們在詩句中能感受到詩人思想的深邃,情感的摯熱,心靈的敏感以及對生命、對大地、對光明的深愛。
“水在大塊地潮濕/永動者坐在世界的心里/而陸地這陸地/這岸/這莊嚴的黑暗與光明”。
這些由心靈深處和靈魂深處噴薄而出的語詞讓人升發無限遐想。
四、世界的血和世界的光
世界的血即是世界的光,這是我與駱一禾詩歌對話時最深的感受。當然,駱一禾詩歌所呈現的讓人如醉如癡的壯麗之美,讓人手舞足蹈的玄幻之美和讓人情感激越的音韻之美,也在我的內心掀起狂風巨浪。
“你要在大自然中飛行/飛行是加上命運的速度/你要飛行于靈魂/飛向黑暗的斧子”。(大海)
“河流在光閃閃地奔跑/大地在光閃閃地奔跑/……它的門窗對開/……生活穿過/和平神祗璇舞而過/……謊言之王殺死了天下之王/高高的山頂布滿灰燼”。(屋宇)
我在這些鮮活的詩句中沐浴大地的光澤!駱一禾和他的《世界的血》,以生命為美!以光明為美!以力量為美!
五、哀傷和美麗之光
哀傷和美麗天衣無縫的交集是駱一禾詩集《世界的血》以及駱一禾自身的生命軌跡的重要特質。生命對于人的告誡與指引是無聲的,它僅在人行走在無關緊要的路上而生發的空虛中顯露些許的端倪。而我在此不得不高聲贊美詩人們的敏感:他們在為生命的由來而疑惑,在為生命的使命而顫抖,在為生命的故鄉而永懷哀傷。
駱一禾生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于河南農村的淮河平原上度過的他的童年。在改革開放的后一年即1979年考入了中國文學學習的圣地——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在那樣的背景下,駱一禾更加珍視敬畏生命,更加強調追求和平,追求明亮。因而他向自己,向華夏大地乃至全體人類投射了生命更為宏大的目標。
而在中國文學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就讀,知遇恩師、著名詩歌評論家謝冕,與海子等詩人惺惺相惜,以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思想解放的大潮涌動等,也使駱一禾更快地脫離時代矇昧的阻隔與地域狹窄的目光。
他的詩歌注重具象、意象、意境的構筑,每個意境間看似分離卻又表達著相合的情緒,東方和西方交融,古代與現代交融,現實與夢幻交融,理性和非理性交觸,力量與深刻并存,美麗與哀傷
并存。
六、使命和自我之光
駱一禾是一個一生都活在他的詩中的人,因而他一生都在憂郁——他有著對生命使命的永恒追尋;因而他一生都在歡喜——他有著對生命占有者的美現世的欣賞。
駱一禾通過他的詩論《美神》,表達了他作為生命的占有者對生命的無上尊重。
他說:“在這篇題為‘美神的詩論里,我所要說的并不是我自己或我自己的詩,而是情感本體論的生命哲學。因為我清明地意識到:當我寫詩的創造活動淹沒了我的時候,我是個藝術家,一旦這個動作停止,我便完全地不是。也就是說,生命是一個大于‘我的存在,或者說,生命就是這樣的生成。”
他認為人的一生是生來就有使命有待完成的,而“人”是踐行這個使命的主體,只有行走在各不相同的、通向這一使命的路上的時候,我才成為了“我”。而這也透出詩人面對世界的恭謙與面對每一個生命個體的尊重。他說:“我鄙棄那種詩人的自大意識和大師的自命不凡,在這兩者之中——含有雙重的毒素,它戕害了生命的滋長、壯大和完美。”
縱觀世界詩壇,每一首優秀的詩作,都有著鮮明的作者風格,突出的時代特色,與深厚的民族底蘊。而每一首優秀詩作的背后,都潛伏著一種博大的鄉愁——“我們這些大地上的人們都曾經衷心地感覺到這樣的痛苦,眼望著家鄉”。
駱一禾作為生命使命最偉大的追求者之一,有著急切地想承載使命的興奮,有著對生命前路與生命故鄉的幻想,和對完成使命后僅余留下寂寞與空虛的至深恐懼。
何為生命的使命?尋找生命的原鄉。
如何去尋?我們能夠,也只能夠通過生命來達到生命的原鄉。
如何讓自己的“生命”流露?人的一切在參與詩與美神的熔鑄之前,都只屬于柵欄中的自我。
七、故鄉和原鄉之光
《世界的血》,許多詩篇仿佛具有生命,具有靈魂。詩篇的身體流動鮮活的血液。它讓人想到屈原的《離騷》,想到意大利詩人但丁的《神曲》。屈原在《離騷》中說:“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亦余心之所向兮,雖九死尤未悔。”但丁在《神曲》中說:“地獄的颶風吹刮不已/用狂暴的威力鞭戳靈魂。”
他的許多詞語會讓人想到辛疾疾“郁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的悲涼;想到陸游“一千五百年間事,惟有灘聲似舊時”的寂寥;想到博爾赫斯的“死亡是活過的生命,生命是在路上的
死亡。”
但其中的一個透徹靈魂的基調,卻是在表達對生命原鄉的追求止步于彼的遺憾。長詩《飛行》中他將自己幻化為生命本身,使一人與他并肩飛行,看承載他的占有者的無盡而無盡美的起落。他將所有的個體都看作泥土,而又對每一捧泥土都一往情深。他因離自己的故鄉愈來愈近而欣喜若狂,又因那仿佛無盡的距離而扼腕無言。對于在追尋原鄉路上離去的占有者,他會獎勵他們一個夢——他們將夢到自己對原鄉的幻想,以遮蓋自己的抱憾永恒。
在這尋鄉的路上,生不是歸程的終點,死更不是——它是每一個尋找原鄉的人最后的贊嘆,是每一個生命的占有者迸發出的卑微的火,是披滿金銀枷鎖的行者落入嶙峋輪回的笑,是生命對生命最真切的膜拜與臣服,是穿越有質量的時間輕啟的呢喃:“何處是故鄉?”
而他詩中的一切意象的善惡又如此鮮明。對于那些生命所象征的與追求生命的,他毫不吝惜他的贊美,對于那些有悖于生命的,他也決不掩飾他的憎惡。他不畏懼人的輪回反復,他不畏懼死亡,不畏懼華夏大地和人類歷史上的至暗時刻,也不畏懼和生命原鄉幾欲不可及的距離。
參考文獻:
[1]西渡.壯烈風景[M].中國社會出版社,2012-12.
[2]陳東東.我們時代的詩人[M].東方出版社中心,2017-07.
[3]博爾赫斯.博爾赫斯文集[M].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11.
[4]史蒂文斯.史蒂文斯詩選[M].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
編輯 李燁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