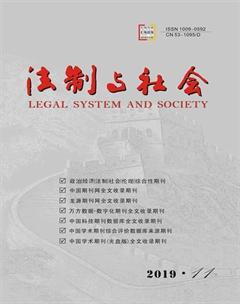京津冀知識產權糾紛調解機制的理念協同
趙民興
關鍵詞京津冀 知識產權 糾紛 調解 協同發展
2015年《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實施以來,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高度重視推動了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機制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協同發展。最高人民法院相繼出臺的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中不斷提升三地知識產權案件管轄和審判的協同程度。與知識產權糾紛訴訟解決機制協同發展的積極態勢相比,以調解為代表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協同發展明顯滯后。本文分析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對知識產權糾紛商事調解的發展提出建議。本文認為知識產權糾紛調解機制的協同發展需要以服務京津冀協同創新的理念為指引,逐步淡化調解中的公權力色彩,逐漸回歸到當事人自我管理糾紛解決的自治模式,用理念的協同實現知識產權糾紛調解機制的協同發展。
一、人民調解的協同發展
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實施以來,京津冀三地都已經開始嘗試設立專業性比較強的人民調解組織來解決知識產權糾紛。三地也相繼出臺了規范知識產權糾紛調解的相關規定。不可否認,三地知識產權人民調解組織的專業化建設和相關政策措施的出臺對于協同發展都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到目前為止三地人民調解組織還無法實現跨區域的機構設置,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也都沒有出臺關于人民調解協同發展的政策措施。除了三地對知識產權人民調解協同發展的認識水平和重視程度等因素外,人民調解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結構性問題也影響了協同發展。
按照行政區劃設置的人民調解組織限制了協同發展。《人民調解法》規定由各地依法設立的人民調解委員會負責開展調解活動。這種按照行政區劃設置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制度安排主要是為了方便人民調解化解當地的婚姻家庭糾紛和鄰里糾紛。制度設計的初衷并不是用來解決其他地方的矛盾沖突。因此,《人民調解法》并未對跨區域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設置作出相應規定。當然,《人民調解法》也沒有限制跨區域人民調解。有些省份就涉及省際邊界地區糾紛進行了人民調解跨省聯動的有益嘗試。比如,2007年泛珠三角九省區司法廳共同簽署的《泛珠三角九省(區)省際邊界人民調解協作聯調協議》。2009年川滇黔渝陜甘青藏八省市區的司法行政機關簽訂的八省市區邊界人民調解聯調協作協議書。2016年四川、陜西、甘肅三省五市司法行政機關簽署的《川陜甘三省五市司法行政工作區域合作框架協議》。知識產權糾紛雖然與上述跨區域人民調解所要解決的糾紛性質不盡相同,但是人民調解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也可以參照其他地區的實踐嘗試,設立跨區域的專門知識產權糾紛調解組織以便適應新的發展要求。目前京津冀協同發展并未涉及到行政體制的改革,人民調解組織的跨區域設置要比最高人民法院推進知識產權法院跨區域的案件管轄和審判難度大。司法部作為人民調解的業務指導部門出臺的司法行政工作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意見中并未明確提到人民調解的協同發展問題。這種制度創新涉及到司法行政體制的改革問題,不是三地政府的簡單合作就能解決的。
人民調解主要用來解決民間糾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定位與調解知識產權糾紛的目標不完全符合。《人民調解法》第一條規定:“為了完善人民調解制度,規范人民調解活動,及時解決民間糾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雖然《人民調解法》并未明確民間糾紛的具體含義,但是從《人民調解法》對調解程序的規定可以看出民間糾紛指的主要是婚姻家庭糾紛和鄰里糾紛。《人民調解法》對人民調解是否適用于知識產權等專業性質的糾紛并未作出具體規定。從相關條文的規定可以看出《人民調解法》并不限制人民調解在專業糾紛上的適用。《人民調解法》第二十條規定:“人民調解員根據調解糾紛的需要,在征得當事人的同意后,可以邀請當事人的親屬、鄰里、同事等參與調解,也可以邀請具有專門知識、特定經驗的人員或者有關社會組織的人員參與調解。”這里說的“邀請具有專門知識、特定經驗的人員或者有關社會組織的人員參與調解”可以理解為人民調解在知識產權糾紛上適用的法律依據。盡管京津冀三地已經開展人民調解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實踐,《人民調解法》對糾紛類型的模糊規定還是會影響人民調解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效果。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知識產權糾紛基本上不會涉及社會和諧穩定的問題。在適用人民調解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時候應更多從知識產權行業發展的角度考慮問題。只有從知識產權專業的角度進行制度創新才能有效實現糾紛解決機制協同發展的目標。
人民調解制度所透射出來的“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與協同發展所需要的基于當事人自治的糾紛解決方式還有一定差距。從《人民調解法》對調解組織設立、調解員選任和調解程序的規定中隱含的行政性就可以看出人民調解不是完全基于當事人自治的糾紛解決方式。各地建設的調解知識產權糾紛的專業性調解機構也很難完全貫徹當事人自治的原則來調解糾紛。協同發展的目標是為當事人創造一個主動使用人民調解來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法治環境。如果人民調解不能淡化公權力色彩的話,人民調解就很難成為糾紛當事人的主動選擇。因此,在知識產權糾紛調解機制協同發展問題上,人民調解只有全面回歸當事人自治原則才能更有效的解決知識產權糾紛。
人民調解的協同發展必須適應知識產權糾紛的特點才能實現協同發展。沒有制度上的突破和理念上的提升,人民調解制度不僅無法在知識產權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構建過程中發揮作用,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還會影響其他糾紛調解方式的發展。
二、行政調解的協同發展
作為一種獨立的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方式,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部門提供的行政調解的協同發展也同樣面臨行政壁壘的限制和調解理念落后的影響。首先,與人民調解一樣,知識產權管理部門負責行政調解的制度設計決定了行政調解的協同發展也要受行政區劃的限制。在目前京津冀三地知識產權部門各自負責本地區行政調解的情況下,協同發展的問題有賴于國家知識產權管理部門的推動和三地知識產權政策措施的協同發展。其次,三地行政調解機構對行政調解性質和調解理念的認識也會影響協同發展。行政調解解決的是涉及知識產權的民事糾紛。《專利法》第六十條規定“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應當事人的請求,可以就侵犯專利權的賠償數額進行調解”。由行政部門負責知識產權糾紛調解難免帶有公權力色彩。從理論上來看,知識產權糾紛行政調解是知識產權行政部門為糾紛當事人提供的一種公共服務。如果知識產權行政調解能夠實現何煉紅教授主張的行政調解從權力型模式向服務型模式的轉型,那么行政調解在京津冀三地的協同發展就會較少受到公權力的影響。因此,行政調解的協同發展有賴于知識產權行政機關從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再次,在行政調解向公共服務轉型發展的過程中,負責調解知識產權糾紛的行政部門應最大程度貫徹糾紛當事人對糾紛自我管理的自治理念。唯有如此,才能在不打破行政壁壘的情況下實現糾紛調解機制的協同發展。
三、司法調解的協同發展
法院主導的司法調解與其他調解形式的協同發展聯系緊密。首先,法院在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過程中需要借助其他調解形式。從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無論是知識產權案件的訴前調解還是訴中調解,審理案件的法院基本上是邀請專業性人民調解或者商事調解組織來參與調解。法院對非訴訟調解機制的借助說明在協同發展的問題上人民調解或者商事調解等調解形式的發展會影響司法調解的協同。同時,人民調解等調解形式的協同發展在減少知識產權訴訟方面也能發揮一定作用。其次,司法調解的協同發展會隨著知識產權案件跨區域管轄和審理的發展而發展。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在京津冀的高度協同發展能夠帶來人民調解等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在訴訟過程中協同適用。在知識產權糾紛主要以訴訟解決的情況下,法院主導的調解對于促進非訴訟調解機制的協同發展有積極意義。這種協同發展也許不是其他調解形式的主動行為,但是卻能取得其他調解形式協同發展意想不到的效果。司法權威下的調解活動與當事人在訴訟外主動尋求糾紛調解的效果不會一樣。這也說明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發展無法擺脫以訴訟為核心的制度安排。真正意義上的非訴訟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也只有在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充分發展的前提下才能實現。再次,司法調解也必須堅持糾紛當事人對糾紛自我管理的自治理念。司法調解與其他調解形式的互動關系必須基于當事人自治的理念才能有助于司法調解的協同發展。
四、商事調解的協同發展
當前關于知識產權糾紛的理論研究和糾紛解決實踐都基本上集中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上,較少重視和研究分析商事調解的功能與作用。這一方面與我國商事調解制度的不夠完善有關,另一方面也在于糾紛當事人更加青睞有行政權力和司法權威為背景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與上述三種有公權力內涵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相比,商事調解顯得不是很正式。目前我國還沒有關于商事調解的專門立法,現有的商事調解組織規模還比較小,調解的糾紛范圍也比較有限。然而,正是這種不正式才是調解這種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魅力所在。雖然不是所有涉及知識產權的糾紛都可以歸入商事糾紛的范圍,但是商事調解完全可以成為調解知識產權糾紛的選擇。與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相比,商事調解較少依賴行政權力和司法權威,能夠在更高程度上實現當事人自治的調解理念。2019年8月7日,我國簽署了《聯合國關于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又名《新加坡調解公約》)。我國加入國際調解公約對于我國按照當事人自治的調解理念來制定商事調解法律和推動知識產權糾紛商事調解的發展都有重要意義。商事調解完全可以利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時機實現跨越式發展。
五、結語
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實施對知識產權糾紛的解決提出了新的挑戰,也為糾紛解決機制的協同發展提供了制度創新空間。制度的創新不光需要體制改革,更重要的是需要理念的更新。調解這種當事人自我管理糾紛解決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具有超越京津冀協同發展行政體制限制的理念優勢。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和商事調解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只有全面回歸當事人自治的糾紛解決理念才能在更大范圍更大程度上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