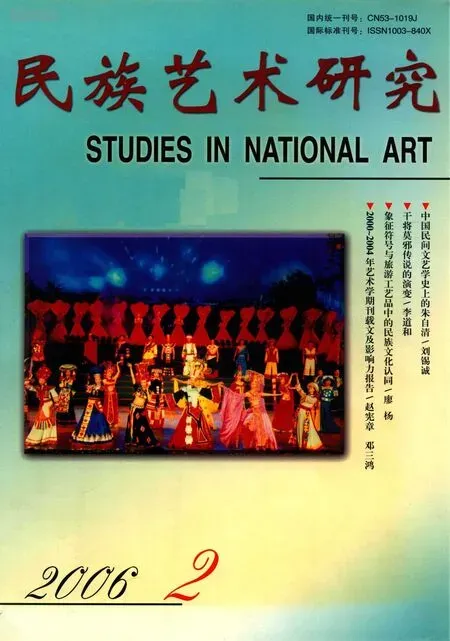確立中國民族音樂學深耕研究意識與內涵
馬琦玥
如果追問中國當前的民族音樂學研究存在什么問題?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民族音樂學的深耕研究意識”不夠,其直接反映在民族音樂學研究中的“兩張皮”問題,從而導致學科學理體系的建構力度與學科知識體系的完善度不夠。
美國著名民族音樂學家恩克蒂亞(J.H.Kwabena Nketia,1921-2010)于1984年在中國音樂學院做民族音樂學系列講座時,提出了民族音樂學研究存在認識與行為分離的“兩張皮”問題,這是目前已知論及民族音樂學領域“兩張皮”問題的較早文獻。盡管恩克蒂亞所論“兩張皮”的問題,主要是針對音樂與之根植的文化的關系而言[注]沈洽:《描寫音樂形態學引論(自序)》,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5年版。。但是,如果將“兩張皮”問題作為一個審視指標來綜觀整個民族音樂學的研究狀態,可以說,從20世紀80年代提出“兩張皮”問題到當下,在近40年的學術研究變遷中,該問題一直都還突出地存在著。在筆者看來,導致這種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研究個體或群體欠缺學科深耕研究的意識、觀念與作為。本文所論是本著探究和進一步清晰與建構中國民族音樂學知識理論話語體系之理想,著力將“兩張皮”問題聚焦于“音樂事象”與“理論闡釋”之間,以自己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間在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田野工作為案例,從“民族音樂學深耕研究意識提出的邏輯前提”“民族音樂學深耕研究意識的內涵”兩個方面,主張和論析用“深耕研究”解決民族音樂學研究中“兩張皮”的問題。
一、民族音樂學深耕研究意識提出的邏輯前提
提出確立“民族音樂學深耕研究意識”主張的邏輯前提,是訴求解決中國民族音樂學研究中“音樂事象”與“理論闡釋”呈現出的“兩張皮”問題。所謂兩張皮,是指甲與乙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未達到融合一體式的存在狀態。如:常說的“理論”與“實踐”脫節之類的兩張皮問題。在筆者的學習過往與觀察思考研究中發現,不少的研究者時常困惑、牽絆于“對音樂事象進行觀察、分析”與“對音樂事象進行理論闡釋”的關系連接中,二者經常表現出“貌合神離”的狀態。究其問題的實質是出現在“田野作業”和“理論認知”兩個核心維度上。總之,民族音樂學研究中突出的“兩張皮”問題,就是彼此互融性差的問題,且在多個方面存在著。
(一)民族音樂學田野作業不到位
民族音樂學田野作業“不到位”之論,是相對于“到位”而言的。“到位”的民族音樂學田野作業,是既能發掘出存在的深度事實信息,又能揭示和闡釋出存在的深度意義。
田野作業是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基石,無論是在民族音樂學的教學還是實踐中,它的重要性都是被反復強調的。在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nowski,1884-1942)出版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后,“較長時間的實地生活+掌握當地語言”成為“科學的”民族志寫作的基礎以及人類學田野作業的必要條件,對于與人類學/民族學有著深厚淵源的民族音樂學來說,這樣的要求也成為必須遵守的規則。但即便如此,民族音樂學田野作業依然表現出“不到位”的現狀,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 欠缺田野作業的“深度”
如果凡事僅在平面維度活動,深度意義的揭示總是會有限的。民族音樂學田野作業的邏輯起點與目標,就在于謀求“深度清楚事實信息”與“深度發現存在意義”。雖然對“民族音樂學”的界定在業界依舊沒有達成統一共識,研究者的研究邊界、內容、方法、視角、立場等各有側重,但民族音樂學研究音樂與整體文化之間的關系,探究該文化中的音樂觀念以及音樂的生成邏輯之信念是一致的。“關系”“觀念”“邏輯”一系列具有哲理性的高度抽象、凝練的內涵,就決定了達成這一任務的手段不可能是“浮皮潦草”“蜻蜓點水”的,而是吃透“深度”二字才能完成的。在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專業(或研究方向)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培養方案中,田野作業必須達到1年時間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共識,即便沒有達到1年時間,也會以“較長時間”作為要求。除此之外,研究者與當地人的田野關系似乎也成為檢驗田野作業是否到位的重要評判標準,如果在二者交往過程中出現如美國民族音學家內特爾(Bruno Nettle,1930-)所說的“下周二回來找我”這樣的被受訪者委婉拒絕你采訪的情景[注][美]布魯諾·內特爾:《民族音樂學研究:31個論題和概念》,聞涵卿 等譯,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頁。,基本可以說明田野工作關系的經營有待加強。誠然,在田野作業中也不乏這樣的現象:研究者田野時間足夠長,懂得當地語言,并且與當地人保持了良好的關系。在此之上,研究者掌握了足夠多的地方性知識,能夠說出一籮筐的田野趣事,但在檢視研究者田野作業之最終成果時,卻發現研究者并未提出和解決專業領域的真問題,只是停留在“淺描”方面,無法進入到存在或事物的核心層。可見,時間、語言、田野關系雖然是保證田野作業質量的重要條件,但這些因素并不能等同于田野作業的深入程度。研究者需要在這些因素基礎上,以專業的視角去發現散落在“田野”中的專業問題,并且用專業的方法予以解決。可見,這在學理上與實踐上都要求研究者自己必須具有獨立的“深耕研究意識”。
2. 欠缺田野作業“規格”
凡人類行為皆有自己的前提性與限制性規范。民族音樂學的田野工作也不能丟失自身行為的內在規格依據。
對于很多研究者,尤其是民族音樂學的入門者而言,田野作業通常是“跟著感覺走”的經驗性活動。當自己懷揣著激動、緊張、興奮、忐忑的心情走入田野,懵懵懂懂且認真地開始所謂的田野作業后,時常發現不僅在田野作業結束后,甚至是在田野過程中自己就會感覺到:田野中進行錄音、錄像、拍照等操作時會手忙腳亂;面對一個場景時不能對所應進行的操作進行準確判斷;音樂活動結束后,突然發現記錄過程中遺漏了某個重要環節或者信息;回到案頭工作需要調取某個信息數據時,發現在茫茫數據庫中無從下手尋找;在對調查進行文本寫作時發現所拍攝的圖片、錄像均達不到學術規范或是出版規格要求……面對這些問題,自己可以將其歸結為“經驗不夠”。但從根本上來說,這是由于田野作業過于依賴“經驗”,而忽視了能夠讓這一切變得井然有序的、基于一定學理引領的規格性技術路線的學術訓練。所以,深耕研究需要依循研究規格的推進。
(二)理論認知不到位
筆者所言“理論認知不到位”的狀態,主要出現在民族音樂學學習者群體中。這里的“理論”既包括既有的民族音樂學理論,也包括其他學科中的既有理論。“認知”既包括對理論本身內涵的認知,也包括對理論價值所在的認知。
1.對理論內容認知不夠深入
每一個專業理論,都有自在的本質內核意義指向與功能范圍,否則就不需要創生新的理論了。在當下民族音樂學研究或者教學中,對于理論與方法的學習確實擺放在了相對重要的位置。幾乎我國每一所設有“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專業或者研究方向的藝術院校都會開設“民族音樂學理論與方法”課程。從民族音樂學產生之初到今天的不同階段,民族音樂學的相關理論和方法論,以及對民族音樂學產生過影響或者正在產生影響的人類學、民族學或其他學科相關理論,都是學習者必修和要了解的基礎性專業內容,是武裝自身學養的學理知識。此外,研究者還會在各自研究中,主動“遠距離”跨學科地尋找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領域的理論來運用。然而,在現實中不僅“理論的應用”出了問題,根本的是在出發時對“理論的認知”就出了狀況,所以才持續出現了類似“我知道有那么多理論,可是怎么用啊?怎么才能用理論來說明問題,而不是淪為證明理論正確的材料?”這樣的疑問和困惑在學習者中卻并非個案。深究其原因就在于學習者對這些理論的認知程度僅停留在皮毛層面而已,以至于將某一理論的體系性學理知識僅僅簡化為一個只有空殼的概念或術語來運用。
2.對理論價值認知不夠深入
有研究者認為,在以田野作業為學科基石的專業面前,如果重視了或大談理論、概念有違專業精神,是一種學風浮躁或研究“不實在”的表現。此種認知結論,對專業而言至少是一種不周全的認識。在此類認知的指導下,有的研究者會更容易出現故步自封或者沉浸于田野資料的收集和“展示”中。例如,在碩博士學位論文答辯環節經常會有專家指著“結論”部分問答辯者:“說了這么多,你的結論究竟是什么,你的觀點是什么?”。也就是說,一些研究者的論文,很容易成為一種材料的堆積,而缺少從材料中揭示、抽離和概括界論出個人獨立見解及結論的意識與能力。很多研究都只是將資料停留在平面化階段,沒有獨立找到自己研究的學理支點、意義立場、立體性建構成型結果。論文“結論”的寫作都是如此,那么,訴求主動尋求學理上的支持或者在個人研究中提升出一個自己的專業理論則更是難上加難了。
總之,民族音樂學學科中研究個人或群體謀求有獨立價值創建性研究,不能缺失“民族音樂學深耕研究意識”這個指導思想。
二、民族音樂學深耕研究意識的內涵
中國當前的民族音樂學研究需要在認識論上確立“深耕研究意識”這個觀念,尤其落實到具體解決“音樂事象”與“理論闡釋”的關系問題上,更是需要確立“民族音樂學深耕研究意識”。
“深耕”,原本是農業范疇的術語,指的是有深度的耕與種。也就是農民種田的良好收成,是依賴對泥土不斷向下翻弄與經營獲得的。這里將“深耕”一詞借用到民族音樂學研究中,作為一種推進專業研究深入的研究意識來強調與實踐,是有現實性與學理意義的。深耕研究意識,是指研究者基于已有研究狀態進行進深性求真學術覺察反映。所謂民族音樂學深耕研究意識,是指民族音樂學研究者基于對被研究對象一般事項層級探究的基礎上進行的進深性求真學術覺察反映。也就是說,民族音樂學的學術研究,應該是一種持續的、新舊知識反復交融、不斷深入推進與揭示意義性結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將學術思維進行縱深發展和拓展,以越來越接近事物的內核,直到揭示出了真知。對于民族音樂學而言,“事物之內核”也就是民族音樂學研究訴求的最終目標——研究音樂表征與深層社會及其文化的關聯。其解決途徑是解決“理論認知”與“田野作業”與二者融和一體的問題。針對這一核心關系問題的解決,筆者提出“民族音樂學深耕研究意識”的“理論深耕”與“實踐深耕”兩個維度,是為著力解決“兩張皮”問題提供的另一種思路。
(一)實踐深耕
“實踐深耕”的最終落腳點就在田野作業的過程中,其內涵是筆者結合個人學習及田野作業中的反思和希冀提出的。這里的“田野作業”是真正人類學意義上的田野作業,而非泛化的田野作業概念。民族音樂學者的“田野”可以處處皆是,但是田野≠田野作業。比如,參與一場會議或者演出活動,可以被視為“田野”,但并不是參與了相關活動就代表著進行了田野作業。
什么才是田野作業?對田野作業的定義也是多樣的,隨著學科和學術氛圍與思潮的向前推進,對于田野作業的理解也在不斷變化著。《民族音樂學導論》中引用了Everett Hughes(1897-1983)的定義:“觀察處在原地的人,即在他們自己的地方發現他們,以某種他們可以接受的角色與他們待在一起;即允許親近地觀察他們的某些行為,并允許用有益于社會科學、不傷害被觀察者的方法來報告自己的觀察”[注][美] 海倫·邁爾斯:《民族音樂學導論》,秦展聞、湯亞汀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4版,第30頁。。而《民族志:步步深入》中說:“田野作業是所有民族志研究設計最具特色的要素……田野作業是在自然中探險”。該作者將田野作業分為基本知識儲備期、綜合觀察期、后綜觀階段等階段[注][美]費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龔建華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3版,第9頁。,更是把民族志學者比喻為人型機器,認為田野作業是“腦中帶著研究問題、社會交往或行為的理論以及各種概念性指導方針……大步走進某種文化或社會情景中去探究其文化形態,搜集和分析資料……穿越個體性觀察的荒野,對構成某個社會情景的紛繁蕪雜的事件和行為進行準確的識別及分類”[注][美]費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龔建華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3版,第37頁。。這段描述是從民族音樂學者的任務的角度闡釋田野作業是什么的問題。最本質地講,田野作業是研究者對被研究存在之所見事實信息與非所見意義信息的敏覺捕獲行為。從總體和系統的立場看,可以簡略地將田野作業分為:進入田野前、進入田野、從田野中抽離三個階段,三者在整體上構成一個完整的田野作業。每個階段都有自己的核心任務,其目的都是達到實踐的“深耕”,以解決田野作業“深度”欠缺的問題。下面以“關鍵主題詞”解析的方式,力圖在揭示田野各階段主旨內涵的過程中,推進達成“實踐深耕”的研究目標。
1.進入田野前的關鍵詞——“解題”
“解題”是田野作業前期準備階段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中國音樂學院的趙塔里木教授就一直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范本向研究生講解并進行訓練。解題≠讀書筆記,“讀書筆記”強調的是記錄讀書過程中的心得體會或者是將精彩的部分進行摘抄;“解題”除了對文獻作者和內容的準確、簡要的概括外,更重要的是需要閱讀者自己對文獻的重要觀點進行提煉、歸納以及評論。解題篇數越多,閱讀者越能夠將其中的問題進行分類,并逐漸明晰每一類問題的主要觀點、關聯,以及在歷史進程中該領域問題研究成果的推進程度如何。當自己能夠將每一類問題的學術脈絡理清時,也就離整體掌握該領域的研究現狀更接近了。比如,筆者在閱讀《淺談朝鮮族民族打擊樂組合“四物樂”的歷史起源》一文后的解題中寫道,“將該文與《朝鮮族‘四物樂’的社會學視覺研究》《朝鮮族風物與四物樂流變研究》關于‘四物樂’歷史起源問題進行比較,可以得到以下信息和問題:文論將‘四物樂’作為朝鮮半島和我國朝鮮族共同存在的打擊樂表現形式;《朝鮮族‘四物樂’的社會學視覺研究》和《朝鮮族風物與四物樂流變研究》兩篇文章認為‘四物樂’是在1978年由韓國產生,后傳入我國朝鮮族地區。但本文中雖然提到1978這個年份,但并沒有明確指出是產生于韓國,相反在行文中有朝鮮族地區自古就有‘四物樂’這一表現形式。這種‘共同存在’之說是否成立,究竟是源起于朝鮮半島,還是兩地同時產生?作為同源的音樂表現形式在三地的發展情況有何異同?”[注]選自筆者2018年5月1日所做的解題。筆者就“四物樂”起源問題將閱讀的3篇文獻進行串聯,發現對其起源時間和起源地點的闡述都相對模糊。當筆者進入田野時,就可以有針對性的尋求答案。在進入田野工作后再來反思這一問題就會發現:文獻中的模糊性正是由于研究者并沒有開展扎實的田野工作,沒有理清“四物樂”在延邊地區呈現的不同發展階段,以及中韓“四物樂”文化根源指向的不同。解題的過程會使自己的文獻庫數量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大,同時解題也會如一條紅線般將每一類問題都串聯起來,使研究中的問題迷霧越來越清晰。
2.進入田野的關鍵詞——“不放過”與“不輕信”
當研究者進入田野后,要盡可能將所有面對的事項都收入到頭腦中,變為自己對于田野作業、對于學科的一種認識和思考,也就是所見即田野,換言之就是“不放過”。“不放過”,既是一種行為理想與規格,又是一種實在行為目標。這就要求研究者“忘記”腦海中預存的文獻、預判和設想,“忘記”這些基于“他者說”的“束縛”,放空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當場面對的田野中,感受田野中所經歷的一切。當然,“所見即田野”之論,并非是漫無目的地“見”,而是帶有專業敏銳度的“放空”,心中時刻裝著被研究對象的“看見”。任何來源于生活中的細節,都有可能成為揭示和解釋音樂與之所根植的社會及其文化相互關聯的關鍵密碼。與此同時,也要注意到在田野當中自己所看到的真實,有時并非是真實的,也就是所謂的“田野非所見”。這種“非真實”的背后,有時卻恰恰隱藏了一些值得推敲的信息等著研究者去揭秘、闡釋和界定,即“不輕信”所見。

筆者研究認為延邊朝鮮族群體對“樂(le)”字的選擇與認同,反映了中國朝鮮族族群音樂審美的變化,以及“四物樂”在延邊地區發展過程中體現出的文化適應性。由一個概念引發的問題成為自己進入“四物樂”音樂事象與族群文化關聯的重要突破口。對這一個概念異議的發現和追問,就是“所見即田野”和“田野非所見”意識與觀念的體現。


圖1 “四物樂”演奏
(2018年9月24日《2018最美賞月地——了不起的非遺·感受邊境線上的“秋夕節”》節目錄制現場 馬琦玥 攝)

圖2 “百種集市”中的打擊樂表演(2018年10月1日 馬琦玥 攝)
3.從田野中抽離的關鍵詞——抽離≠脫離
雖然按照階段的劃分它被置于末位,但是這一工作并不是要在田野作業的最后才來完成,而是應該每天,甚至是在每個作業單元思考每個問題時都要及時進行抽離式分析,這是促進實踐深耕的重要保障。對研究對象的沉浸式融入和作為研究者的理性分析并不沖突,研究者作為感知者、挖掘者、整理者、分析者、翻譯者、傳播者,恰恰說明了主位與客位相結合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當然,對于研究者來說,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這類似于要求研究者同時擁有兩個大腦,一個負責沉浸式融入田野,一個又時刻對發生的一切進行理性的判斷。這似乎比“一天結束后必須寫田野筆記”的要求更為嚴苛。事實上,在田野過程中我們通常會出現三種情況:沉浸于田野中難以自拔,忘記了研究者的身份;沉迷于研究者的身份,無法沉入田野,主觀臆斷;在田野資料堆積如山后再進行分析,毫無頭緒。最后一種情況的遺憾之處在于,我們會錯失對田野復數性信息的及時感知和把握。
但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分析”是抽離式的,而非脫離式的分析。也就是說,研究者的分析是要基于事實,而非又回到以研究者為尊的臆想式的脫離音樂情境、文化環境、族群主體的分析。抽離式的分析是讓研究進一步深入的重要環節,是推進問題思考的助推力;而脫離式的分析則說明了研究者沒有對田野作業進行內化式理解,也沒有進行有效的田野作業。研究者不是小說家,也不是詩人,研究過程中尤其是田野作業中必然伴隨著人性的感悟、情感的表達與專業注意力分配,但是研究的落腳點依舊是學術、學科、學理。研究者的研究是否可以做到這一點,反映了研究者田野作業的水平;而研究者在進行田野作業時擁有這樣明確的意識,也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實踐深耕”的最終目的是能夠發現隱藏在繁雜族群音樂事象背后的音樂特質與文化本質,這是研究者由“實踐”走向“理論”,由“描述”走向“闡釋”,由“知識體系”走向“學理建構”的基礎和關鍵契合點之一。總之,民族音樂學的田野作業并不是單純帶有浪漫情懷的奇幻冒險之旅,而是帶領研究者走出“荒野”,帶有整合性、持續性、科學性、系統性、深耕性的專業研究行為,以探求和解答學科專業中某一問題為目的的民族音樂學研究方法。
(二)理論深耕
針對前文提到的“理論認知不到位”的問題,在此,從“明確學術研究需要理論支持的觀念”以及“對理論的‘細讀’”“尋求自己的理論建構”三個角度提出解決方案。
1.明確學術研究需要理論支持的觀念
“學術研究需要理論支持”既是命題也是觀念。對“學術研究需要理論支持”,可以從兩個方向進行解讀:一是,在進行學術研究之前,需要尋求已有理論的支持。這就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不僅需要知道自己所在學科專業有什么理論、有哪些理論可為自己本次研究所用,還要清楚所用理論的主旨意義與功能所在。對于民族音樂學而言,當研究者進入某一課題的研究時,會對將要涉及的理論取向問題有所預判。理論預判或設定的取向不同,運用和研究訴求的方向也會有所不同。比如,是認同問題、變遷問題、性別問題研究,還是國家在場問題研究?或許對于研究問題的準確落腳點會在田野進入之后會有所調整,但在設計某一課題,或者進入田野作業之前,這樣的“理論預設”是有助于研究定位的;二是,在田野作業結束后,研究者需要對原始材料進行梳理、歸納和分析,并形成具有知識性和學理性的學術成果。盡管有的學術成果本身就是理論,但是,在學術成果的形成過程中是需要理論的支持,除了與前期理論預判一脈相承的理論“闡釋”外,還需要研究者對自身研究進行合理的學理揭示與提升——生成自己的專業理論。
需要明確提出的是,于此所說的“需要理論支持”并不是為所要研究的音樂事象強行穿上某件“理論”的外衣,也并非是讓研究者生編硬造出一個所謂的理論為自己的研究扣一頂高帽,而是闡釋理論于獨立研究中的不可缺失性價值與重要性所在。任何站得住腳的學科專業理論都是產生于豐富的實踐經驗解析與深入研究中,并且可以不斷被實踐所論證的。
2.對理論的“細讀”
中國當下的民族音樂學研究過程中的確不缺少理論的養分支持,不論是音樂學內部,還是跨學科的。但對于這些理論的運用,在很多研究過程或最終成果中,都程度不同地呈現出“饑不擇食”與“消化不良”的癥狀。因此,對于采用或選擇來用的支持理論,研究者需要對其“細嚼慢咽”,既驗證自己理論選擇的恰當性,又確定理論應用的精確性。
研究者在面對基礎理論以及個案研究所需要的理論時,應該注重對理論的“細讀”,避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拿來主義”狀況出現。這里所說的“細讀”,強調在研讀過程中理解該理論產生的語境,并且能夠讀懂該理論的推導邏輯。任何理論的提出都有其特有的歷史學術背景,有其針對的某一現象、趨勢或者問題,以及該理論力圖解決的問題。理解理論產生的語境,有助于研究者從更為宏觀、全面、客觀的角度看待該理論,并且對理論的運用提供邏輯前提。反之,若將理論抽離出產生的語境來看待,則會產生誤讀。讀懂理論的推導邏輯,如同跟著理論提出者的思維進行一次學術探秘之旅,梳理出理論的內部邏輯結構,由此還獲得一個寶貴的收獲——啟迪性習得自我理論形成的意識與方法,這為體系性助推自己的研究獲得有力的條件性資本保障。此外,由于中國當下民族音樂學教學中所用教材多為外文譯著,所以,學習者最好在研讀過程中將英文原文與譯著結合起來看,獲得原汁原味地知道與理解。畢竟,“翻譯”這樣一種文本轉述方式,還是會因譯者的專業水位和專業立場存在些微差異的。
3. 尋求自己的理論建構

雖然在民族音樂學研究中,研究者不應該把單純追求理論建構作為研究活動的唯一且終極的目標。但是筆者同樣認為,研究者要有基于事實和學理創生理論的追求和能力。理論就是能夠將自己的想法編碼為一套可以普遍適用的知識體系,是對事象與事項、事實與經驗、經驗智慧與洞見等存在的“意義”“學理”“價值”之發現、析出、概括、結論及其體系化。當然,這并不是說個人創生的理論一定會適用于所有個案研究中,而是說明這樣的理論創生思考,有助于豐富民族音樂學的研究生態,并提供獲得更多深耕研究的可能性。
總之,民族音樂學的研究離不開對理論的深耕。研究者需要明確學術研究需要理論支持的觀念,在學術研究之前對所需理論有所預判,并進行細讀式的理論研讀;在形成學術成果的過程中,研究者也應該注重對個案研究進行自我的理論揭示與提升成型。一句話,“理論深耕”的目的在于發現借用和自我建構的某一理論的指向空間和生成可能性。當然,這也是“理論認知”的最終目標,也是理論認知訴求的本質性指標內涵。
換言之,通過“實踐深耕”探究到的音樂事象的特質與文化內涵的本質,應該與“理論深耕”揭示的指向空間和生成可能性匯集于一點,這就是“實踐深耕”與“理論深耕”的“本質契合點”。無論是“田野工作”與“理論認知”的一體發力目標指向,還是“音樂事象”與“理論闡釋”的一體融合生成意義,都是為了定位和探究這一“本質契合點”。可見,形成“本質契合點”是解決民族音樂學研究活動中“兩張皮”問題的關鍵策略所在。
綜上所述,一方面,有效解決“音樂事象”與“理論闡釋”這“兩張皮”的問題,需要在民族音樂學研究中確立“深耕研究意識”這個觀念。二方面,對民族音樂學研究中基于消解“兩張皮”問題而進行的“深耕研究”認識與實踐,可以依循如圖3所示的研究邏輯和路徑而為。換言之,要認識和理解到:“實踐深耕”的實現依賴于田野作業過程中注重“解題”“不放過與不輕信”“抽離≠脫離”三個環節及其主旨意義與功能的整合與作用;確立學術研究需要理論支持的觀念、理論需要細讀和尋求自己的理論建構,則是達成“理論深耕”的方案。三方面,找到“本質契合點”是民族音樂學個案深耕研究目標達成的價值與標識。“實踐深耕”的目的是發現音樂事象背后的族群音樂特質和文化內涵本質;“理論深耕”的目的是發現某一理論的指向空間和可能。對“實踐”和“理論”進行深耕的最終目的是挖掘出“音樂事象”和“理論闡釋”中各自的本質性內涵,兩個本質性內涵所達成的契合點就是該研究中“音樂事象”和“理論闡釋”的本質契合點。所以,本質契合點是解決“音樂事象”和“理論闡釋”“兩張皮”問題的關鍵所在,也是解決影響民族音樂學中的“理論”和“實踐”融合一體發力作用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