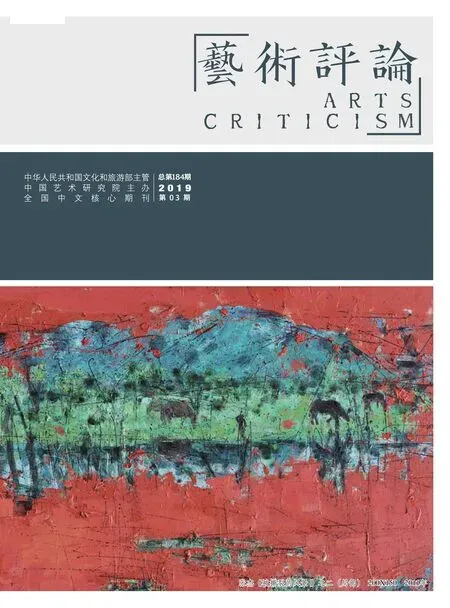《阿伽門農》,是回歸,也是開始
羅 彤
埃斯庫羅斯被譽為古希臘悲劇之父,但他同時也是一名戰士,一名為了城邦的正義參加過戰斗的公民。公民、詩人、戰士,這些關鍵詞構成了他的身份。作為公民,他有責任參與城邦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他以劇詩的方式表述自己對于制度與正義的態度。作為詩人,戰爭不僅是他創作的題材,更是他親身經歷的生活。他的墓志銘上驕傲地寫著:“歐福里翁的兒子,雅典人埃斯庫羅斯長眠在這墳墓里,四周有革拉的麥浪在蕩漾。馬拉松圣林會稱頌他的英勇,那蓄著長發的波斯人,對這最是了解。”
這位悲劇詩人出生于公元前525年。那一年,強大的波斯征服了古埃及,結束了埃及二十六王朝百余年的統治。雄心勃勃的大流士隨后把矛頭指向城邦眾多的希臘。公元前490年,大流士命中注定般地遭遇了那著名的馬拉松戰役,以損失6400人的代價,輸給了僅僅陣亡192名英雄的雅典。埃斯庫羅斯便是這場戰役的親歷者,時年剛好35歲。18年后他寫出了悲劇《波斯人》,以抨擊不義的戰爭和東方的專制,贊揚雅典的民主。同樣描寫戰爭之殘酷的,還有作者以67歲高齡演出的悲劇《阿伽門農》,那時距他去世還有兩年的光景。讀一讀劇中傳令官的臺詞,我們便會看到,一位親歷戰爭的老者在將死之前對戰爭的反思。一邊是阿伽門農洗劫特洛伊的豐功偉績,一邊是“滿目的瘡痍像花兒一樣開遍了愛琴海的海面,到處都是希臘人的尸體和船只的殘骸”。在生命面前,所謂的正義已黯淡無光。
然而,《阿伽門農》之所以成為埃斯庫羅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并不僅僅是因為它對戰爭細致入微的描述,而是它豐富多義的主題和深刻的內涵。正像所有古希臘經典劇目一樣,《阿伽門農》的主題也是多義而深廣的。要理解這些,我們不妨先來看看阿伽門農的故事。
阿爾戈斯國王阿伽門農受弟弟斯巴達國王之邀,集合希臘大軍討伐特洛伊,原因是特洛伊王子拐走了斯巴達的王后海倫。大軍出發之前,由于阿伽門農傲慢地射殺了狩獵女神的麋鹿,女神發怒,使港口無風,艦隊無法啟程。阿伽門農為了希臘城邦的利益,在先知的建議下忍痛將自己的大女兒殺來獻祭,因此受到妻子克呂泰墨斯特拉的強烈譴責。大軍雖順利出征,但仇恨的種子已深深埋在王后的心中。國王離開的日子里,她竟與國王的堂兄通奸,一起霸占著阿爾戈斯的王位。后面的事情我們隨著《阿伽門農》的劇情都已知曉,國王雖得勝歸來,卻死在了自己妻子的陰謀之下。表面上看,這故事講的是阿伽門農慘烈的經歷,但背后卻隱含著復雜的背景與玄機。且讓我們再往前看看。阿伽門農的曾祖父曾經把自己兒子的肉煮來獻給天神們吃,以試探天神是否具有神力辨別。這不敬神的行為受到懲罰,他被打入地獄,饑不能食、渴不能飲。阿伽門農的祖父因為不守承諾,受到詛咒,注定后代族群中將充滿血腥、背叛與仇殺。到了阿伽門農父親一輩,殺戮與陰謀更是在兄弟與血親之間蔓延,沒有人可以逃脫。他們甚至再度上演祖先殺子煮肉的罪惡行徑。阿伽門農的曾祖父是煮了自己的兒子給神吃,他的父親卻是殺了兄弟的兒子給兄弟吃。堂兄埃奎斯托斯的獨白,清楚地為我們描述了人可以犯下的最深的孽。那么后來呢?這悲慘的命運并沒有因為阿伽門農的死亡而結束,接踵而至的是他的兒子俄瑞斯特斯長大歸來,殺死自己的母親,替父報仇。殺母之罪使俄瑞斯特斯終日不得安寧,被復仇女神四處追逐。直到他逃到雅典,經眾神的審判,才得以洗清這家族世代的詛咒。
沒有任何一件事是孤立發生的。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強調,悲劇完美的布局要求一個事件與另一個事件之間應具有因果關系。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詛咒,貫穿在阿伽門農整個家族中,后代命中注定要為祖上的罪孽承擔惡果。一場殺戮換來另一場更為慘烈的殺戮,阿伽門農殺女、克呂泰墨斯特拉殺夫、俄瑞斯特斯殺母。然而,這一層一層遞進的殺戮,卻在俄瑞斯特斯這里,得到了神的寬恕。男權最終穩固地進入了我們的世界!可正是因為如此,王后克呂泰墨斯特拉的控訴才越發顯得彌足珍貴,無論是在埃斯庫羅斯的《阿伽門農》中,還是在索福克勒斯的《厄勒克特拉》中。后世更有現代希臘著名劇作家卡班奈里斯的《晚餐》,以浪漫主義的情懷為阿伽門農家族的血仇續寫了后傳,以女性的立場為克呂泰墨斯特拉辯護。

《阿伽門農》劇照 王雨晨攝
阿伽門農歸來了,但孰知卻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當他踏上那紫色的花毯,前面等待他的是王后口中他永遠的家——墳墓。回歸,是所有劇中人物的中心詞,場上所有角色都圍繞著回歸這一事件展開著行動,哪怕是尚未出場的俄瑞斯特斯,也預示著下一場回歸的開始。《阿伽門農》最后一句臺詞是王后對情夫說:“且讓我們好好治理這座宮殿。”而導演卻特意安排歌隊長將阿伽門農的尸首放回了空空的王位。這是歌隊的態度,更是城邦公民的態度,它表明了對專制的抗衡,對俄瑞斯特斯歸來的期盼。《阿伽門農》是埃斯庫羅斯《俄瑞斯特亞》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詩人借之后的兩部悲劇,講述了俄瑞斯特斯的復仇和審判,它們分別是《奠酒人》和《報仇神》。三部曲中,《阿伽門農》是回歸,卻也僅僅才是開始。
今日,中國國家話劇院聯手希臘國家劇院共同出品經典名劇《阿伽門農》,由兩國演員同臺,以雙語演出,是一件幸事,也是一個挑戰。所幸的是,我們終于有機會與來自希臘的主創團隊合作,共同打造國話版古希臘悲劇。當然,這樣的先例并非沒有,去年11月上話版《厄勒克特拉》就同樣是邀請了希臘的導演以及主創。所難是,兩國演員同臺,“各說各話”。這的確是一件大膽的嘗試,對雙方都是首次,都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耐心去磨合、去適應。古希臘悲劇內容原本就隱喻難懂,又有著系統龐雜的神話作為背景,對于東方文化語境下的中國演員和觀眾自然更是存在難度。為了貼近當代演出,讓觀眾更直觀地進入情境,導演特意要求重新翻譯文本。這又是一個挑戰。
古希臘文學在中國的引進早在明代便有記載,并于清代末年受到矚目。1857年英國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在雜志《六合叢談》(第一號)上發表文章《希臘為西國文字之祖》,并在第三號上撰文《希臘詩人略說》,開了介紹希臘戲劇詩人的先河。但真正系統地翻譯古希臘戲劇作品,始自20世紀30年代,由羅念生先生先后譯出埃斯庫羅斯悲劇七種、索福克勒斯悲劇七種、歐里庇得斯悲劇五種、阿里斯托芬喜劇六種等。2007年王煥生先生和張竹明先生合譯了《古希臘悲喜劇全集》,將古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一位喜劇作家以及新喜劇作家米南德現存的劇作盡收其中。然而,自20世紀30年代起至今,近一百年的時間過去了,古希臘戲劇的翻譯仍停留在這幾個有限的版本中,未出現新的有價值的譯本和箋釋。而語言是活的,是社會生活與時代變遷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因此,重新翻譯古代經典是新時代的需要,也是使命。
戲劇翻譯又不同于其他文學形式的翻譯,它必須適合舞臺演出,必須適應演員的現場朗讀,必須讓觀眾在一定距離下聽得朗朗入耳。這便需要翻譯者了解舞臺演出的規律,甚至了解舞臺表演的規律。古希臘戲劇原文以韻律詩為載體,有著嚴格的節拍和格律。翻譯成漢語后如何達到既保持原意,又合拍押韻,是歷代翻譯家們共同面臨的課題與難題。而這次雙語版演出的文本重譯,又迎來了另一個具體的挑戰。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同臺表演,需要翻譯者協調不同語種之間的語言結構、語言節奏和語言風格,以使它們達到內容上及聽覺上的同步與和諧。這一點并不容易。因為古希臘戲劇作品是多義的,往往那些深刻的思想并非簡單地通過顯性臺詞傳達出來,而是隱含在豐富的潛臺詞之中。
今天,國話版《阿伽門農》已經走上舞臺,面向觀眾,接受考驗。希望觀眾朋友能通過這部戲感受到古希臘戲劇文學的美,并從中得到心靈的啟迪。戰爭、正義、詛咒、命運、男權、回歸……2500年前,埃斯庫羅斯為我們提供了如此多的具有鮮活生命力的關鍵詞。它們跨越時間、跨越地域、跨越民族,講述著人類共通的主題。它使我們痛,卻不悲。它凈化我們的靈魂,陶冶我們的情操,升華我們的精神,使我們變成更好的人。這是戲劇的魅力,也是戲劇的初衷。2500年后,在今天五色斑斕的社會環境、藝術環境、戲劇環境下,我們有必要回到源頭,去看一看自己是否已經目盲,是否已忽視了自己的初衷。這初衷于我們,如早春的貴雨,是我們的給養。
中國國家話劇院與希臘國家劇院的合作,是一次跨時代的相遇。當古老東方的中國舞臺牽手戲劇之源的希臘,是回歸,也是開始。
注釋:
[1]黃薇薇編譯.《阿卡奈人》箋釋[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