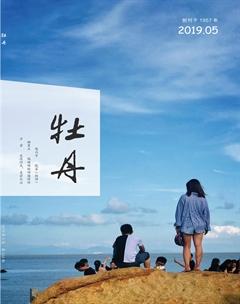從精神分析學角度淺析莫言小說創作
莫言于1984年創作的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1985年在《中國作家》發表后引起巨大反響,并奠定了他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這篇小說在創作心理、主題意蘊、風格營造方面呈現出豐富的內涵,使得許多研究者從作品的語言風格、懷鄉主題方面對文本進行了細致的解讀。本文試從精神分析角度剖析小說主人公“黑孩”的精神世界及莫言創作心理,試圖更好地理解小說人物形象,更進一步發掘小說的深刻內涵。
一、莫言的“童年情結”及在黑孩形象里的體現
個人無意識有一種重要而又有趣的特性,那就是,一組一組的心理內容可以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簇心理叢,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稱之為“情結”。所以,當人們說某人沉溺于某種事物而無法自拔時,可以說他有一種‘癮”。莫言似乎對饑餓、孤獨的描寫有癮的趨勢。
莫言1956年出生于中國北方的農村,正值左傾思想嚴重、農民物質極大匱乏、生活水平低下的時候,大多數人處在溫飽線下,僅僅是為了生存而努力。據他回憶,他12歲時被派去參加修建水利工程當小工,因為偷吃一根紅蘿卜而被幾百人批斗,之后并沒有結束,不僅要跪在毛主席像前請罪,而且回家后又立即挨了一頓毒打。這個孩童時期真實被羞辱的事件在他的記憶深入留下了極深的烙印,令他刻骨銘心。同樣,《透明的紅蘿卜》中出現了他人語言和肉體上的肆意暴虐,對黑孩的生命能量進行著無盡的壓榨,作品開頭平淡地寫道,隊長看到黑孩時說:“黑孩兒,你這個小狗日的還活著?我尋思著你該去見閻王了。”這句看似日常問候實則冷血無情的話,讓人心生寒意。一個剛剛十歲還處于充滿希望的少年時期的孩子,他人生旅程僅僅開啟了極小的一部分,被期待和被祝福理應是最該有的情感,可現在別人卻懷疑他活著的常理性。冷漠、麻木的隊長和村民是困苦年代里的真實再現,隨意到令人震驚,是那個時代無法抹去的印痕。作品中殘酷無情的生存環境和堅強的孩童形象,是莫言自己和自己童年社會生活現實再創造的結果,在黑孩身上投射出對命運的無力感和絕望,這是為黑孩悲泣,亦是為他曾經的自己。更深層次地說,黑孩作為莫言自我內心的象征,隱含著作者自己內在經歷了童年的晦暗苦澀時期之后依然按照自己內心的方向堅定地走向了文學的堅韌精神。
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強調,無意識并不只是靜靜地躺在心理結構底層的暫時忘卻的東西。它更多地是被長期壓制的動機和情感的聚積,它們大多來自過去的生活事件,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兒童期性發育過程中的創傷性經驗。這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莫言能對黑孩形象有合理的把控與描寫,以及為何在成名后不同場合多次提到童年時期饑餓、孤獨、受屈、挨打等深刻際遇。他自己曾多次強調,“因為吃,我才發奮走上了創作之路”。這種童年饑餓經驗影響著莫言的性格,也影響著莫言的創作,2000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作演講時,莫言即以《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為題。這樣看來,生存的苦難、愛的缺失,不公正的體驗等,成為莫言童年敘事的中心主題和表現對象就不難理解了,“童年情結”在其創作中所起到的巨大動力作用儼如心理學家所稱的“情結”。莫言的“童年情結”大體由饑餓與孤獨、隱忍與無奈、愛和被愛的欲望等“心理因素”構成。這些被壓抑的個人無意識隱匿于心靈的深處,一旦碰到啟動點,便洶涌而出,成為其創作的源泉。
這部小說雖然存在虛構的童話因素,但實際上是以當時真實的鄉村生活面貌為構圖基礎,附帶著作者濃厚的個人記憶與生活感受,蘊含著厚重的生命氣息,小說作為藝術作品時常隱藏著作家真實的一面,《透明的紅蘿卜》是作家無意識的童年經驗的折射,經過作家“再度矯正”后呈現的內容,不僅表達了作者對黑孩的同情和對實現生活的控訴,也體現出莫言對童年記憶想要掙脫卻又不由自主時常喚起、不能徹底擺脫的糾結感受。從這個意義上看,此小說是莫言對自己個人記憶的藝術再創造和再加工,是對現實生活的“再度矯正”,即便是極力克制想要做到零度情感,更多的時候作家作品都會自然而然地受到主觀感受和個人記憶的影響。
二、黑孩的“戀母情結”
弗洛伊德認為,“人所有的行動都受欲望的驅使,人從生下來就有性意識”。意識是說,無論人有什么樣的日常行動,都是由“性”這種原始欲望引發的,并且這種欲望是與生俱來和不可完全控制的。
黑孩從小沒有母親,父親也早拋下他自顧自地走了,后母對他非打即罵,冷眼相待,他從未認真感受到過來自親人的關懷,盡管獨自努力成長到十歲,他依舊瘦弱、饑苦、孤獨、自閉,在他的內心深處父母的概念和形象是非常陌生和模糊的。自小缺少家庭關愛和溫情的黑孩,在遇到菊子姑娘以后,黑孩第一次被一個女性像母親一樣溫暖和關懷,菊子姑娘對他的好喚起了他對愛和被愛的渴望,并讓他有了改變。以前,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自然景物之中,把人隔絕在外,但現在他對人有感觸了,他害怕失去菊子姑娘,害怕失去這份愛。所以,黑孩把菊子給他包扎過傷口的手絹視若珍寶,當作愛的象征,不顧身體的疼痛將手絹塞進石縫里,試圖將這份關愛珍藏起來。所以,黑孩常常坐在菊子干活時的座位上,雙眼緊緊盯著石縫,會對菊子姑娘親手洗過的蘿卜產生幻想,以至于看到“一片黃麻倒地,像有人打過滾”時,會覺得難過、會哭。菊子在黑孩的世界里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年幼的他不愿再次失去被愛的感覺,菊子給黑孩孤寂的靈魂里帶來了溫暖,出于一種母性本能,菊子關心黑孩并認真給他包扎傷口,給了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感受過的關心和愛護。
因此,可以看到黑孩對待菊子姑娘的感情里帶有一種“俄狄浦斯”情結,亦即“戀母情結”。菊子姑娘是闖進黑孩黑暗生命日子里的第一人,她帶給他全新的感受。人對于最初進入視野的人都有一種天然的依戀性,他依戀著菊子,愛慕著菊子,這些構成了他對菊子的一種特殊的感情,他不愿意有人從他這里奪走或者分享這份愛,奪走本該屬于他的關注。因此,在小石匠和小鐵匠發生沖突時,去幫助粗暴對自己的小鐵匠,而不是去幫日常友善待他的小石匠,黑孩知道小石匠和菊子彼此喜歡,但正因為如此,在他潛意識里小石匠是他的敵人,因為他的存在,黑孩不能享有菊子全部的關愛,所以這種“戀母”情結讓他有后續幫助小鐵匠的行為。最后的結局就是菊子姑娘瞎了一只眼睛,菊子和小石匠離去,黑孩“家”的夢想徹底破滅,弱小又無助的他注定無法與現實相抗衡,只能是留下難言的抑郁和惆悵。
弗洛伊德說:“我們不愿入世,因而和人世的關系,只好有時隔斷才可忍受。”這里的“世”指的是社會生活,“人世”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這里,筆者認為,人帶有一種“不愿入世”的心理,人之所以生活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是人們的本意,是人本身無法自主選擇的結果,因而面對人與人之間復雜的關系,出于自我保護的天性,只有持續是“隔斷”才可以繼續維持下去。面對這樣苦難的“人世”,黑孩能選擇的也只有“隔斷”,恰好沒有感受過溫暖與力量的黑孩,能選擇的也只有“隔斷”,他放棄了說話,漠視外界的一切。全文呈現失語狀態,除了哭泣和偶爾的咳嗽聲,黑孩幾乎就沒有回應過任何人的詢問,即便是他遭受指甲蓋被錘子砸裂流出血的疼痛時,也只是下意識地迸出音節;這種“隔斷”還表現在他漠視自己的感受,后母打他他只是覺得熱乎乎,不痛,拉風閘時,甚至去抓鉆子,“聽著手里‘滋滋啦啦響像握著一只知了”。
雖然壓制了表達欲望,但是這并不代表黑孩內心的麻木。可以看到,在他自己的幻想世界中,生活還是豐富多彩的,他非常專注于自然界的一些細節,如不斷出現對于農村天空、河水以及大片黃麻地的描寫,這些充滿奇異色彩的景色、聲音和感受,便是黑孩在時不時游離出現實社會時,所感受到的他心目中的自然世界。這使得他能夠最早注意到菜園里的瓜地和蘿卜,敏感地發現河上傳來的奇異聲。小黑孩善于幻想出內心的渴望,以求片刻逃離現實的世界,這種暫時的意識出走游離,可以用弗洛伊德的“夢的分析”理論來解釋。弗洛伊德《夢的解析》提到,“夢乃是做夢者潛意識沖動欲望的象征,做夢的人為了避免被人察覺,所以用象征性的方式以避免焦慮的產生”。也就是說,夢是被壓抑的潛意識沖動或渴望以改頭換面的形式出現在意識里的,由此人們也能很好地解釋“透明的紅蘿卜”出現在小黑孩眼前的原因了。作者這樣寫“透明的紅蘿卜”:“光滑的鐵砧子,泛著青幽幽藍幽幽的光。有一個金色的紅蘿卜。紅蘿卜的形狀和大小都像一個大個陽梨,還拖著一條長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須須像金色的羊毛。紅蘿卜晶瑩透明,玲瓏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殼里苞孕著活潑的銀色液體。紅蘿卜的線條流暢優美,從美麗的弧線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長有短,長的如麥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黑孩眼前呈現出這樣神奇的幻象:一棵散發著溫暖光芒的紅蘿卜,在人的眼前飛躍、跳動,沒有其他人、事物的參與,只有黑孩和“透明的紅蘿卜”在一起。在黑孩的自由遐想世界里,沒有他人的存在,掩飾了這些人在現實中的缺席,同時也反映出黑孩內心對愛和溫暖的強烈欲求。
紅蘿卜代表著愛、溫暖和滿足,通過這短暫而神奇的幻境,人們看到了黑孩生存狀態下的向往與矛盾。黑孩愿意被這美妙安詳的氣氛吸引,他想抓住這個美麗的“透明的胡蘿卜”,然而這種凝結著溫馨的家的夢想破滅了,他不惜舍命趟水要打撈也一無所獲。內心渴求的出現只能是在幻象中的書寫方式,注定了黑孩尋找精神家園、渴望溫暖的希望會破滅的悲劇結局。
(伊犁師范大學)
作者簡介:馬優梅(1990-),女,新疆伊犁人,碩士,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