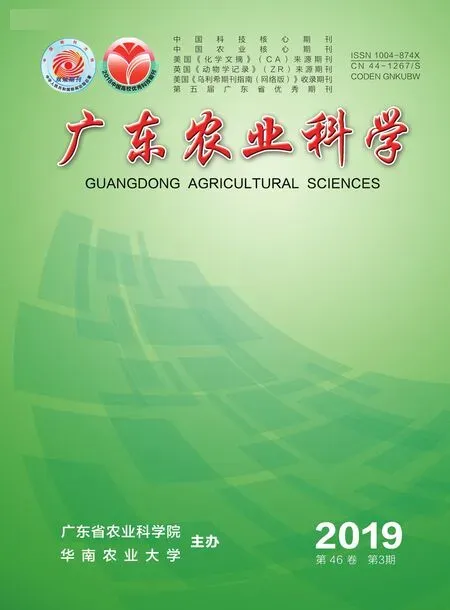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生豬供應體系現狀研究
梁桂超,張 利,鄭業魯,薛春玲
(1.廣東廣墾畜牧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廣東 廣州 510507;2.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642)
【研究意義】 廣東是我國主要的生豬生產大省、消費大省以及供港澳活豬的唯一出口和重要基地,近年生豬出欄量保持在年均3 500多萬頭,但其仍需從外省調入生豬近2 000萬頭[1],才能基本滿足廣東省對豬肉的各類消費需求。但隨著國內生豬養殖區域轉移和升級的需要、非洲豬瘟等疫情風險以及環保規制等疊加因素的影響,廣東省近年生豬出欄總量在逐漸減少,而作為國內主要豬肉消費區,2017年廣東常住居民人均豬肉消費量為29.07 kg(數據來源于2018年《廣東省統計年鑒》)。因此,當前現狀一方面突出了生豬的穩定供應在廣東省整個農產品供應體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廣東省需進一步加大從外省調入生豬數量或增加豬肉的進口量,以保證廣東省的生豬供需關系穩定和內地供港澳活豬的積極性和安全性等。位于泛珠三角區域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發展規劃、合作等議題成為眾多學者關注或研究對象[2],而農產品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居民基礎的日常消費品,其穩定供應及安全可靠等問題也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其中肉類消費特別是豬肉消費作為居民主要肉類消費選擇,其穩定供應等問題是管理部門、居民關注和學者研究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農產品供應不可忽視的板塊。針對近期非洲豬瘟等疫情風險的出現,一方面沖擊著國內生豬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更直接導致了國內及區域的生豬調運暫停和城市供應偏緊,特別是依靠已被劃為非洲豬瘟疫區的區域進行生豬調入的城市,其生豬供應受到的影響更為顯著、直接,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生豬需求基本依靠區外調入來滿足,其生豬供應穩定顯得尤為重要。【前人研究進展】 當前針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研究主要集中人口流通、產業合作、資源流通、科技交流合作等領域[3-7],探討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融合發展問題,并為其各方面的融合發展提供決策參考建議,在農產品供應體系方面相對較少,主要通過農產品供應主體或基地的視角,探討如何保障城市或供港澳地區農產品的質量及其做法經驗總結等[8],特別是生豬供應體系方面,雖然對生豬產業發展影響研究已取得不少的研究成果,但隨著近年國內生豬產業調整,針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生豬產業和供給體系等領域面臨的風險和挑戰,研究相對較少。【本研究切入點】 監管部門保障生豬養殖供應端視角,對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生豬供應體系進行梳理分析,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本研究的出發點和意義所在。【擬解決的關鍵問題】 旨在基于目前國內生豬產業發展面臨的風險與機遇的背景下,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生豬供應體系進行梳理,分析其影響因素以及對策建議,為進一步完善生豬供應體系提供決策參考。
1 粵港澳大灣區生豬供應體系現狀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生豬總出欄量、豬肉總產量以及各大城市的生豬出欄量和豬肉產量基本呈逐年較大幅度下降趨勢(表1、表2),其中廣州、東莞、佛山等城市生豬出欄量下降趨勢顯著。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生豬出欄量為1 134.65萬頭、豬肉產量85.25萬t,分別較上年減少75.95萬頭、5.60萬t。據估算,目前僅廣州和深圳兩市的生豬消費總量合計1 400萬~2 000萬頭,因此,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生豬總出欄量不能滿足廣州和深圳兩市的生豬消費量。另外,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常住總人口約6 957.16萬人(表3)并且處于持續性增長期,龐大的人口規模決定了豬肉消費的巨大需求量,以人均豬肉消費量29.07 kg估算,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豬肉消費總量約202.24萬t(不含加工豬肉消費量等),而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的豬肉總產量僅為85.25萬t,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生豬供應難以靠自給滿足其需求,需要通過外調生豬或進口凍豬肉等方式彌補各環節的豬肉消費缺口。

表1 2014—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生豬出欄量(萬頭)Table 1 Number of live pig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4 to 2017 (104 head)

表2 2014—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豬肉產量(萬t)Table 2 Pork produc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4 to 2017 (104 tons)

表3 2014—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人口數量(萬人)Table 3 Popula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4 to 2017 (104persons)
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生豬及產品難以通過自給方式滿足其需求且供需缺口較大的情況下,就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生豬供應體系如何實現保證本城市生豬供需穩定的目標,本文進行了梳理和分析。目前,根據政府監管特征和市場關系等因素,可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生豬供應體系大致分為以下3類:第一類,基本靠通過外調生豬及其產品供應滿足本區域居民日常的豬肉消費需求,并且這些城市的生豬供應體系基本由相關監管部門制定管理辦法,確保定點生豬供應能力滿足本區域的消費需求,該部分城市主要有廣州、深圳和東莞;第二類,具有一定生豬自給能力,同時存在生豬外調入本地屠宰場,完成屠宰加工等環節,通過調肉的方式向周邊批發等市場供應豬肉產品,這類城市主要有佛山、中山、珠海、肇慶、惠州和江門等;第三類,港澳地區,其活豬供應基本靠內地進行配額制管理方式,確保港澳地區居民的豬肉供應穩定。此外,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除港澳地區為單向流動)生豬供應體系基本存在著兩兩城市之間的生豬雙向流動的情況。
1.1 廣州、深圳和東莞的生豬供應體系
廣州、深圳、東莞作為大灣區中廣東9市城市化水平最高的3個城市,在生豬自給率方面卻最低。廣州、深圳、東莞三市面對豬肉消費量缺口如此之大的狀況,如何保障其居民的豬肉消費需求?目前,廣州、深圳和東莞在整體上保證生豬供應的制度大致相同,均納入城市“菜籃子”工程[9],與省內外的生豬養殖場實行定點產銷區聯結供應機制(圖1),實現與城市“菜籃子”產品銷售網絡相對接,形成優質穩定的農產品供城市基地網絡,以提升生豬供應市場的調控能力。

圖1 廣州、深圳和東莞的定點生豬供應機制Fig.1 A sketch of pig supply mechanism in Guangzhou, Shenzhen and Dongguan
這類定點生豬供應體系的特征主要包括:一是實行的區域外生豬定點產銷區聯結供應機制,在管理層面由該市農業管理部門牽頭發改委、商務等部門制定具體的定點生豬供給養殖基地建設、認定標準、管理和退出等制度,在執行層面存在細微差異;二是要求定點生豬養殖基地所在地的管理部門進行“委托”式監管,實行雙保險共監管模式,保證定點生豬養殖基地所供應的生豬符合該市對生豬供應質量要求;三是基本都鼓勵或要求實行“雙定點”供需對接模式,即要求“定點生豬供應基地所供應的生豬”必須要該市“定點的生豬屠宰場(企業)”進行屠宰、加工,以保證在流通環節定點生豬供應基地所供應的生豬安全衛生、方便管理和供需關系穩定。例如,東莞通過實行區域外生豬定點產銷區聯結供應機制[10],保證東莞豬肉終端市場的供應穩定,目前東莞市已經共認定了657家供莞生豬基地,主要分布在廣東粵東西北地區、湖南、廣西等區域(表4),使其生豬供應能力達1 200多萬頭[11]。
1.2 佛山、中山、珠海、肇慶、惠州和江門的生豬供應體系
相對于廣州、深圳、東莞3市而言,佛山、中山、珠海、肇慶、惠州和江門6市生豬有一定自給能力,能夠滿足部分消費需求。其中,肇慶、江門和惠州市基本可以實現自給,并實現部分生豬外調,是廣州、深圳、東莞和港澳等地區的重要生豬供應基地,如惠州市2017年向香港地區供應活豬14.4萬頭、冰鮮冷凍豬肉0.7萬t。但這6市整體上還存在生豬供不應求的局面,如2017年佛山市生豬出欄量129.51萬頭,而同期定點生豬屠宰量達557.57萬頭;珠海市生豬整體供應中也存在60%的生豬需從外地調入,年調入生豬量達到70萬頭[12]。

表4 主要供莞生豬定點養殖場分布Table 4 Distribution area of main pig farms in Dongguan
因此,當前佛山、中山、珠海、肇慶、惠州和江門的生豬供應體系,基本可以通過消化本地養殖的部分生豬,實現局部區域的自給供應,同時因市場價差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區域也存在本地養殖的生豬外調到廣州、深圳、東莞等市場和周邊省市生豬調入的現象,既成為這些區域生豬供應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也成為大灣區的廣州、東莞、深圳及港澳等地區的活豬、豬肉重要來源地。此外,雖然佛山人口規模大,但該市部分地區存在較大規模的生豬養殖場,具有一定生豬自供能力,并且目前佛山市定點生豬供應的養殖場主要在市內和肇慶市,數量不多,而外調入生豬主要通過市場行為來滿足本市的屠宰消費,同時隨著近兩年環保政策壓縮佛山市的生豬養殖空間和規模,生豬養殖量受到較大沖擊,因此監管部門基于保障居民消費需求的角度,目前也逐步開始在周邊省市建立定點生豬供應基地。
隨著生豬產業政策變動,部分生豬產能從這些城市退出或轉移,造成生豬自給能力逐漸下降。廣東省生豬養殖大市惠州、江門和肇慶等都已提出生豬存欄、出欄量調減、控養計劃,如惠州市要求未來生豬出欄量控制為2018年198萬頭、2019年191萬頭、2020年180萬頭;江門市則明確要求將全市生豬養殖以2017年出欄357萬頭為基數進行壓減,2018年底存欄量控制在100萬頭以內。因此,這些城市的相關部門也開始逐步建立穩定的定點生豬供應體系,確保本城市的生豬供應穩定和質量安全可靠[13]。
1.3 港澳地區的生豬供應體系
目前,港澳地區的生豬需求基本由內地供應,主要由國內相關部門制定具體的管理措施,根據港澳市場規模、容量和內地供應資源布局,通過實行年度配額制管理方式保證港澳活豬供應穩定,如2018、2019年的配額分別為187.76萬頭、182.40萬頭(表5)。廣東、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和浙江作為供港澳活豬的重要來源(圖2),占比高達89.58%,其中廣東出口配額占比達35.61%,2016、2017年內地安排供港活豬數量均為173萬頭,同期生豬屠宰量分別為152.73萬頭和155.87萬頭(圖3),因此通過配額制有力地保障了港澳市場的日常生豬供應。

表5 2016—2019年供港澳活豬配額分配方案(萬頭)Table 5 Allocation quota of live pigs supplied to Hong Kong and Macao from 2016 to 2019(104 heads)

圖2 2018年內地供港澳活豬出口配額主要來源地Fig.2 Main sources of mainland export quota for live pigs supplied to Hong Kong and Macao in 2018

圖3 2016—2017年香港地區生豬屠宰量和內地供港活豬配額Fig.3 Slaughtering amount of live pigs in Hong Kong and quota for live pigs supplied to Hong Kong by the mainland from 2016 to 2017
內地供港澳活豬的體系運行相對標準化,主要得益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等主體的高度重視,給予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來保障供港澳活豬充足穩定的供應[14]。
針對內地供港澳地區的活豬體系(圖4),在各環節都做出了標準化的管理要求:首先,在供港澳生豬養殖基地環節,實行嚴格的動態備案監管制度和標準化生豬養殖流程,并且活豬供應區域相對固定,從源頭上保證了生豬供應的質量;其次,在貿易流通環節,對經營供港澳活畜禽企業實行審批制,在銷售港澳市場活豬實行代理制,以此保證供港澳活豬的質量和可追溯;第三,內地供港澳活豬體系是相對封閉獨立運行的農產品供應系統,并且在整個供應系統中,供港澳活豬的養殖過程、運輸流通等環節都由內地和港澳的雙重全流程監管,并明確界定了政府和企業在各個環節的分工合作,全流程“政府(機構監管)—企業(市場經營)”雙軌并行模式,為港澳市場提供優質、適量、均衡、應時的活豬。

圖4 內地供港澳地區的活豬機制Fig.4 Mechanism of live pig supplied from the mainland to Hong Kong and Macao
2 粵港澳大灣區生豬供應體系面臨的問題
2.1 生豬產業政策變動影響
隨著國內生豬養殖政策的變動,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生豬供應體系造成較大的影響。其中最大的政策沖擊來自環保政策的實施,根據中央環保政策的要求,地方管理部門都在短期內制定了詳細的生豬“禁-限-適”養殖區劃分的工作執行方案。例如,廣東省及其周邊省份等都根據各區域的環境承載能力,提出了具體的生豬調整及控養的具體工作目標,并且都要求在規定時限內,明確以生豬存欄等指標為主進行養殖控量,倒逼養殖主體根據其養殖場所處區域,進行養殖退出、轉移、減量及完善糞污處理設備的配套等工作。為此,許多地方管理部門紛紛出臺相關政策,在環保政策規范生豬養殖業的基礎上,進一步要求其區域生豬產業發展進行轉型升級[15],引導生豬產業往綠色環保方向發展[16]。生豬產業的引導、支持政策的落實加快了其規范發展的進程,同時也給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生豬供應體系帶來了一定的挑戰,這是由于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現運行的生豬供應體系主要建立周邊省市生豬養殖體系的基礎上,特別是生豬需求基本靠周邊省市定點生豬養殖基地供應來滿足珠三角城市群和港澳地區,周邊省市生豬養殖體系的調整,定點生豬供應基地面臨的政策調整風險,直接關系著這些城市的生豬供應穩定和質量安全。
2.2 生豬市場波動影響
生豬市場波動是目前影響我國生豬市場供需穩定的關鍵因素,特別是每一次周期性的生豬價格波動,都預示著一次大規模的生豬產能調整,致使國內或區域內生豬供需關系長期處于較大的波動范圍內,一方面極易造成生豬養殖端的養殖主體根據行情、獲利空間等變化,調整自身的生豬養殖規模、加大或減緩出欄計劃或者是否退出養殖行列等行為;另一方面受到影響的主體則為消費群體(消費者、屠企、加工企業),由于生豬市場波動現象的存在以及難以監控預測等因素,在生豬供應端受影響的基礎上,直接導致豬肉消費端供不應求或供過于求,使終端消費市場面臨恐慌性消費或屠企壓價等現象,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作為南方地區生豬消費的核心區和處于生豬產業鏈的屠宰加工環節、鮮肉環節;并且其當前運行的生豬供應體系為單一的“雙定點”供需對接模式,在生豬市場波動風險頻現下,生豬定點供應基地的供應數量、供應能力的波動,都影響著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生豬供應體系的穩定運行。
2.3 生豬行業疫情風險影響
當前隨著非洲豬瘟等疫情在國內蔓延,嚴重危害著國內生豬產業的發展[17],既對生豬產業的中長期發展規劃調整有著重大的影響,也造成區域內短期性的生豬供需失衡的局面出現,特別是豬肉的主要消費區域。根據國家對非洲豬瘟等疫情的防控工作規定,針對疫情爆發區,活豬跨區域調運是禁止的,因此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而言,目前非洲豬瘟疫情的風險對其生豬供應的影響是具有直接性,同時由于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現有生豬供應體系主要以活豬調運為主,其生豬外調的區域主要為廣西、湖南、江西、貴州等地,但當前這些區域目前都已爆發了非洲豬瘟疫情,無法以活豬形式調入粵港澳大灣區的消費圈內,特別是2018年底廣東省接連爆發多起非洲豬瘟疫情,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生豬供應影響更為明顯。根據疫情防控規定,省內市際間活豬調運也按規定執行明令禁止,由此出現了珠三角城市群的部分屠宰企業無活豬可宰的現象,短期內豬肉消費終端出現緊張供應的局面。港澳地區因其特殊性,活豬調運整體上并未受太大影響,但也因疫情爆發的影響,在調運區域、數量、線路上不得不做出相應調整,以保證對其活豬的穩定供應。
3 完善粵港澳大灣區生豬供應體系的對策建議
3.1 供應穩定視角
針對豬肉消費供應來源主要由區域外調入來滿足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消費區,建立穩定的生豬供應體系是第一要義。因此,首先,整體上需針對本區域內的生豬供應體系面臨的風險進行梳理分析,并對潛在的風險、問題等做好一一對應的應急預案,以期降低突發性事件或風險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豬肉消費市場的影響。其次,針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單一生豬供應模式的弊端,相關部門應該通過調研,探討建立適合本城市的多元化生豬供應模式,防止單一的生豬供應模式難以應對多重風險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生豬供應體系的沖擊,如調肉、動態凍肉儲備與調豬相結合多種生豬供應體系搭建,滿足終端消費和加工端對生豬的需求。同時,對于已建立定點生豬供應體系的城市群,需進一步優化定點供應生豬養殖基地的區域空間結構布局[18],以提高生豬供應體系應對各種風險的能力。最后,借助目前大數據技術等方式,構建科學的市場信息預警機制,對生豬市場供求數據進行動態管理[19-20],保證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生豬供應穩定。
3.2 食品安全視角
生豬供應穩定是保證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居民豬肉消費的基本要求,而保證供應高質量、安全可靠的豬肉則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生豬供應體系的核心。雖然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生豬供應穩定成為保障農產品供應重要的任務,但仍需繼續確保所供應的生豬質量是安全可靠的,因此在生豬定點供應或市場自由調入供應方面,監管部門必須繼續完善生豬養殖、流通屠宰加工、進口等全流程的監控制度,確保生豬供應質量安全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生豬供應體系存在的底線。另一方面,也需繼續完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供應豬肉的可追溯制度,雙保險確保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供應的豬肉質量安全可靠。此外,向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所供應的生豬出現質量安全問題的主體實行“一票否決”的清單制度,長期限制其向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供應各類生豬產品,以此確保各類途徑供應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豬肉產品質量安全可靠。針對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也是國內豬肉及副產品進口的主要目的地,相關部門應繼續加強進口的豬肉產品的抽檢、監管以及杜絕不安全的豬肉產品通過走私途徑進入市場。
3.3 合作視角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內城市間的全方面、多方位融合發展,也可在農產品供應體系特別是生豬供應體系方面,探索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生豬供應體系的合作模式,確保區域內的生豬供應穩定和質量安全可靠。一是基于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都基本建立了定點式的產銷對接模式的基礎上,各方管理部門通過溝通協調,實行定點供應的生豬養殖基地相互認證制度、流通規范制度和質量安全監管體系,多方監控,保障供應能力的穩定和生豬產品質量的安全可靠。二是基于當前大灣區各城市已建立生豬供應體系,在強化管理部門的監管功能的同時,積極與相關生豬產品供應企業進行合作,建立穩定的市場合作供應制度,提高生豬供應的質量和數量,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提供豐富優質的生豬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