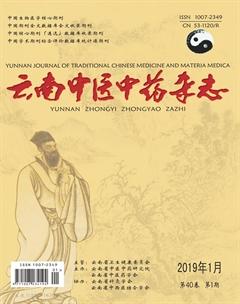運用血府逐瘀湯臨證經驗初探
于丁雯 高建忠 賀文彬
摘要:血府逐瘀湯,出自清代王清任的《醫林改錯》,是用于治療“胸中血府血瘀”的名方。高老師臨證時多強調立足脾胃,調暢氣血觀點的重要性,并將血府逐瘀湯靈活化裁運用于臨床各類雜病,取得較好的臨床療效。
關鍵詞:血府逐瘀湯;脾胃;氣血
中圖分類號:R24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2349(2019)01-0100-02
高建忠,副主任醫師、碩士生導師、山西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經方研究室主任,山西中醫藥大學中醫臨床學院副院長。長期從事經典方劑治療疑難雜病的臨床研究。筆者在跟師門診期間,觀察其在臨證時善立足脾胃,調暢氣血以治療疾病,且靈活運用血府逐瘀湯及其合方治療各類雜病,療效較好,現總結經驗如下。
1 立足脾胃,調暢氣血的辨證思路
1.1 以通立法,調暢氣血 氣的運動,稱之為氣機。導師認為氣機的流通,氣血的流暢至關重要。所謂氣血流暢,百病不生;氣血呆滯,百病叢生。故治病常以通立法,調暢氣血。
明代醫家繆希雍在《先醒齋醫學廣筆記》一書中指出:“天地之間,動靜之為者,無非氣也;人身之內,轉運升降者,亦氣也[1]。”金代醫家張從正在《儒門事親·凡在下者皆可下式》一書中說:“《內經》一書,惟以氣血通流為貴。世俗庸工,惟以閉塞為貴。又只知下之為瀉,又豈知《內經》之所謂下者,乃所謂補也。陳痤去而腸胃潔,癥瘕盡而榮衛昌,不補之中,有真補者存焉[2]”。臨床上,當遇到實證時,自然會選用血府逐瘀湯等方藥,以瀉實邪,調暢氣血。但是,不能眼光局限,血府逐瘀湯不單單可以治療實證,亦可用于虛證。
當遇到虛證時,往往會發現應用補法不效,此時當以條達氣血為務,氣血和暢,諸臟才能得以溫煦、濡養,才能恢復生機。因氣血不運,補藥只會徒增脹悶。亦如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中所說:“治病之要訣,在明白氣血[3]。”
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曾說:“氣血沖和,萬病不生,一有怫郁,諸病生焉。故人身諸病,多生于郁[4]”。朱丹溪認為諸病多因郁而生,他善用越鞠丸,立足中焦,重視中焦的氣機升降浮沉,以通立法,郁解則氣自行也;而血府逐瘀湯,則是立足氣血,重視人整體的氣血條暢,治氣滯血瘀而郁者,氣血行則郁解。郁就是不通,而不通既可以是氣分的不通,亦可是血分的不通;既可以是邪滯引起,亦可是正虛引起。血府逐瘀湯既活血祛瘀,又能行氣止痛,既行血分瘀滯,又解氣分郁結,且升降相施,氣血調和。所以,血府逐瘀湯以通立法,為治療邪實而郁所致的氣分與血分不通的良方。導師在臨床應用此方頗廣,不局限于病,而是隨證立法,屢有奇效。
1.2 重視后天生化,立足脾胃 東垣創立脾胃學說,在《脾胃論》卷中言:“歷觀(內經)諸篇而參考之,則元氣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氣既傷,而后能滋養元氣;若胃氣之本弱,飲食自倍,則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亦不能,而諸病之所由生也[5]。”東垣強調脾胃為元氣之本,而導師深受東垣“內傷脾胃學說”影響,臨床多立足脾胃,注重對脾胃的顧護。
李東垣在《脾胃論》中云:“夫內傷用藥之大法,所貴服之強人胃氣[5]。”導師臨證多次強調:“中醫治的不只是局部的病,更重要的是人的整體,若以損傷脾胃為代價的治療,是不可取的。”血府逐瘀湯為瀉法,且活血祛瘀易傷脾胃。導師在臨床運用血府逐瘀湯時發現,劑量過大易導致患者出現便稀、納食差、氣短等不良反應,所以常用劑量為甘草3 g,余皆為6 g,既可達到氣血條暢的目的,又防止力量過大,傷及脾胃正氣。并且此方通常只可暫用,不宜久服。在服藥期間逐步評估患者情況,酌情加入黃芪、黨參、白術等,甚或與枳術丸、四君子湯、保和丸等方合用,以補益正氣,顧護脾胃。這樣才能達到祛瘀而不傷正,活血而不傷血的治療目的。
2 相關方藥介紹
2.1 血府逐瘀湯源流 所謂“血府”,清代醫家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中提出:“血府即人胸下膈膜一片……低處如池,池中存血,即精汁所化,名曰血府。”而血府逐瘀湯,就是用于治療“胸中血府血瘀”[3],書中主要列述病癥有“頭痛”,“胸痛”,……“干嘔”,“晚發一陣熱”等。
晚清醫家唐宗海[6]所著《血證論》中所述:“王清任著《醫林改錯》,論多粗舛,惟治瘀血最長……凡癆所由成,多是瘀血為害,吾于血癥諸門,言之纂祥,并采此語為印證。”
筆者對血府的部位理解更廣闊,不單是“胸下膈膜一片”,而是引申為整個上焦;而中醫上講肝為藏血之藏,亦可以把血府引申為肝,將血府逐瘀湯治療部位由血府擴大至上焦和肝。現代醫家認為凡由血瘀所致的各類雜病,均可用之。但應用時需要辨明病癥是否有瘀血之征象。
2.2 血府逐瘀湯用方思想 王清任在書中提到“治病之要訣,在明白氣血,無論外感、內傷……所傷者無非氣血[3]。”即不管疾病分屬外傷或者內感,均會累及氣血,所以王清任認為治病的前提是要調和氣血。而血府逐瘀湯便是他在血府以及氣血的理論基礎上創立了的用以治胸中血府血瘀的一代名方。
2.3 方中配伍意義 血府逐瘀湯的配伍,始終圍繞著如何活血祛瘀,行氣止痛進行,全方共奏氣血兼顧,活血不傷血,升降同用,祛瘀下行的制方特點。方中君藥、臣藥共助活血祛瘀之功;佐藥助行氣滋陰,使氣行血行,祛瘀不傷正;最后甘草為使藥,可以調和諸藥。肖勇[7]認為,在血府逐瘀湯的配伍中,桃仁、紅花、川芎、當歸構成活血藥組,柴胡、枳殼構成理氣藥組,諸藥合用,既能活血祛瘀,又能行氣止痛,既行血分瘀滯,又解氣分郁結,且升降相施,氣血調和,則諸癥可愈,為治胸中血府血瘀證之優良組合。
3 驗案舉例
患者張學軍,男,46歲,2018年1月2日初診。間歇性偏頭痛20余年,再發1周。患者偏頭痛20余年,有時左側有時右側。每年于入夏前發作,多為憋脹痛,伴冷汗出、煩躁。每次發作可持續20余天。2009年自服“鹽酸洛美利嗪片”、“煙酸肌醇酯片”、“布洛芬緩釋膠囊”等藥物治療,有3~4年未發作。近3~4年頭痛再發,去年入夏前仍有發作。1周前無明顯誘因頭痛再犯。診見:左側偏頭痛,有憋脹感,伴冷汗出、煩躁。納眠可,大便日1行,小便調。舌質暗紅,舌體大,舌苔白粘,脈象細緩。既往高血壓病史3~4年,口服“康忻”、“海捷亞”治療,目前血壓控制良好。辨證:氣滯血瘀,脾虛痰滯。治法:活血祛瘀,健脾化痰。處方:炒雞內金15 g,茯苓15 g,鉤藤15 g,桃仁6 g,紅花6 g,當歸6 g,生地黃6 g,川芎6 g,赤芍藥6 g,柴胡6 g,枳殼6 g,牛膝6 g,桔梗6 g,生甘草3 g。7劑,水沖服。2018年1月9日二診:近幾日頭未痛,自覺前額不舒。舌質暗,舌苔白,脈象細緩。處方:炒雞內金15 g,黨參9 g,鉤藤15 g,桃仁6 g,紅花6 g,當歸6 g,生地黃6 g,川芎6 g,赤芍藥6 g,柴胡6 g,枳殼6 g,牛膝6 g,桔梗6 g,生甘草3 g。7劑,水沖服。
2018年1月16日三診:病情平穩。舌質暗,舌苔薄白,脈細緩。
處方:炒雞內金15 g,黨參9 g,全瓜蔞15 g,桃仁6 g,紅花6 g,當歸6 g,生地黃6 g,川芎6 g,赤芍藥6 g,柴胡6 g,枳殼6 g,牛膝6 g,桔梗6 g,生甘草3 g。7劑,水沖服。至2018年6月間斷因他病就診,頭痛未再犯。
按:王清任在《醫林改錯》書中提到過:“查患頭疼者,無表癥,無里證,無氣虛、痰飲等癥,忽犯忽好,百方不效,用此方一劑而愈。”而這個患者就恰恰符合了以上幾點,遂選擇血府逐瘀湯。再觀患者舌質暗紅,提示氣血失暢,結合患者此時病況左側偏頭痛,有憋脹感,伴冷汗出、煩躁,應屬氣滯血瘀;而舌體大,舌苔白黏,脈象細緩,且患者每年于入夏前發作,頭痛可能與痰濕有關,考慮為瘀血阻滯影響脾胃運化導致痰濕瘀滯。高老師臨床運用血府逐瘀湯,常用劑量為甘草3 g,余皆為6 g,防活血祛瘀過度而傷及正氣。此病案在運用血府逐瘀湯的基礎上加鉤藤以清熱平肝,清利頭目;加茯苓以健脾祛濕安神;加瓜蔞以清化痰熱痰;加黨參以補氣健脾。此外,方中一味消食運脾之要藥雞內金,幫助顧護脾胃。縱觀全方,以通立法,立足脾胃,共奏調暢氣血,健脾化痰之效。
此患者病情看似無處下手,然經久不愈,痛處相對固定的頭痛多考慮為瘀血頭痛,而患者的表現又符合《醫林改錯》中血府逐瘀湯治療頭痛的準則。高老師也在《高建忠讀方與用方》書中提到:“廣用、活用血府逐瘀湯,著眼于久病不愈,著眼于疑難病證[9]。”所以,患者辨證為實證,為氣滯血瘀,脾虛痰滯所致。當選用血府逐瘀湯以活血祛瘀,行氣止痛,健脾化痰,其充分體現了導師以通立法,調暢氣血,立足脾胃的思想,也達到祛瘀而不傷正,活血而不傷血的治療目的。雖不似《醫林改錯》中所述方一劑而愈,但是三診即愈并且至今未復發也是療效奇佳了。
參考文獻:
[1]繆希雍.先醒齋醫學廣筆記[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44.
[2]張從正.儒門事親[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22.
[3]王清任.醫林改錯[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8.
[4]朱丹溪.丹溪心法[M].沈陽:遼寧科技出版社,1997:1-115.
[5]李東垣.脾胃論[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4.
[6]清·唐宗海.魏武英,李佺整理.血證論(中醫臨床必讀叢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5.
[7]肖勇.試論血府逐瘀湯中活血藥與理氣藥配伍的核心意義[J].江西中醫藥,2014,4504:12-13.
[8]高建忠.高建忠讀方與用方[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8.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