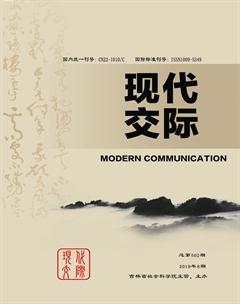“交往形式”范疇與“生產關系”范疇的關系探究
郭久強
摘要:《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關系”等術語與“生產關系”并不完全等同。馬克思、恩格斯將“市民社會”“所有制”等范疇作為確定“交往形式”等術語與“生產關系”雙方之間關系的媒介,進而展現出“交往形式”等術語與“生產關系”概念等同的一面。“交往形式”等術語作為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論的內容,其在文本中所具有的原初含義又決定了其與“生產關系”概念不同的一面。
關鍵詞:交往 交往形式 生產力 生產關系
中圖分類號:A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9)08-0216-04
《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中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關系”等這些術語與“生產關系”概念的關系問題一直以來備受爭議。爭議的形成根源在于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在其所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中有關《形態》部分,都給出了這樣一段注釋:“《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用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關系‘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這些術語,表達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生產關系概念。”[1]但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在《形態》的一些段落中,“生產關系”并不能全權代表“交往形式”等術語。由此,許多學者認為中共中央編譯局所給出的這種注釋有待商榷,他們將自己的觀點訴諸筆端與中共中央編譯局及學術界同僚進行探討,從而引起了對該問題的學術爭鳴。
總觀目前學界討論概貌,對于交往形式的討論主要有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是“交往形式”等術語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生產關系”概念,雙方可以同義替換。這種觀點常見于發表于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的論文中,學者們往往以“交往形式就是指生產關系”一筆帶過。但更多的學者還是贊同這種觀點:“‘交往形式有其自身的內涵和理論地位,把它等同于‘生產關系是對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論的一種誤解。”[2]
雖然已經有太多學界前輩對該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但是,只有做到常想常思,思想理論才能保證其常思常新。不斷深入探究和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每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的義務和責任。因此,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對這些“迷”一樣的思想進行探討都不會多余。在進行詳細論述以前,首先需要確定生產關系的概念,以此作為參照考察雙方關系。本文根據學界對于生產關系概念所形成的普遍共識,將該術語統一界定為人們在直接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相互關系,主要內容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以及產品的分配方式。下面,本文將從“交往形式”與市民社會、“交往形式”與所有制、“交往形式”自身所具備的本原含義等方面來論證雙方概念的同與不同
一、“交往形式”等術語與生產關系概念等同
為了便于分析,本文將直接用“交往形式”來替代“交往方式”“交往關系”等術語。在《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直接明確地界定“交往形式”的概念,但仔細分析文本可以發現馬克思、恩格斯并非完全沒有交待。要充分把握“交往形式”的具體內涵需要經過轉換,即“交往形式”的旨趣是借助市民社會、所有制和“這些條件”“生存條件”等內容間接闡釋的,而這三個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都指涉了生產關系的概念。因此,“交往形式”通過市民社會、所有制和“這些條件”等來牽線搭橋實現了與生產關系的連接,進而推斷出“交往形式”與生產關系雙方等同的關系。為了便于理解,本文將之比喻為三座橋梁:“交往形式”—市民社會—生產關系、“交往形式”—“所有制”—生產關系、交往形式—“這些條件”—生產關系。
橋梁一:“交往形式”—市民社會—生產關系。市民社會是《形態》中的重要概念,同時也是理解“交往形式”的突破口。原因在于,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被不同歷史時期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發展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3]此外,“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4]根據引文可知,《形態》中的“交往形式”在特定的段落可理解為“市民社會”概念。由此,借助馬克思、恩格斯對“市民社會”的闡釋,我們可以間接地理解“交往形式”的相關內涵。
那么,馬克思、恩格斯又是如何定義“市民社會”的呢?在《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論述道:市民社會是一種社會組織,它是從生產與交往中發展而來,“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5]市民社會這種社會組織之所以能夠作為國家構成和上層建筑的基礎,原因在于社會組織并非“動物式”的人的集合,而是一種以生產關系連接起來的共同體。據此推斷,馬克思、恩格斯將“市民社會”理解為國家和其他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而經濟基礎又是指在一定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進而,交往形式通過“市民社會”這個中介與生產關系取得了間接關聯,得出“交往形式”具有與生產關系等同的概念。
橋梁二:“交往形式”—所有制(私有制)—生產關系。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這種矛盾”在過去的歷史中曾發生過多次,表現為革命和各種形式的斗爭沖突,成為“一切歷史沖突的根源”。[6]此處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將“生產力”與“交往形式”并列使用了。根據我國思政課教材的編寫慣例,通常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并列使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并列使用。那么,我們能否將這里的“交往形式”解釋為生產關系呢?即能否轉化為“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呢?筆者認為是可以的。但這需要借助私有制得出生產關系與“交往形式”二者等同關系的結論。筆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這里所指涉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就是“生產力和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原因有二:
首先,在提到“一切歷史沖突的根源”之前,馬克思、恩格斯還指出私有制是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在私有制的統治下,這些生產力只獲得了片面的發展”,許多生產力都得不到有效利用,且私有制的統治對大多數人而言成了破壞的力量。[7]由此可以看出,私有制掣肘了生產力的發展,二者的矛盾成為“沖突的根源”。它不僅造成了生產力的片面化發展,也造成了工人糟糕的生活境遇,引起了社會各階級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這種矛盾與沖突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提及的革命以及各種附帶形式的沖突。這種矛盾和沖突易于爆發,以至于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不用等到其“發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才引起國內斗爭,僅是工業化水平不對等的國家之間的競爭就足以引發這種問題。對此,馬克思、恩格斯以英國的工業對德國無產階級的出現的影響為例進行論證。總而言之,上述的這種矛盾是由大工業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和對其他階級的剝削而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所引起的。因此,表面上看歷史沖突的根源是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造成的,但從本質上來說,這種矛盾其實是由于私有制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所引發的結果。
接著,馬克思、恩格斯還繼續談到,“這種單個分開的家庭經濟由于私有制的進一步發展而更加必需的了”。[8]“單個分開的家庭經濟”的出現離不開私有制的發展,前者成為后者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這種“單個分開的家庭經濟”并不適合未來的社會形態,與之相匹配的應該是“共同的家庭經濟”。但是“共同的家庭經濟”要以“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作為其實現的條件。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即實現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統一,這就意味著要消滅私有制。[9]但現實情況是私有制不斷發展,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影響著整個社會,阻礙著“共同的家庭經濟”的實現。“共同的家庭經濟”的實現條件不具備,“共同的經濟本身將不會再成為新生產力”,故此,生產力受到阻礙。[10]因此,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現實與他們所期望的未來之間存在著一股張力,這股力量就是源于私有制的發展。
綜上所述可知,私有制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由此,我們可將“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替換為“生產力和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得出“交往形式”等同于私有制的結論。
至此,我們已完成了“‘交往形式—私有制”這一環節的論證,那么,所有制(私有制)又和生產關系又有什么聯系?馬克思、恩格斯又是如何論述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借助一個概念:分工。在《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不同階段的分工,同時也就是各種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分工和私有制表達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而且,“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根據個人與勞動的材料、工具和產品的關系決定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11]具體分析,“‘個人與勞動的材料、工具的關系指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個人和勞動產品的關系指的是產品的分配方式;‘人們相互之間的關系指的是各種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根據個人與勞動的材料、工具和產品的關系決定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指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各種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12]通過所有制我們看到了馬克思、恩格斯后來所提出的生產關系概念的雛形,所有制(私有制)已經包含了生產關系的“三要素”。因此,所有制(私有制)亦即“交往形式”具有生產關系的含義,“交往形式”可理解為生產關系。
橋梁三:交往形式—“這些條件”—生產關系。為了便于論述,筆者根據這部分討論需要,將《形態》中的相關引文按其在文本中的先后順序摘錄如下:
引文1:這種在一定條件下不受阻礙地利用偶然性的權利,迄今一直稱為個人自由。——這些生存條件當然只是各個時代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13]
引文2:在后來時代(與在先前時代相反)被看作偶然的東西,也就是在先前時代傳給后來時代的各種因素中被看作偶然的東西,是曾經與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水平相適應的交往形式。[14]
引文3:個人相互交往的條件……在這些條件下,生存于一定關系中的一定的個人獨力生產自己的物質生活以及與這種物質生活有關的東西,因而這些條件是個人的自主活動的條件,并且是由這種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馬克思加了邊注:“交往形式本身的生產”)。[15]
引文4:這些不同的條件,起初是自主活動的條件,后來卻變成了自主活動的桎梏,這些條件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構成各種交往形式的相互聯系的序列,各種交往形式的聯系就在于: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于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于進步的個人的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后又為另一種交往形式所代替。[16]
引文5:……較早時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經為屬于較晚時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擠之后,仍然在長時間內擁有一種相對于個人而獨立的虛假共同體(國家、法)的傳統權力,一種歸根結底只有通過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權力。[17]
引文6:可見,這些國家在開始發展的時候就擁有老的國家的最進步的個人,因而也就擁有與這些個人相適應的、在老的國家里還沒有能夠實行的最發達的交往形式。……這種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國還受到以前時代遺留下來的利益和關系的牽累,而它在這些地方卻能夠而且應當充分地和不受阻礙地確立起來……[18]
引文7:貨幣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為對個人來說是偶然的東西。[19]
在引文1、2、3、4、5、6、7及這些引文前后的文本中,筆者注意到,馬克思、恩格斯頻繁地使用了“這些條件”和“自主活動”等詞匯。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條件”還被表述為“這些生存條件”“這些條件”“一定條件”,等等,為便于論述,筆者將在后文統一使用“這些條件”。那么,對這些詞句的把握是否對于我們理解“交往形式”的含義有幫助呢?
首先,我們需要明確一點,那就是“這些條件”包含有“交往形式”的內容。毫無疑問,只有證明了“這些條件”和“交往形式”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等同性,我們才有繼續探討“這些條件”的必要。那么得出二者具有等同性的原因在于,第一,馬克思、恩格斯在引文1就明確交代了“這些條件當然只是各個時代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第二,根據引文3可以得出,“這些條件”是自主活動的條件,“這些條件”又是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第三,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給出的邊注:這種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就是“交往形式本身的生產”。綜合以上三點即可得出“這些條件”就是“交往形式本身的生產”。進而言之,“這些條件”經歷了由起初適應自主活動到成為其桎梏的角色轉變,使得自主活動不斷地演變,進而形成了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構成了各種交往形式相互聯系的序列。在《形態》中有這樣一句話可以作為參考,雖然它被馬克思、恩格斯刪掉了,即:“在每一個歷史時代獲得解放的個人只是進一步發展自己已有的、對他們來說是既有的生存條件。”[20]所謂既有的生存條件,也就是人們自主活動的條件,更是人們從上一輩人那里繼承下來的交往形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這些條件”不同,“交往形式”也就不同,它們在歷史發展中一一對應。如同分工和私有制之間的關系一樣,“這些條件”和“交往形式”表達的是同一件事情。
歸根結底,“這些條件”是什么意思呢?馬克思、恩格斯在引文7前后都給出了答案:“在大工業和競爭中,各個人的一切生存條件、一切制約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為兩種最簡單的形式——私有制和勞動……這些條件可以歸結為兩點:積累起來的勞動,或者說私有制以及現實的勞動”。[21]現實的勞動也就是生產力,而私有制在前文中已經論述過了,就是生產關系。進而也不難看出,引文7中的“私有制和勞動”與引文1中的“這些生存條件當然只是各個時代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相對應,從而更加證實了筆者的觀點。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先讓交往形式和“這些條件”建立聯系,然后再表明“這些條件”指涉了私有制,進而最終間接地表明了“交往形式”與私有制的關系。這一結果也再次印證了前面所論述的“交往形式”等同于私有制的合理性。這也呼應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寫作“費爾巴哈”章節伊始就談到的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以及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這三種所有制形式。由此可見,所有制在《形態》中占據重要地位,是打開生產關系與“交往形式”雙方關系之謎的鑰匙。
二、“交往形式”等術語與生產關系概念不同
至此,筆者基于文本分析得出了“交往形式”與“生產關系”概念等同的結論。但此時還不可以就這樣對雙方關系蓋棺定論,否則很可能造成對生產關系和《形態》中的“交往形式”理解得不夠全面和徹底,“交往形式”和生產關系之間的另一面,即“交往形式”不等同于生產關系就會被遮蔽。應看到,馬克思、恩格斯還有意賦予“交往形式”其特殊的歷史使命。
首先,市民社會本身就具有多重含義。承接前文所得出的馬克思、恩格斯將“交往形式”作為市民社會理解的觀點,對市民社會的內涵挖掘的越充分,“交往形式”的內涵就越顯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這一術語有兩重含義。廣義地說,是指社會發展各歷史時期的經濟制度,即決定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物質關系總和;狹義地說,是指資產階級社會的物質關系。”[22]在《形態》中,市民社會包括一定時期的一切物質交往,包括某個時期的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雖然它對外要作為民族,對內要組成國家,但是它也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范圍。市民社會是歷史的發源地和舞臺,這也符合資產階級社會的特征。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指出市民社會是同資產階級的發展而起來的。據此我們可以指認“此時馬克思、恩格斯主要用交往形式和市民社會來指稱資產階級社會”[23]。所以,從這個層面看來,“交往形式”又不等同于生產關系。
其次,“交往形式”有其本原意義,呈多樣性。在《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提及了多種形式的交往,如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內部交往和外部交往、區域交往和普遍交往,個人交往和集體交往,等等。此外,馬克思、恩格斯還明確地把戰爭作為一種常用的“交往形式”,這種“交往形式”是“先前時代”“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產生的主要方式,它自身不僅作為一種“交往形式”,而且也帶動了其他“交往形式”的介入。另外,很顯然,馬克思、恩格斯還把交換作為交往來理解,交換形式即是一種“交往形式”。商品交換不僅是一種物品交易,它反過來也成為人自身的束縛。交換活動影響著人們之間的連接,也影響著民族及國家之間的關系。“用一位英國經濟學家的話來說,這種關系就像古典古代的命運之神一樣,遨游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見的手把幸福和災難分配給人們,把一些王國創造出來,又把它們毀掉,使一些民族產生,又使它們衰亡。”[24]另外,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催生出了許多“交往形式”,其中就包括“保險公司”。這些都是從“交往形式”的本原意義上來理解的,不牽扯別的引申義。
再次,從“交往形式”的作用來看。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關系等術語與“交往”始終是形式與內容、葉與枝的關系。如果我們只談形式而不談內容,那么形式和關系必定都是空洞的。相反,只談內容不講形式、關系,內容也無法展現和外化出來。因此,交往中必定包含著“交往形式”“交往關系”等內容,而“交往形式”“交往關系”又是交往所不可或缺的載體。盡管馬克思、恩格斯在《形態》中主要從“交往”來論述交往理論,即交往是確立人本質的前提、交往促進了分工的發展、交往的擴展是生產力(文明)得以存續的保障、交往影響著共同體之間的關系以及普遍交往的建立確保共產主義得以實現,但無論“交往”這一內容如何豐富,它都必然包含了“交往形式”,都必須借助一定的“交往形式”才能表現出來。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借助“交往形式”闡發了交往理論的思想。僅憑這一點,“交往形式”就不等同于生產關系。
三、回應質疑
要確保本文所得出的“交往形式”與生產關系具有等同的一面這一結論的正確性,還需要對文本中的一句話進行合理解釋,這句話也是眾多學者不贊成“交往形式”等術語等同于生產關系的理由。那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形態》中所提到的“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并且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作前任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它們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25]據此,大部分學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提出了“生產關系”這一術語,如果“交往形式”也有生產關系的概念,那么這里馬克思、恩格斯顯然是贅述了,而馬克思、恩格斯顯然是不可能犯這種低級錯誤的。所以他們堅持認為:“交往形式”等術語與生產關系不等同。這種觀點顯然是沒有全面理解“交往形式”等術語的內涵,并非文章中出現的所有“交往形式”都能解釋為生產關系,而是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因為“交往形式”等術語的內涵要遠遠大于生產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在此使用的生產關系這一術語指的是人們在物質生產中所結成的社會關系,與物質交往相關,而此處的交往關系則是對除了物質生產關系以外的其他關系的概括。所以,此處生產關系不等同交往關系,但這并不代表其他地方雙方也是不等同關系。
為什么馬克思、恩格斯后來用生產關系來替代“交往形式”而不繼續使用“交往形式”這一術語呢?從《形態》文本中可以找尋到原因。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26]雖然生產是以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為前提,但是交往的形式又由生產決定,即表明了物質生產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占據主導作用。所以,即使馬克思、恩格斯在《形態》中所使用的生產關系僅指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之間的物質關系,但由于生產的這種決定性的作用,在其普照光的影響下,始終代表物質交往的生產關系自然而然地涉及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對人類發展影響最大的一種社會關系,進而馬克思、恩格斯后來漸漸用生產關系取代了“交往形式”。
參考文獻:
[1][3][4][5][6][7][8][9][10][11][13[14][15][16][17][18][19][20][21][22][24][25][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7-868.
[2][23]許斗斗.《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交往形式”理論新釋——析“交往形式”即“生產關系”的觀點[J].東南學術,1999(2):56-58.
[12]趙家祥.解析《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一個難解之謎——“生產關系”概念與“交往形式”等術語的關系[J].哲學動態,2011(4):5-10.
責任編輯:楊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