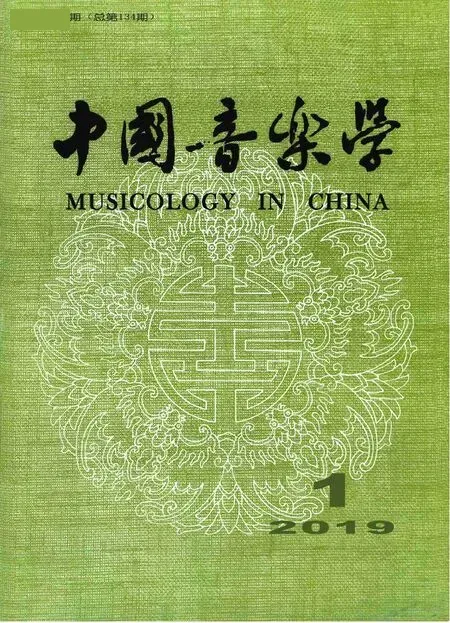“審美參與”:音樂審美經驗的身體化建構
2019-05-23 13:30:56王文卓
中國音樂學
2019年1期
□王文卓
從學科形成角度說,美學問題是知識學問題,其理論疆域及概念間邏輯的形成是人類對“情”知識不斷進行確認的結果。美學知識的合法性始終與具體審美實踐相聯系,情感實踐的拓展及感性樣態的出新必然引起對固有美學概念的反思。當下,對審美經驗這一概念的反思與重構成為一個十分突出的理論問題,主要動力來自于當代美學研究對身體與意識、藝術與生活、通俗與高雅等一系列二元對立觀念的反駁。“審美經驗的身體化”就是其中較為重要的議題之一。
學界對音樂審美經驗的身體化問題已有探討,但理論上還需進一步探索并選擇合適概念或范疇闡釋這種現象。“身體化”僅在現象的一般性層面進行表達,還難以揭示音樂審美“體化實踐”(incorporated practisces)①這一概念由美國人類學家保羅·康納頓(Paul Connerton)在《社會如何記憶》一書中提出,“體化實踐”與“刻寫實踐”是人類記憶實踐的兩種形式,“體化實踐”意在說明身體行為在信息記憶與傳播中的重要作用。蕭梅曾借用這一概念來闡釋身體在中國傳統音樂傳承中的重要價值。從音樂審美經驗的角度說,這一概念將表達出身體的理性積淀與感性表達的基本關系。的豐富性。由此,本文試圖借助由阿諾德·柏林特(Arnold Berleant)的“審美參與”(aesthetic engagement)②阿諾德·柏林特(1932~),國際美學會前主席,美國長島大學榮譽退休哲學教授。“審美參與”是柏林特美學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據他本文所述,“審美參與”首次使用于1967年的《經驗與藝術批評》一文中。……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杭州(2023年3期)2023-04-03 07:22:36
美食(2022年2期)2022-04-19 12:56:08
黨課參考(2021年20期)2021-11-04 09:39:46
阿來研究(2021年1期)2021-07-31 07:38:26
新世紀智能(高一語文)(2020年9期)2021-01-04 00:42:46
小哥白尼(軍事科學)(2019年6期)2019-03-14 05:49:56
黨課參考(2018年20期)2018-11-09 08:52:36
Coco薇(2017年8期)2017-08-03 02:01:37
Coco薇(2015年5期)2016-03-29 23:16:36
新課程研究(2016年21期)2016-02-28 19:2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