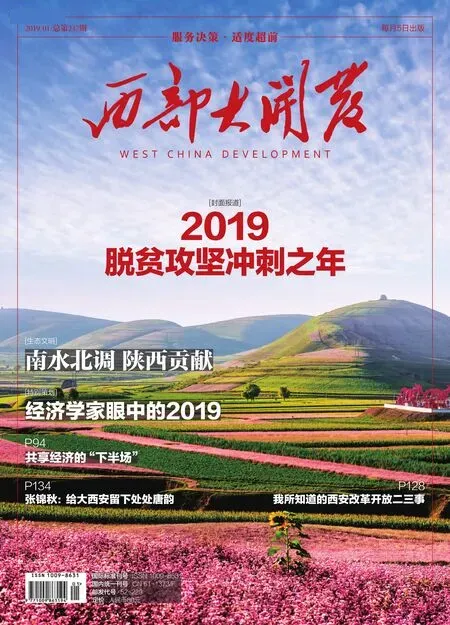共享經濟的“下半場”
文 / 本刊記者 王薇
2018年12月,大概是ofo最難熬的日子。在位于中關村互聯網金融中心的ofo總部,前來上門討還押金的隊伍從五樓排到一樓,又從大堂延伸到馬路上。焦灼萬分的ofo創始人戴威通過一封“內部信”向1000多萬用戶道出承諾——“ofo要為我們欠著的每一分錢負責,為每一個支持過我們的用戶負責”。口頭上的承諾并沒有使用戶們放松警惕,ofo作為共享單車領域的創始者與引領者,還是陷入了近乎“敗局”的困境。除去創始人和團隊的管理失控、各路資本利益方的復雜博弈,資金缺口甚至成為導致ofo難以為繼的直接原因。
作為共享經濟的代表行業,共享單車曾經炙手可熱,甚至2017年人們都還在感慨原來生活中的諸多難題都可以通過共享的方式來解決,共享經濟一夜之間更新了人們的生活觀念與方式,但似乎也是一夜之間,共享經濟就從欣欣向榮的“康莊大道”轉向了不可收拾的“一地雞毛”。讓人不禁懷疑,共享經濟是否已進入寒冬?強弩之末的共享經濟模式是否大勢已去?
“大起大落”的“上半場”
本刊曾在2018/04(總第229期)《共享經濟:從一地雞毛到鳳凰涅槃》一文中提到,“共享經濟是一種創新,它不僅人人享有,人人參與,使消費與生產深度融合,而且將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帶來資源利用率的提升。”這種優越性不僅恰到好處的便利了人民生活、引導了消費的升級,更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方面意義重大。

共享充電寶
但如此突出的優越性并不能掩蓋共享經濟在運轉不利中帶來的瘋狂后果。不只是單車,整個共享經濟領域,很多新鮮事物都可謂曇花一現。在被視作共享經濟元年的2017年,共享充電寶、雨傘、汽車、服裝等,讓人應接不暇。沒有清晰的商業模式和盈利邏輯,并不妨礙共享模式在資本市場快捷融資。以共享單車為例,《2017年度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底,國內共有77家共享單車企業,累計投入了2300萬輛單車,當年融資金額達258億元。
冷靜反思的“中場休息”
共享經濟前期的爆發式增長回落后,其運營模式的弊端開始顯露出來,“下半場”隨之而來的是資本冷靜下的“大浪淘沙”。
真共享還是偽需求?
當共享經濟的泡沫破滅時,人們開始思考,共享經濟的本質究竟是什么?是社會閑散資源實現自由組合和效率最大化,還僅僅是商業租賃行為?
在資本的推動下,當下許多模式通過繳納押金、按時租賃的形式為用戶提供服務,這與共享經濟的本質相差甚遠,更像是“租賃商業行為”。
打造共享居住的Airbnb(愛彼迎),在中國市場的不景氣,體現了中外家庭隱私觀的差異、社會誠信水平的高低以及中國廉價酒店行業高度競爭的現實狀況,脫離商業環境的推廣運營,必然會造成共享模式下的“水土不服”。
盲目跟風下的資本泡沫
過熱的資本往往引發創業者的盲目跟風,這也能從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么會出現共享雨傘、共享籃球、共享睡眠倉、共享按摩椅等各式各樣的類目。
扎堆式的盲目發展存在不小的泡沫。從經濟學上來講,作為“產業”或“生意”的共享經濟應該有其盈利預期。但在資本的瘋狂角逐之下,共享單車時常推出類似于5元騎一季度的競爭策略,成為企業不可承受之重;為搶奪市場占有率,單車大量且無序投放的現象層出不窮,一排排嶄新的自行車不僅消耗大量的資本,占據大量的擺放空間,也導致城市街角擁擠不堪。
資本的跑馬圈地使得共享經濟行業儼然已經出現了供需失調、甚至是供過于需的狀況。這時候,從社會經濟效率層面上看,它是“非經濟的”,而非“經濟的”。

Airbnb(愛彼迎)共享居住
龐大體系運轉之下的管理之殤
2017年中國共享單車市場概況及用戶行為分析顯示,52.9%共享單車用戶表示聽說過共享單車被丟入江中、掛樹等相關新聞。此外,共享單車的二維碼被毀、亂停亂放、零部件被偷等影響使用現象的報道也得到廣泛傳播。近40.0%的用戶表示曾見過單車二維碼被毀、車鎖被撬等惡意影響使用現象,超過30.0%曾見過共享單車被亂停亂放、故意破壞。據艾媒咨詢分析指出,目前缺乏對共享單車相關破壞行為的有效監督,人為破壞影響用戶體驗的同時,會進一步提升共享單車運營成本。
組串式并網光伏逆變器的MPPT路數有1~5路,集中式逆變器的MPPT有1~3路,集散式逆變器則把匯流箱和MPPT升壓集成,有多路MPPT。從減少失配的角度出發,MPPT路數越多失配越少,但從可靠性的角度出發,MPPT路數越多損耗就越嚴重,經濟效益越低。通常當兩者失配超0.5%以上,多路MPPT的價值才能體現。故需結合當地實際,根據不同地形、光照,選擇不同的逆變器,降低投入,提高經濟效益。
而共享經濟的成長速度之快,也常常令創始人和管理者措手不及。界面新聞針對ofo創始人的文章《棄子戴威》中提到:“管理是戴威唯一自己承認過的弱點。‘我并不認為在個人能力、做事能力上甚至融資能力上有問題,如果一定說有問題,那就是在管理上’。”管理的弱點像一把鈍刀子一般,日復一日的劃刻在共享這個新生經濟模式的鮮嫩表皮之上,經過長久的堅持,最終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否還有“深思熟慮”的“下半場”?
共享經濟大退敗只是資本寒冬的一個縮影,低谷可能還遠未到來。但不可否認,不管是人人參與、人人享有的發展模式,還是以信用體系為基礎的經濟行為,都將成為提高社會經濟效率的必然趨勢。因此資本市場的轉冷會更加突出那些真正優秀的模式和公司,而在共享經濟的“下半場”,也必將回歸本質與理性。
消費者能否共享風險?
對于消費者而言,成為共享經濟的消費者不僅僅是一次鮮活的共享行為體驗,也是在嘗鮮各色共享時的一個個風險提示,背后則是市場風險的共享。


共享汽車
2018年4月11日,據英國勞埃德(Lloyd's)《共享風險:誰應該在共享經濟中承擔風險》報告中公布的調查結果,中國消費者最愿意使用這些平臺,即使他們認為有風險。大約68%的中國消費者認為,使用共享經濟的好處大于風險,而持這一觀點的美國消費者占58%。報道還稱,大約71%的中國消費者認為,平臺提供商,比如優步和愛彼迎,應當提供保險來維護消費者利益,另有21%的中國消費者稱保險的事應該由房主和車主負責。從區域來看,中國受訪者更喜歡共享經濟,無論是作為提供方還是消費者。相比之下,近一半的美國人從未使用過共享經濟(49%)。
由此可見,相比較而言,共享經濟在中國擁有更好的“市場環境”。但從2017年酷奇單車“退押難”到2018年ofo“退押難”,共享經濟的外部環境也在給消費者以關注“共享風險”的警示。
創業者能否回歸商業?
在共享經濟大打價格戰的一兩年里,背后依靠的正是資本帶來的強有力補貼。在資本的助推之下,共享單車的發展已經脫離了商業的本質。但同時,沒有資本的作用,共享單車可能發展10年甚至20年都達不到過去一兩年的進程,資本就好像摁下了快進鍵一樣,加速了這一行業的發展、整合和淘汰。
如今,外來的輸血不再給力,而自身的“造血模式”還沒有修煉成功,取消補貼等優惠政策,必然引起外界熱議和質疑,甚至涉及到一些企業的生死洗牌。而如何實現資源的管控與體系的正常運轉,以撐起這個龐大運轉體系,卻是這些創業公司缺乏思考的問題。
《共享經濟大敗局》中提到,“在資本的推動下,當下許多模式通過繳納押金、按時租賃的形式為用戶提供服務,這與共享經濟的本質相差甚遠,更像是‘租賃商業行為’。既然是租賃商業行為,就要回歸到商業本質,如何實現盈利才是創業者們的最終課題。”
監管者能否迎難而上?
伴隨著共享經濟的迅速發展,共享經濟監管的問題也開始進一步凸顯——已經出臺的一些措施明顯失當又引發了一些新問題,對新經濟業態缺乏了解也讓監管方有無從下手之感。
共享經濟的快速滲透和廣泛普及,引發個人信息安全、押金風險、社會福利等用戶權益保護難題。在平臺責任界定不清、誠信體系不健全以及先行賠付機制缺乏等情況下,共享經濟面臨“監管難、取證難、維權難”的挑戰。
網約車、共享單車、共享汽車、共享停車位、房屋短租、外賣配送等新業態、新模式的出現,都會對原有的城市規劃、配套設施、公共空間資源管理方式等產生沖擊,也給政策制定帶來很大困擾。
當然,共享經濟存在的問題不止以上方面。共享經濟起步較晩,發展太快,變化也快,很多是跨行業、跨領域、跨地區,涉及人數眾多,相應的統計監測體系難以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來也無可厚非。但更為棘手的是,即使發現了問題所在,也知道了利益相關方各自的訴求所在,實際監管起來也還會面臨手段缺乏的問題。
因此,在共享經濟這個新業態不斷發展的前提下,一定會出現層出不窮的監管問題。而監管者如何在共享經濟問題的“泥沼”中不斷突破和創新,是創造良好共享外部環境的必然之舉。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師、分享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新紅說:“共享經濟發展才剛剛開始,監管創新永遠在路上。中國共享經濟已經開始引領全球,說明過去的監管方針是行之有效的。對于創新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需要在實踐中創新性地去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