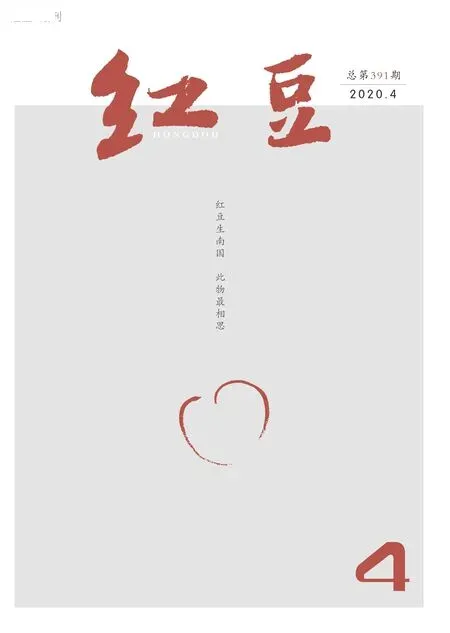般若與先驗
趙焰
緣起
《彼岸》與《無常》這兩部長篇小說的創作,時間跨度都很長,一直在陸陸續續地寫,也陸陸續續地改。一部分內容,也曾經發過。這兩部小說,像是栽下的兩株樹,我也看著它長大,它看著我變老。樹能不能長高長大不重要,重要的是過程,與樹木一同成長的過程。
小說有無數種寫法。我寫小說,一定要寫那種幾十年后還想看還能看還說好的東西。那些為當下而寫、為功利而寫、為人情而寫的東西,我是不會動筆的。人的時間本來就少,寫一堆自己都不想寫的東西,無疑浪費生命。發發呆也比寫那些東西好啊!我想寫人性的根本,世界的根本,想捕捉到生活的光影。我寫作,是因為我有想寫的東西。我從不奢望從寫作中得到什么。
原本是三部曲的,《無常》《彼岸》之外,還有一部《色空》。《色空》會把讀者嚇一跳。不能強求,只能繼續等。
一部長篇小說的成長,與人一起成長的感覺真好。好像影子,伴你而生。也許到了一定程度,二者互為影子。生命和作品之間,彼此襯托,都不是紅花,也不是綠葉;都是紅花,也都是綠葉。
兩部長篇小說的情節,我就不復述了。想說的話,都融進小說中了。人物也好,情節也好,都有一種樸素、深沉甚至優雅的姿態,也有相關的內心理解。故事也好,人物也好,都是有深厚的意蘊。
這兩部小說,若是能憩息幾顆流浪的心靈,加持三兩個破碎的旅人,那是我最欣慰的。
黃山
兩部長篇小說的背景,都在黃山。《無常》的故事,體現了黃山的俠、禪、真、美。《彼岸》則有著專屬性,是串起來的黃山記憶。我為什么一直鐘情黃山?那是我一直視黃山為神,也如巨大無碩的蓮花,開放在天宇之上。我第一次去黃山,才五六歲,從溫泉那上山,才蹣跚幾步,就走不動了,父親無奈,只好將我背在身上,一直背至玉屏樓。我在父親背上看著黃山,黃山真美啊!我嗅著黃山松針的清香味,聽著身邊山谷溪流的嘩嘩聲,感覺就像行走在云霧繚繞的天堂里。
我一直以為,我身心、靈魂背后的點亮和通透,跟早期去黃山的經歷有關。黃山的霞光,貫通了我身體中的黑暗隧道,打開了我對美好事物孜孜追求的愿望。黃山于我,是一種昭示,是生命不可多得的垂憐。
我后來去黃山并不多。每一次去,都很激動,也小心翼翼。我寫黃山,其實是還債。我一腔情愿地認為,黃山跟我應該有某種私密的暗合和默契。天知地知,山知我知。天地人間,存有如此因果,感覺真是美妙。
小鎮
一個人的特質,跟他的童年成長經歷有關。我的身上,應該說有江南小鎮的氣息吧?細膩、聰穎、天真、調皮、反叛、桀驁……特質是先天的,改變和夯實靠的是后天的努力。
就生活而言,我認為人最適宜的生長地,就是江南小鎮了吧?江南的小鎮,與天地自然,與人情世故,都異常的接近,如魚游在水中,充滿情趣,暢達溫暖。人在這樣的地方長大,最具人的靈性。如此稟性,最適合文學。每一個小鎮孩子,都有很好的文學感覺。
江南的小鎮,讓人盡享生活。生于江南的小鎮,就是上蒼賜予你豐富的生活,讓你充分體味人世的喜怒哀樂。我了解到的世相,了解人間的歡樂、煩惱以及種種瑣屑,還有豐富而美妙的人生經驗,絕大部分都是對于江南的小鎮人與事的觀察而得到的。
江南的小鎮還是多彩的。季節多彩,生活多彩,人心也多彩。墨分五色,色彩也不是單一的概念化——西瓜的紅,與蜜桃的紅,與西紅柿的紅,都是不一樣的紅。外部的事物,映照于心,溫度不同,色彩便不同。色彩其實是人心的反饋,人心溫潤,色彩自然溫潤;人心黯淡,色彩自然黯淡。希望也好,未來也好,其實是幽深的井,渴望陽光的赤橙紅綠青藍紫。
色彩是緣起緣落;萬物都是緣起緣落。
少女
少女露著藕一般白嫩的胳膊,在河邊浣衣,是夏日一景。世上最美好的東西,就是含苞欲放的少女吧?少女是花的蓓蕾,是正在綻放的夢幻。少女不同于女人,是美而不是性;她是超越性別的,融合了男人、孩童和女人的美。
少女如新竹。竹子在筍脫去衣殼的時候,是最美好的吧?清翠、碧綠、清亮,迎風搖曳。很難找到適合的詞匯去形容她們。少女之美,干凈明亮,有著神性,讓人自慚形穢。
我少年的時候,人世黯淡,可卻有風景之美,少女之美。我是從少女的身上看到了超出現實的美好。美于我,是一種觀照,讓我覺醒,疏導了我身上的凡俗之氣,讓我意識到有天然的氣息可采集。我后來知道,很多能量,必須有一種明確的念想,才能采擷得到。
少女天生具有美感與慧心,如早春茶樹的芽尖。這種美感和慧心,除了天意垂憐,還需覺醒的自知,承接天命,悉心凝聚,才能醞釀培育醇明馥郁的芳香。
少女如蓓蕾般綻放,可花朵不能自知,也難以自救,終究是美夢一場。大觀園中,一度春色滿園,有那么多冰清玉潔之人。可是紅塵襲來,霜凍過后,都是殘枝敗葉的悲涼。花朵絢麗,終于枯萎,如此故事,周而復始,可是寫起來,還是讓人筆頭鉛重。
少女,依存美好和純凈,其他一切,皆可忽略。
般若
人其實有先驗成分,只是很難印證罷了。這種生而知之,不是智慧,而是般若。般若跟智慧是有區別的。般若帶有先天性,智慧是后天開發的;般若是連接虛空,智慧側重于入世;般若清亮且善良,智慧功利而陰鷙。
般若忽有忽無。人,最大的幸運,就是帶有般若性,若隱若現,若淺若深。在生命的過程中,擁有般若,是一種造化。
般若經常躲藏于文字中。有般若的文字,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會意。你不知道,卻會懂得。
文字的般若性,一直是我追求的。般若性往往表現為平和,口語化、哲思化。沒有口語化,沒有平和的氣息,沒有哲思化,很難有般若性。
般若,背后仍是空寂。作品有般若性,是以有限連接無限;沒有般若性,文字只是文字,背后沒有虛空,也沒有藍天白云清風明月。
記憶
記憶一定是曾經的真實嗎?我想不是。時光流逝,過去、現在、未來經常混淆,經驗和體驗難以為證。提筆寫字的人是有福的,可以將記憶和未來摻雜在一起,讓有限成為無限,讓一切成為可能。紙上的故事,在這個世界上可能發生過,也可能沒發生過。一個人寫作,其實是以冥想發現了它,將它牽引進這個世界,以文字賦予它生命。
寫作不是蓋房子,蓋房子的比喻太機械。我喜歡的比喻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寫作就是捕捉時間之風。靈魂之所以成為靈魂,是因為自由地迂回于彼岸和此岸之間,像無形的渡船,將彼此的秘密,捎來捎去。我喜歡這樣的感覺,一直想在空靈和現實之間,做一個擺渡人。
記憶就是河流中的波光瀲滟。用記憶打造的夢幻,是超越時空的,可以稱之為月亮河。
擺渡于此岸與彼岸的過程,是創造,也是自觀。它解決了內心的諸多困惑和疑問,平息了波瀾和沖突。一個時常在時空之中飄來浮去的人,自己是自己的上帝。
小說中的人物,因緣而起,由筆墨賦予生命。每一次紙頁的翻動,都讓他們活過來,演繹既定的故事,進行重新講述。生命不僅僅是活著,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存在,以文字存在的方式,與現實存在的方式,存在著錯位。以文字存在的世界,終究為心靈直接吸收,會活在一個不老的時空里。
讀小說吧,一切,都在里面了。凡文字,都很難隱藏自己,呈現的,都是真諦。風來竹面,雁過留聲。凡風起時,故事便如花一般開放,也如植物一樣瘋長;凡風落起,該迷頓的迷頓,該凋零的凋零。隨緣的文字,隙縫中會有清香拂面,如黃山風起的松針之香,也如夏日荷塘的蓮花之香。味道即記憶,也是不朽。
小說如果能將作者導入永恒的空寂,也是一種造化吧?如是我聞,這世界的一切,都是從空寂來來往往的一個個故事,如螢火蟲,一直或隱或現,也一直飄來飄去。
責任編輯? ? 張凱
特邀編輯? ? 張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