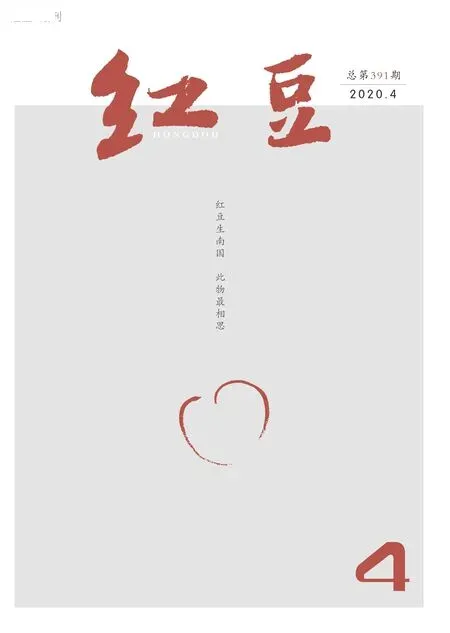深度諦視個(gè)人與歷史記憶的生命般若
盡管早就對(duì)趙焰兄有所耳聞,但認(rèn)真地接觸他的小說(shuō)文字,《彼岸》的確是第一次。閱讀趙焰的文字,首先一個(gè)突出的感覺(jué)便是一種詩(shī)意盎然的逼人才氣。且不要說(shuō)他的小說(shuō)本身,單只是他的一些創(chuàng)作談,這一方面就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讀小說(shuō)吧,一切,都在里面了。凡文字,都很難隱藏自己,呈現(xiàn)的,都是真諦。風(fēng)來(lái)竹面,雁過(guò)留聲。凡風(fēng)起時(shí),故事便如花般開(kāi)放,也如植物一樣瘋長(zhǎng);凡風(fēng)落起,該迷頓的迷頓,該凋零的凋零。隨緣的文字,隙縫中會(huì)有清香拂面,如黃山風(fēng)起時(shí)的松針之香,也如夏日荷塘的蓮花之香。味道即記憶,也是不朽。”如此這般清新自然但卻充溢著詩(shī)意的文字,一般的作家斷然難以寫出。創(chuàng)作談已經(jīng)如此,其小說(shuō)本身文字的迷人,當(dāng)可想而知。“有一種情感輕輕撩撥我,像羽毛輕拂,又似音樂(lè)纏繞。這種感覺(jué),似乎是從很多年前那一天開(kāi)始的:它如霧靄般自然升騰,輕舞飛揚(yáng),由輕微變得強(qiáng)烈,由陌生變得熟悉,然后始終纏繞縈回。”這樣一種簡(jiǎn)直就是純凈如水一般的文字感覺(jué),在一般的小說(shuō)閱讀過(guò)程中著實(shí)難見(jiàn),所以,我真的想就這么一直抄下去。因?yàn)椋喿x和抄寫本身,就是一種難得的愉悅感受。然而,無(wú)論這語(yǔ)言有多么詩(shī)意和美妙,作為一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的《彼岸》,卻終歸不能僅僅停留在語(yǔ)言的層面上。在必然要充分及物的語(yǔ)言之外,作家還必須以必要的形式建構(gòu)承載更為深刻的思想內(nèi)涵,勾勒塑造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
毫無(wú)疑問(wèn),《彼岸》是一部與作家的個(gè)人記憶緊密相關(guān)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我們注意到,在這部采用了第一人稱敘述方式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中,作家曾經(jīng)專門談到過(guò)法國(guó)作家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的寫作緣起。那是在第九章的第三節(jié)開(kāi)頭部分:“氣味就是記憶。原先我讀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小瑪?shù)锰m蛋糕一節(jié),明白了味道和回憶的關(guān)系,明白味道對(duì)記憶的誘導(dǎo)。‘小瑪?shù)锰m是一種充當(dāng)茶點(diǎn)的小蛋糕,看上去是用扇貝殼那樣的點(diǎn)心模子做成的,四周還有規(guī)整的一絲不茍的皺褶。一個(gè)冬天的下午,普魯斯特掰了一小塊蛋糕放進(jìn)茶杯里泡軟并且食用,奇跡產(chǎn)生了——‘帶著點(diǎn)心渣的那一小勺茶碰到我的上顎,頓時(shí)讓我渾身一顫,我注意到我身上發(fā)生了非同小可的變化,然后,記憶之門打開(kāi),當(dāng)年的情景如黑色的河流一樣呈現(xiàn)在眼前。普魯斯特所要做的,就是溯源而上,一直到達(dá)河流的發(fā)源地。”趙焰之所以要專門引述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的寫作緣起,是為了說(shuō)明味道與記憶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為了引出一直沉寂在“他”(也即“我”)記憶中的那些稍有年月的紙質(zhì)書(shū)的味道,并由此而展開(kāi)一段圖書(shū)館竊書(shū)歷史的追憶。但其實(shí),如果從這部聚焦于個(gè)人與歷史記憶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的整體來(lái)說(shuō),其真正的緣起,應(yīng)該是“楔子”部分“我”與年邁的“革命母親”洪春花的重逢,這個(gè)時(shí)候,已經(jīng)是上個(gè)世紀(jì)的九十年代。看到佝僂著身子走路的洪春花,“我”腦海里情不自禁浮現(xiàn)出的便是幼年時(shí)的好友小玉:“我遲疑了一會(huì),問(wèn):小玉外婆,您認(rèn)識(shí)我嗎?我注意到,當(dāng)我發(fā)小玉這個(gè)音節(jié)時(shí),她的全身如電擊似的一陣戰(zhàn)栗。我知道那是殘留在她身上的刺,我觸碰到它了,刺深入地扎了她一下,那種尖利讓她一凜,于麻木中再次感到痛楚。”與洪春花的重逢,不僅激活了本來(lái)就一直深印在“我”腦海中的關(guān)于小玉的記憶,而且“我”還從洪春花這里意外地獲得了小玉在當(dāng)年留下的一厚沓手稿:“我打開(kāi)一看,是一沓手稿,很明顯,是小玉寫的。我的心一凜,開(kāi)始小心翼翼地翻動(dòng)它們,稿紙已泛黃,筆跡也已發(fā)黑模糊,內(nèi)容是我熟悉的黃山游擊隊(duì)的故事。從寫作手法上來(lái)說(shuō),像是小說(shuō),也像是一篇有關(guān)皖南游擊斗爭(zhēng)以及歷史和地方故事的筆記。”“文字的最上方,寫著兩個(gè)遒勁而清秀的大字:清明。這應(yīng)該是這篇東西的標(biāo)題,生硬而堅(jiān)決。以此詞匯而命名,應(yīng)該是對(duì)曾經(jīng)的歲月的祭奠。”從根本上說(shuō),正是與小玉外婆洪春花很多年之后的重逢,以及從洪春花手中意外獲得的小玉事關(guān)黃山游擊隊(duì)的手稿,如同那塊“小瑪?shù)锰m蛋糕”一樣,徹底喚醒了沉睡在第一人稱敘述者“我”(也即“他”)腦海中的記憶,讓我們的思緒伴隨著敘述者回到了那些既往的“似水年華”之中:“這是一個(gè)簡(jiǎn)單的記憶,也是一個(gè)復(fù)雜的故事;是一段尋常的時(shí)光,卻是一個(gè)非常的事件;是曾經(jīng)的真相,也是永遠(yuǎn)的疑問(wèn);是曇花一現(xiàn)的情感,也是永恒的懷念……”就這樣,一段塵封已久的個(gè)人與歷史記憶,伴隨著對(duì)于幼年好友小玉的懷念而被敘述者“我”徐徐打開(kāi)了。
面對(duì)《彼岸》,我們首先應(yīng)該注意到的,就是敘述形式上的一種特別設(shè)定。具言之,也就是敘述者“我”和人物“他”的合一與分身。一方面,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小說(shuō)中的所有故事都是經(jīng)由“我”的敘述視角講述而出,即使是那些早已遠(yuǎn)逝歷史往事,也同樣是由“我”轉(zhuǎn)述給讀者的。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卻又可以發(fā)現(xiàn),這個(gè)敘述者“我”,一旦返身到一個(gè)人成長(zhǎng)關(guān)鍵時(shí)期的少年時(shí)代,一旦返身到看起來(lái)已是相對(duì)遙遠(yuǎn)的1970年代,馬上就變身為自始至終都處于無(wú)名狀態(tài)的“他”:“我會(huì)不由自主地被它吸引,跟隨記憶的召喚,置身于時(shí)光之下,就像一個(gè)觀眾,棲身于觀眾席,靜靜地回眸往昔的時(shí)光。仿佛電影膠片,再次在眼前播放。主角已不再是我,而是他,一個(gè)小男孩。我與他相互凝視,構(gòu)成了彼此的對(duì)應(yīng);我可以穿越記憶的河流看到他,能看到他的背影,卻看不到他面孔的真切;而他呢,也可以在想象中,在靈魂的深處意識(shí)到一個(gè)將來(lái)的我,如同意識(shí)到一點(diǎn)光亮,像目睹對(duì)岸的星星之火,或者感知未來(lái)冥冥的昭示。”“這是另一種真實(shí)。與現(xiàn)實(shí)的時(shí)空觀相同的真實(shí)。”這里,除了作家一種迥異于尋常的帶有明顯超越性的真實(shí)觀,另外一個(gè)不容回避的問(wèn)題就是,絕對(duì)擁有人物命名能力的趙焰,為什么拒絕給“我”/“他”這個(gè)人物命名呢?對(duì)此,我想從兩個(gè)方面給出相應(yīng)的解釋。其一,如果說(shuō)第一人稱“我”更多地顯示出一種主觀性色彩的話,那么,第三人稱“他”所具備的,就更多地是一種客觀性色彩。趙焰之所以一定要在小說(shuō)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完成這種人稱的轉(zhuǎn)換,正是為了能夠盡可能擺脫“為自己諱”的心理羈絆,以達(dá)到更接近于事物存在真相的客觀性敘事目標(biāo)。其二,趙焰之所以拒絕給“他”以具體的命名,肯定是要憑此而賦予人物一種更具普遍性的抽象性特質(zhì)。這一方面,魯迅先生筆下那個(gè)早已不朽的人物形象阿Q,就是一個(gè)非常恰當(dāng)?shù)陌咐H绻f(shuō),當(dāng)年同樣擁有命名能力的魯迅,為了達(dá)到普遍的國(guó)民精神性象征的藝術(shù)目標(biāo),可以借用一個(gè)帶有突出抽象性的字母“Q”來(lái)為人物命名,那么,很多年之后的趙焰,也一樣可以將一個(gè)具體的人物形象徑直命名為“他”。究其根本,趙焰之所以要采用如此一種帶有突出抽象性特質(zhì)的敘述人稱處理方式,正是為了使“他”具有更普遍的代表性,將“他們”這一代人的生存經(jīng)驗(yàn)與心理體驗(yàn)更多地凝結(jié)體現(xiàn)在“他”這一具像化的人物形象身上。與此同時(shí),我們無(wú)論如何都不能輕易忽略的另外一點(diǎn),乃是作家由此而獲得的那樣一種敘事自由度。歸根到底,作家趙焰在這部被命名為“彼岸”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中,之所以能夠如同高水平的自由體操運(yùn)動(dòng)員一樣,以一種閃轉(zhuǎn)騰挪的方式自如地出入于歷史與現(xiàn)實(shí)、過(guò)去與現(xiàn)在、時(shí)間與空間、此岸與彼岸、形而下的生活實(shí)體與形而上的哲學(xué)玄思之間,正與如此一種敘事自由度的獲得,存在著緊密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
然而,與敘事人稱的特別設(shè)定相比較,作為一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彼岸》藝術(shù)層面上更加值得注意的一點(diǎn),乃是一種復(fù)雜藝術(shù)結(jié)構(gòu)的成功營(yíng)造。約略計(jì)來(lái),整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由三條彼此交叉的結(jié)構(gòu)線索組合而成。其中,最主要的一條,當(dāng)然就是與第一人稱敘述者“我”亦即人物形象“他”的個(gè)人成長(zhǎng)緊密相關(guān)的發(fā)生在1970年代的那段故事。具體來(lái)說(shuō),“他”人生故事的開(kāi)始,是不經(jīng)意間目睹了一個(gè)女人不無(wú)艱難的生產(chǎn)過(guò)程。那是在“他”五歲時(shí)候一個(gè)春雷震蕩的上午,“他”“醒世了”:“醒世的含義,是混沌初開(kāi),有了記憶,也有了自我。”“人的醒世,如光照耀混沌天地,一切有了亮色,有了記憶。”那一次,“他”跟隨著母親在公社大院里。母親突然間不見(jiàn)了,傳入“他”耳中的,是一個(gè)女人聲嘶力竭的哀號(hào)。就這樣,一個(gè)女人的生產(chǎn)場(chǎng)面深深地刻印在了“他”的腦海里:“正對(duì)著他視線的地方,放著一張床,同樣污穢的床單上,躺著一個(gè)女人,下身赤裸著,肚皮挺得老高。叫聲就是那個(gè)女人發(fā)出的,她如生病的老貓一樣扭動(dòng)著身軀,不斷發(fā)出哀鳴,有血水不時(shí)從她兩腿之間流出,地上小山般堆滿了沾染了血水的草紙。他的內(nèi)心害怕又好奇,看得心驚肉跳,血往頭上直涌,雙腳不由自主地顫抖,松軟得差點(diǎn)跪下來(lái)。”如此一種不無(wú)丑陋慘烈的女性生產(chǎn)過(guò)程無(wú)意間的目睹,就這樣不期然地成為“他”“醒世”的起點(diǎn)。一個(gè)人的生命記憶,就此而開(kāi)始建立。但需要特別強(qiáng)調(diào)的一點(diǎn)卻是,正如同這個(gè)女人的生產(chǎn)過(guò)程一直伴隨著污穢的血水一樣,“他”“醒世”之后建立起來(lái)的個(gè)人生命記憶,以及由此而進(jìn)一步延伸開(kāi)去的廣義層面上的歷史記憶,都伴隨著堪稱慘烈的“血水”。某種程度上,趙焰這部《彼岸》所呈現(xiàn)在廣大讀者面前的,就正是這樣一種充滿著慘烈“血水”的個(gè)人生命記憶與歷史記憶。
具體來(lái)說(shuō),與“我”的個(gè)人生命記憶緊密相關(guān)的這一條結(jié)構(gòu)線索中,作家主要講述的,乃是“他”生命成長(zhǎng)過(guò)程中非常重要的兩大部分。首先一部分,是“他”、小玉以及小芙他們?nèi)恢g,那樣一種真可謂“剪不斷理還亂”的純真少年情誼。或許與母親打小就把“他”當(dāng)作女孩子來(lái)?yè)狃B(yǎng)有關(guān),那時(shí)候的“他”,總是一副有著一頭彎曲柔美頭發(fā)的,生性柔弱的女性化模樣。唯其因?yàn)槿绱耍栽谌粘I钪校八辈趴偸且氡M一切辦法,去努力證明自身男性氣概的具備。“他”之所以會(huì)對(duì)同性的如同小玉這樣一個(gè)大男孩產(chǎn)生一見(jiàn)傾心式的向往與追求,恐怕正是如此一種自卑心理充分發(fā)揮作用的結(jié)果。具體來(lái)說(shuō),“他”和小玉之間的情誼,起始于腳穿一雙回力牌白球鞋的小玉,在操場(chǎng)邊向“他”借了一顆彈子去玩打彈子游戲。那一次,雖然只是借了一顆彈子,但到后來(lái),小玉還給“他”的,卻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滿滿一捧彈子。兩位男孩子之間的少年情誼,就此而徹底鑄定。對(duì)于“他”和小玉之間超乎尋常的這種同性情誼,作家曾經(jīng)以這樣的筆觸做出過(guò)富有詩(shī)意的生動(dòng)描述:“后來(lái)他想,一切都是緣分,之所以遇上小玉,不是他擁有超出一般男孩的能力和品質(zhì),而是時(shí)間、地點(diǎn),說(shuō)不上的氣息,在起著作用。當(dāng)然,彼此的氣質(zhì)、音容、笑貌、舉止,也起到了粘合作用。他們?nèi)绱似鹾希舜丝释駜闪K橐粯蛹鼻械鼐鄢梢惑w。所有的理性判斷,以及試圖貼上的詞語(yǔ),都顯得太輕飄太蒼白。寫出與分辨出來(lái)的,跟本來(lái)從來(lái)就是兩碼事。”然而,心地單純的“他”,根本就不可能料想到,自己與小玉之間的情誼,竟然會(huì)因?yàn)榕⑿≤降某霈F(xiàn)而遭到強(qiáng)有力的挑戰(zhàn)。女孩小芙與小玉的結(jié)識(shí),其實(shí)緣于小玉一種勇敢的“英雄救美”行為。那一次,當(dāng)身穿花裙子的小芙和她的弟弟大頭,一起在街上意外遭到一伙調(diào)皮的壞孩子用彈弓和紙彈欺辱的時(shí)候,毅然地挺身而出對(duì)他們姐弟倆伸出援手的,就是這位擁有滿腔俠骨柔腸的小玉:“小芙說(shuō),她看見(jiàn)自行車上的小玉,就像看見(jiàn)英俊的騎士騎在馬上一樣。她聽(tīng)見(jiàn)小玉沖著那些壞孩子大吼一聲,那些壞孩子嚇傻了,一個(gè)個(gè)作鳥(niǎo)獸狀散去。然后,她就看見(jiàn)了小玉看了她一眼,眼中充滿著憐愛(ài),又遞過(guò)來(lái)一條干干凈凈的手帕,讓他們擦去眼淚。”問(wèn)題在于,好端端的,那些壞孩子為什么一定要對(duì)小芙姐弟倆“大打出手”呢?行文至此,敘述者“旁逸斜出”地結(jié)合那個(gè)特定的畸形野蠻時(shí)代給出了相應(yīng)的思考:“后來(lái)他想:那些打彈弓的壞小子應(yīng)該是一種妒忌吧?對(duì)于美,人們都會(huì)有一種妒忌的。那幫人顯然是想以他們帶有惡意的行動(dòng),來(lái)表示一種友愛(ài);是示好的方式,只是以扭曲的方式表達(dá)罷了。而這個(gè)時(shí)代,本來(lái)就是扭曲著對(duì)待萬(wàn)事萬(wàn)物的。確實(shí),在這個(gè)世界上發(fā)生的一切,都能佐證這樣的觀點(diǎn)。只要是得不到的,或者不懂的,就會(huì)憎恨它,甚至毀壞它。那些尚沒(méi)有成人的壞小子,只是將那個(gè)時(shí)代的邪惡釋放出罷了。”也因此,隱藏在這些壞小子欺辱行為背后的,即是人性本身的邪惡,更是時(shí)代與社會(huì)的邪惡。能夠“旁逸斜出”地把這一點(diǎn)揭示出來(lái),所充分證明的,正是作家趙焰一種突出思想能力的具備。
就這樣,什么事情都沒(méi)有發(fā)生,僅僅只是因?yàn)樾≤讲唤?jīng)意間的出現(xiàn),便頓然使得“他”、小玉以及小芙三人之間的關(guān)系,陷入到了某種空前緊張的狀態(tài)之中:“我不屑與她為友,而她也不屑向我表示好感。我們兩個(gè)中的任何一個(gè)人,都可以和小玉關(guān)系融洽,無(wú)縫無(wú)隙。可是每當(dāng)三個(gè)人在一起時(shí),總別別扭扭,就像軸承之中夾入一粒沙子。我和小芙相視為陌路人,不僅無(wú)話,目光也從不相對(duì),總是有意無(wú)意地忽略,即使偷偷相瞥,也總是乜斜著眼睛,帶著明顯的不屑。”盡管在意識(shí)到問(wèn)題存在之后,置身于其中的小玉,也曾經(jīng)做過(guò)很多次的調(diào)和努力,但卻終歸沒(méi)有能夠取得理想的效果。說(shuō)到“他”、小玉以及小芙這兩男一女三人關(guān)系的設(shè)定,趙焰的一個(gè)別出心裁之處,就是超越了一般作家總是難免會(huì)陷入到其中的三角戀藝術(shù)窠臼,把小玉設(shè)定為中心人物,讓“他”和小芙圍繞小玉感情的擁有而“爭(zhēng)風(fēng)吃醋”,而發(fā)生了尖銳激烈的矛盾沖突。在那個(gè)書(shū)籍與知識(shí)特別匱乏的時(shí)代,為了能夠更好地鞏固與小玉之間的情誼,一旦得知曾經(jīng)下鄉(xiāng)做過(guò)兩年知青、很是有一點(diǎn)思想的小玉熱衷于閱讀的情況,“他”便不管不顧地利用子弟的身份,開(kāi)始了在群藝館圖書(shū)室里的“竊書(shū)”行為:“源源不斷地,他為小玉拿來(lái)很多種讓他欣喜的書(shū)。《第三帝國(guó)的滅亡》《屠格涅夫散文選》……讓他開(kāi)心的是,每一次帶書(shū)過(guò)去,都讓他撇下小芙,把她冷落在一邊。在他看來(lái),書(shū)籍就是智慧,或者說(shuō),文字就是智慧,書(shū)還有著摒除妖孽的作用,書(shū)就是夾在小玉和小芙之間的屏風(fēng),會(huì)拉著他的視線不再看她。至于小芙,雖然她很漂亮,但她就是妖,就是《聊齋志異》中的女鬼,不能讓小玉更多地接近她。他天真的想法,以及樂(lè)此不疲的成就感,讓他滿懷激情地頻繁出入書(shū)庫(kù),以致離危險(xiǎn)越來(lái)越近。”正如同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動(dòng)翅膀,就很可能在美國(guó)的德克薩斯引起一場(chǎng)龍卷風(fēng)一樣,“他”根本不可能想到,正是自己“竊書(shū)”行為被圖書(shū)管理員俞美芹的發(fā)現(xiàn),最終釀成了小芙母親李玉茹的人生悲劇。李玉茹的人生悲劇這里暫且置而不論,需要注意的一點(diǎn),是作家通過(guò)“我”的“竊書(shū)”事件揭示的1970年代初期知識(shí)與文明的極度匱乏問(wèn)題:“每當(dāng)公開(kāi)或半公開(kāi)談及這一段趣事時(shí),他總是說(shuō),那時(shí)他空虛得要命,無(wú)書(shū)可讀,于是便賒著膽子去偷‘毒草。正是因?yàn)槟且欢螏в忻半U(xiǎn)性質(zhì)的行動(dòng),他讀了很多書(shū),知道了人間與世界的紛紜與復(fù)雜,也知道了世界的神秘。書(shū)真是好東西,書(shū)就是智慧,是人類文明的象征……”一方面,千方百計(jì)地討好小玉,固然是“他”不管不顧地“竊書(shū)”的主要?jiǎng)訖C(jī),但在另一方面,借此機(jī)會(huì)從書(shū)籍中獲得了充分的精神滋養(yǎng),卻也可以被看作是意料之外的一種收獲。
書(shū)籍的作用固然重要,但“他”根本沒(méi)有料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煞費(fèi)苦心從圖書(shū)室“竊”得的書(shū)籍,竟然會(huì)在一架老式的照相機(jī),在小芙面前落了個(gè)一敗涂地的結(jié)局:“琴聲如訴,只是開(kāi)頭。將他們進(jìn)一步連接的,是那架120海鷗相機(jī)。就是掛在脖子上,可以低頭從框子里看到影像的那種相機(jī)。一開(kāi)始,他以為小玉迷上了攝影,后來(lái)才知道,其實(shí)小玉不是對(duì)攝影感興趣,而是以相機(jī)為媒,可以更多地接觸小芙,還有,就是相機(jī)提供了觀察小芙的更多可能性。”面對(duì)著相機(jī),一直對(duì)小玉“情有獨(dú)鐘”的“他”,終于萬(wàn)般無(wú)奈地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在不知不覺(jué)間被“排除”出局:“小玉、小芙、120海鷗相機(jī),三個(gè)聯(lián)手,把他劃在局外。”“在相機(jī)面前,書(shū)本無(wú)疑是失敗者,書(shū)與文字,本來(lái)就是極度無(wú)聊的產(chǎn)物,它難得有生趣,只是以枯燥的思想見(jiàn)長(zhǎng),離生活很遠(yuǎn)。這是一個(gè)尷尬或者痛苦的過(guò)程,很多人并不習(xí)慣于這樣的過(guò)程。有著靈魂的書(shū),在某種意義上,真是敵不過(guò)美麗的倩影。”究其根本,擁有靈魂的書(shū)籍,最終不敵相機(jī),更因?yàn)槟莻€(gè)時(shí)代的相機(jī)與暗房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唯其如此,也才有了趙焰這樣一段關(guān)于暗房的精彩文字:“相比于小小的相機(jī),暗房更像是空間的進(jìn)一步深入和拓展,這空間既是物理性質(zhì)的,也是情感性質(zhì)的,更是人性本身的要求。于人的本性,男女之間的相處,更愿意在一種黑暗和窄小的狀態(tài)。在黑暗中,他們會(huì)更大膽,更放得開(kāi),更容易完成質(zhì)的變化——所有的背景都會(huì)退去,包括場(chǎng)景和聲音,只有他們,在黑暗的擠壓下,變得越來(lái)越近,無(wú)論是身體還是心靈。這場(chǎng)景不可多得,可以說(shuō)天造地合。”在“如此富有詩(shī)意的黑暗中,什么不會(huì)發(fā)生呢?影像在黑暗中開(kāi)成花朵。他們本身,也成為黑暗中的花朵”。就這樣,既然小玉和小芙已然借助于相機(jī)的媒介而成為“黑暗中的花朵”,那么,“他”被迫無(wú)奈遠(yuǎn)離小玉時(shí)刻的到來(lái),自然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shí)。那一次,在他們?nèi)齻€(gè)人又一次聚在一起的時(shí)候,“他”終于感覺(jué)到了自己存在的多余:“終于,小玉站起身來(lái)了,無(wú)可奈何地?fù)u搖頭,走到門邊,拉開(kāi)門,用目光冷冷地看著他,這明顯是示意他離開(kāi)了。”面對(duì)著小玉冷冰冰的目光,“他坐在那里,如坐針氈,感到失望極了,傷心極了。起先,他仍然堅(jiān)持坐在那里,一動(dòng)不動(dòng)。”但到后來(lái),隨著時(shí)間一點(diǎn)一滴地悄然逝去,“他”終于還是堅(jiān)持不住了:“他低著頭,閉著眼走出了房間。他一點(diǎn)也不想看小玉,更不想看小芙,這個(gè)房間的一切,他都不想再看了。剛走出,就覺(jué)得木門在后面掩上了,又聽(tīng)見(jiàn)了插銷的聲音。”緊接著出現(xiàn)的,也就是不甘心的“他”在門縫里的偷窺行為:“肉體與肉體如此之白,白得仿佛發(fā)出灰色的光,像兩只放大的蠶一樣糾纏在一起。”作為一位對(duì)小玉“情有獨(dú)鐘”的男性青年,被迫無(wú)奈地退出小玉的情感領(lǐng)地,其內(nèi)心的失落與憂傷,自然可想而知。在遭受了如此一種突如其來(lái)的情感打擊之后,“終于,那個(gè)小男孩哇的一聲哭了,像夏日午后悶熱天氣導(dǎo)致的暴風(fēng)雨,以及暴風(fēng)雨之前的閃電。這哭聲并不是傷心或仇恨,而是窺視了人類自身的弱點(diǎn),開(kāi)發(fā)了相應(yīng)的驚異和恐懼。”一段美好的“幻象與情感,就這樣永遠(yuǎn)埋葬起來(lái),埋葬在上個(gè)世紀(jì)的七十年代初。”這里的一個(gè)關(guān)鍵問(wèn)題是,我們到底應(yīng)該怎么樣給“他”和小玉之間的這種情感定位。一方面,因?yàn)榘l(fā)生在同性之間,所以首先就排除了愛(ài)情的可能。另一方面,雖然發(fā)生在同性之間,但從趙焰的具體描寫來(lái)看,兩位男性之間卻也絲毫都沒(méi)有同性戀的傾向。由此可見(jiàn),“他”和小玉所發(fā)生的,其實(shí)只能是一種與“他”柔弱的自卑心理緊密相關(guān)的,同性少年之間的純真情誼而已。甚至,包括小芙在內(nèi),他們?nèi)恢g情誼都是非常純真的,只不過(guò)因其純真,這種情誼卻也顯得特別脆弱。對(duì)此,敘述者有著真切的洞察:“小玉、小芙以及他,無(wú)論他們生活的背景,他們的出身,他們的性別,其實(shí)都是一類人,有著相同的質(zhì)地,相同的欲望,以及相同的玻璃心。他們只是尷尬地撞上了那個(gè)時(shí)代,陰差陽(yáng)錯(cuò)中,釀成了他們的茫然無(wú)措,以及悲慘結(jié)局。”此處所謂悲慘結(jié)局,毫無(wú)疑問(wèn)就是指小玉到最后竟然令人難以置信地因殺人犯的罪名而被處以極刑。因其與另外一條結(jié)構(gòu)線索緊密相關(guān),這里暫且按下不表。但不管怎么說(shuō),伴隨著“他”和小玉的情誼因小芙介入而發(fā)生的斷裂,一種少年之間美好的情感就此而被徹底埋葬。在這個(gè)意義上,趙焰的這部《彼岸》就可以被看作是一曲建立在個(gè)人生命記憶基礎(chǔ)上的青春挽歌。
其次一部分,是深深地刻印在“我”/“他”個(gè)人生命記憶中的歷史印痕。這里,一個(gè)無(wú)可置疑的前提就是,任何一部關(guān)于1949年后中國(guó)當(dāng)代歷史的書(shū)寫,只要不與這一時(shí)間段內(nèi)那些重要的歷史事件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其意義和價(jià)值都是可疑的。這一點(diǎn),集中凝結(jié)體現(xiàn)在“他”父親的社會(huì)政治身份與不幸命運(yùn)上。在“他”的記憶中,病體懨懨的父親不僅總是躺在床上,而且父母還總是出于沖突的狀態(tài)之中:“不過(guò)接下來(lái)的場(chǎng)景,經(jīng)常不可控——病體懨懨的父親,哪里爭(zhēng)得過(guò)伶牙俐齒的母親呢,氣喘吁吁地先動(dòng)了手,母親大怒,沖上前去,將床連同父親一起掀翻。父親匍匐在地上,一邊喘氣一邊咳嗽,像一片在風(fēng)雨中飄搖的紙人……”那么,父親和母親為什么總是處于沖突的矛盾狀態(tài)呢?借助于“他”少年時(shí)的調(diào)皮行為,敘述者對(duì)此做出了巧妙的揭示。那時(shí)候,因?yàn)椤八闭炫菰诔侵袠蛳旅娴暮铀校粌H總是會(huì)遭到母親的呵斥,而且還會(huì)用竹鞭狠狠地打他:“有時(shí)候母親打得乏了,看他不哭,自己倒哭起來(lái),邊哭邊數(shù)落:/‘我真是遭報(bào)應(yīng)啊!一個(gè)右派還不夠,又生了這樣一個(gè)孽種!父親在一旁聽(tīng)著,只能嘆著氣,眼光中有一種凄楚的眼神。”謎底到這里徹底被揭開(kāi),原來(lái)“他”的父親,竟然是那個(gè)年代里為人所不齒的右派知識(shí)分子。然而,因年幼尚且懵懂無(wú)知的“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右派,不知道如此一種社會(huì)政治身份將會(huì)給父親,也給自己帶來(lái)多大的恥辱。這樣,也才有了如此令人心痛的一個(gè)場(chǎng)景:“有一天中午,母親發(fā)著大火,把他從城中橋下面拽回家,沖著床上的父親大發(fā)一通火后去學(xué)校了。父親想安慰他,可是沒(méi)說(shuō)半句,就強(qiáng)烈地咳嗽著,咳得死去活來(lái)。他濕漉漉地站在那里,看著床上的父親,覺(jué)得恐懼和傷感。這個(gè)面色蒼白的男人,就是創(chuàng)造他生命的人嗎?要是沒(méi)有他,自己便不存在。可是——要是自己不存在的話,還會(huì)有這個(gè)世界嗎?”“他”在這里所展開(kāi)的,首先是一種存在意義層面上的不自覺(jué)哲學(xué)思考。盡管從血緣倫理的角度來(lái)說(shuō),沒(méi)有父親,就絕對(duì)不會(huì)有自己的存在,但關(guān)鍵的問(wèn)題更在于,從主體與客體的角度來(lái)說(shuō),“我”的存在又是至為關(guān)鍵的。很大程度上,作為客體的世界的存在,必須依賴于作為主體的“我”的存在。倘若缺失了“我”這一主體,那么,世界這一客體的存在,就是無(wú)法想象的。那么,到底是父親重要呢,還是身為主體的自我重要呢?對(duì)此,盡管“他”不可能給出相應(yīng)的答案,但“他”的如此一種思考本身,卻是有意義的。尤其是,當(dāng)如此一種命題,與身為右派知識(shí)分子的父親聯(lián)系在一起的時(shí)候,在那個(gè)血統(tǒng)論彌漫一時(shí)的特別年代,其意義和價(jià)值就更是非同尋常了。
然而,年幼無(wú)知的“他”根本就不可能料想到,到后來(lái),竟然是自己一種懵懂的莽撞行為,把絕望的父親徹底送上了人生的不歸路。那一次,“學(xué)校里鴉雀無(wú)聲,應(yīng)該是放學(xué)了。他悄悄地向教室望去,只見(jiàn)母親赤身裸體地躺在破舊的地板上,身上壓著一個(gè)同樣赤身裸體的人。他們糾纏得異常緊密,不時(shí)發(fā)出怪異的叫喊。他看得膽戰(zhàn)心驚,心跳莫名其妙加速,熱血在快速流動(dòng)。那一個(gè)男人,是城郊大隊(duì)的會(huì)計(jì)。他害怕極了,本能地選擇跑開(kāi),咚咚的腳步聲一定驚醒了他們。他從那個(gè)小洞鉆出,一口氣跑回家,氣喘吁吁地對(duì)父親說(shuō):‘不好了,不好了,媽媽跟那個(gè)會(huì)計(jì)打起來(lái)了!父親有些驚愕。他慌慌張張地說(shuō):‘他們把衣服脫得光光的……滾在一起打架呢!”明明是兩個(gè)成年男女在一起偷情,但在懵懵懂懂的“他”看來(lái),卻變成了兩個(gè)人在打架。在把自己無(wú)意間偷窺到的情形轉(zhuǎn)述給一直病態(tài)懨懨地躺在床上的父親之后,“父親拭去眼淚。自言自語(yǔ)地說(shuō):‘我是該走了。真是該走了,該走了……”就這樣,從肉體到精神本來(lái)早已經(jīng)遍體鱗傷的右派知識(shí)分子父親,在不期然地遭受了母親偷情行為的打擊之后,徹底喪失了生存的意志,以自殺的方式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面對(duì)著父親的遺體,母親放聲號(hào)啕大哭,“他嚇壞了,也放聲大哭。可是他的心里,一點(diǎn)也感覺(jué)不到悲傷,只是覺(jué)得落寞和害怕。”偏偏就是在此時(shí)此刻,一場(chǎng)大雨攜帶著雷電不期而至:“這一場(chǎng)風(fēng)雨讓母親驚慌失措,也使他對(duì)于死亡有了某種象征性的領(lǐng)悟。”其實(shí),早在“他”意外偷窺母親出軌行為的那天晚上,“他”就一直沒(méi)有睡著:“他又開(kāi)始胡思亂想,包括上次在醫(yī)院所見(jiàn)到的慘烈的一幕,包括和平的死,母親與會(huì)計(jì)赤裸地絞在一起……這些都像電影膠片似的一幕一幕在腦海里放映。那個(gè)時(shí)候,他尚不知道自己的思考已觸及了世界上的根本。世界的本質(zhì),就是他想的生、老、病、死,再加上性和時(shí)間。這些,一直讓人們思考,卻一直無(wú)法被破譯。”我們注意到,在敘述過(guò)程中,作家曾經(jīng)特別強(qiáng)調(diào),父親的死,對(duì)于“他”的影響巨大。實(shí)際上,并不只是父親的死,徑直說(shuō)來(lái),即使是父親的存在本身,也對(duì)“他”產(chǎn)生著足夠巨大的影響。“他”性格之所以會(huì)如同女性一樣過(guò)度敏感、柔弱、自卑,一方面固然是天性使然,但在另一方面,聯(lián)系右派知識(shí)分子父親被打入政治另冊(cè)的現(xiàn)實(shí)處境,就不難發(fā)現(xiàn),如此一位身份特殊的父親,其實(shí)也發(fā)生著不容忽視的負(fù)面影響。雖然只是寥寥數(shù)筆,但父親那樣一個(gè)備受屈辱的右派知識(shí)分子形象,卻已經(jīng)給讀者留下了難忘的印象。盡管作家并沒(méi)有詳細(xì)鋪敘父親為什么被打成右派,以及在被打成右派后遭受了怎樣的身心折磨,但會(huì)心的讀者卻自可以憑借想象填充這些耐人尋味的書(shū)寫空白。作家趙焰的值得肯定處在于,僅只是通過(guò)“他”的母親與會(huì)計(jì)偷情這一個(gè)細(xì)節(jié),在寫出父親飽經(jīng)折磨的內(nèi)心世界的同時(shí),也寫出了這樣一位父親在那個(gè)特定年代必然會(huì)帶給“他”的精神屈辱。
與“我”/“他”緊密相關(guān)的1970年代的故事這一條結(jié)構(gòu)線索之外,《彼岸》的另一條結(jié)構(gòu)線索,就伸向了遙遠(yuǎn)的過(guò)去,講述著抗戰(zhàn)時(shí)期曾經(jīng)活躍一時(shí)的黃山游擊隊(duì)的故事。關(guān)于這一條結(jié)構(gòu)線索,我們首先需要注意敘述者曾經(jīng)專門引述過(guò)的小學(xué)作文《祭掃陶小武烈士墓》的片斷文字:“陶小武同志被敵人抓住了,敵人給他戴上了數(shù)十公斤重的手銬腳鐐。在審問(wèn)時(shí),偽縣長(zhǎng)惡狠狠地問(wèn)他:‘你的領(lǐng)導(dǎo)人是誰(shuí)?陶小武響亮地回答道:‘不知道!偽縣長(zhǎng)又問(wèn):‘你的同伙有哪些?都在哪里活動(dòng)?陶小武烈士斬釘截鐵地說(shuō):‘不知道!敵人氣急敗壞,兇殘地把陶小武綁在老虎凳上,把他打得皮開(kāi)肉綻,甚至用竹簽狠狠地釘入陶小武同志的十指。十指連心呀,陶小武同志一連暈厥過(guò)去幾次。昏過(guò)去敵人就用冷水將他澆醒。偽縣長(zhǎng)兇殘地瞪著金魚(yú)眼說(shuō):‘招不招?不招,讓你求生不能求死也不得!陶小武烈士忍住疼痛,傲然一笑,說(shuō):‘你們休想從我嘴里得到什么,為了人民的解放,我這一百斤,豁出去了!”請(qǐng)?jiān)徫以谶@里摘引了如此長(zhǎng)的一段文字,因?yàn)椴蝗绱司碗y以見(jiàn)出究竟何為主流的正統(tǒng)史觀。實(shí)際上,明眼人早就可以看出,這一段小學(xué)作文是那個(gè)時(shí)代的產(chǎn)物,“在很大程度上,這樣的文字,是我們一代人的記憶。二十世紀(j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早年的時(shí)候,都寫過(guò)這樣的作文吧?這樣的語(yǔ)言和文字,就是我們成長(zhǎng)時(shí)穿過(guò)的的確良軍裝、手持的紅纓槍,以及口袋里的紅寶書(shū)。當(dāng)然,這些都是外在的。就內(nèi)在而言,那些東西,也成為了我們血液中的血清蛋白。”將以上兩段文字結(jié)合在一起,我們就不難發(fā)現(xiàn),作家趙焰意欲強(qiáng)調(diào)表現(xiàn)的,正是在那個(gè)特定的社會(huì)政治時(shí)代對(duì)一代人所進(jìn)行的思想意識(shí)形態(tài)規(guī)訓(xùn)。如此規(guī)訓(xùn)的一種直接結(jié)果,就是所謂正統(tǒng)史觀的生成。那一段戲仿性文字所承載體現(xiàn)的,正是這種正統(tǒng)史觀。作家趙焰的難能可貴處,在于特別敏銳地意識(shí)到了文字與思想之間的內(nèi)在緊密關(guān)聯(lián)。“人們都是這樣,先由對(duì)于文字的盲從,擴(kuò)散到對(duì)很多東西的盲從。可又由于對(duì)文字的熱愛(ài),開(kāi)始了撥亂反正。文字讓我們清醒,讓我們覺(jué)悟,讓我們得以真實(shí)地認(rèn)識(shí)這個(gè)世界,與世界建立一種比較和諧的關(guān)系,能夠開(kāi)發(fā)出某種深入屬性,較深刻地明白這個(gè)世界的一些道理。文字可以撥云見(jiàn)日,能清晰地觸摸到這個(gè)世界的真諦所在。”趙焰在這里所敏銳揭示的,其實(shí)正是文字的“遮蔽”與“去蔽”這雙重功能。一方面,正如同所謂的指鹿為馬一樣,文字的確具有“遮蔽”性的洗腦與欺騙功能。當(dāng)謊言被刻意重復(fù)一千遍的時(shí)候,也就往往會(huì)變成所謂的“真理”。趙焰所謂“對(duì)文字的盲從”進(jìn)一步引發(fā)出的“對(duì)很多東西的盲從”,所強(qiáng)調(diào)的正是這一點(diǎn)。當(dāng)然,這種文字,只能是明顯區(qū)別于前一種具有意識(shí)形態(tài)功能文字的另一種“去蔽”式文字。趙焰所謂“文字讓我們清醒,讓我們覺(jué)悟,讓我們得以真實(shí)地認(rèn)識(shí)這個(gè)世界”,所謂的“文字可以撥云見(jiàn)日,能清晰地觸摸到這個(gè)世界的真諦所在”。如果說(shuō)接受過(guò)那個(gè)時(shí)代意識(shí)形態(tài)規(guī)訓(xùn)的小學(xué)作文,是一種“遮蔽”性文字,那么,趙焰《彼岸》中的主體性部分,便是一種能夠讓我們“清醒”“覺(jué)悟”,能夠洞穿生存表象迷霧直抵世界“真諦”的“去蔽”性文字。質(zhì)言之,趙焰之所以要?jiǎng)?chuàng)作《彼岸》這樣一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正是為了能夠充分使用這種“去蔽”性文字,把個(gè)人記憶中的生命與歷史真相,盡可能予以切實(shí)的還原與再現(xiàn)。
具體到抗戰(zhàn)時(shí)期的黃山游擊隊(duì)這一條結(jié)構(gòu)線索,作家趙焰意欲實(shí)現(xiàn)的,正是把那一段曾經(jīng)被意識(shí)形態(tài)嚴(yán)重遮蔽的說(shuō)法,盡可能地抵達(dá)并還原一種歷史真相。比如,關(guān)于周老五參加革命的動(dòng)機(jī),根本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革命理想,而只是緣于個(gè)人的尷尬生存處境。一個(gè)是他嫌棄財(cái)主父親給自己找下的媳婦太丑,再一個(gè)是這么一個(gè)丑媳婦,竟然還跟自己的財(cái)主父親不干不凈的。究其根本,正是出于如此一種強(qiáng)烈的弒父沖動(dòng),周老五才不管不顧地追隨著黃源參加了革命。大約也正因?yàn)橛兄媲械淖陨眢w驗(yàn),所以,在后來(lái)的談?wù)撨^(guò)程中,周老五才會(huì)將水泊梁山做各種比附:“周老五說(shuō):你讀過(guò)《水滸》吧?這一本書(shū),不僅是最好的小說(shuō),也是中國(guó)數(shù)千年社會(huì)的寫照。”“他繼續(xù)說(shuō):中國(guó)五千年的歷史,就是改朝換代的歷史,每一朝每一代,都是一次水泊梁山,都是一次一百零八將的復(fù)活。”“他又說(shuō):不僅是每朝每代,每一個(gè)單位,每一個(gè)團(tuán)體,都是一個(gè)水泊梁山。”他還作了進(jìn)一步的發(fā)揮:“你看啊,咱們的黃山游擊隊(duì),黃源就是宋江,王麻子呢,是李逵魯智深,我呢,搞情報(bào)的,搞交通的,算是‘神行太保戴宗,然后,他說(shuō)出一大堆名字,一個(gè)個(gè)對(duì)應(yīng)著梁山泊的人物。”更關(guān)鍵的一點(diǎn),是他對(duì)宋江的深度評(píng)價(jià):“宋江跟晁蓋是有區(qū)別的,晁蓋是老實(shí)人,仁義、義氣,一諾千金;宋江雖然仁義和義氣,不過(guò)也很狡猾,他可不是婦人之仁,他能把梁山那一幫土匪強(qiáng)盜收拾得服服帖帖。光靠忠義,沒(méi)有智慧是不行的。”在周老五看來(lái),這一方面的一個(gè)突出例證,就是宋江執(zhí)意把扈三娘嫁給了特別窩囊的矮腳虎王英。正因?yàn)樽约簝?nèi)心里特別喜歡扈三娘,所以,宋江才做出了如此一種決斷。盡管周老五沒(méi)有做進(jìn)一步的明確分析,但言已至此,其內(nèi)中隱含的意味實(shí)際上早已呼之欲出。事實(shí)上,周老五之所以要翻來(lái)覆去地把黃山游擊隊(duì)比附為水泊梁山,正是普通游擊隊(duì)員的真實(shí)理解和反映,在他們身上,雖有強(qiáng)烈的革命愿望,卻很難上升到理性和自覺(jué)的革命意識(shí)的。
說(shuō)到《彼岸》對(duì)歷史真相的還原,還有兩個(gè)方面必須予以提及。一個(gè)是陶小武烈士的犧牲真相。作家巧妙地借助于張老頭之口,進(jìn)行了真切的敘述。原來(lái),陶小武并不是共產(chǎn)黨員,真正的共產(chǎn)黨員是他的哥哥陶大文:“國(guó)民黨抓他的時(shí)候,泄露了風(fēng)聲,陶大文就跑了。陶小武沒(méi)跑掉,也沒(méi)想跑,他哪里知道哥哥是共產(chǎn)黨啊!那些國(guó)民黨反動(dòng)派看交不了差,就把陶大文犯的事,全賴在陶小武身上了!陶小武還是個(gè)孩子啊,一開(kāi)始不承認(rèn),他們就給他上刑,坐老虎凳什么的。陶小武為了保護(hù)哥哥,也為了不遭受更多的折磨,干脆就簽字畫(huà)押承認(rèn)了。”張老頭的這一番言辭,對(duì)尚且年幼的敘述者“我”來(lái)說(shuō),簡(jiǎn)直就是一種當(dāng)頭棒喝。再一個(gè),是當(dāng)年王麻子和周老五他們當(dāng)年刺殺國(guó)民黨國(guó)防部少將高參孫鐸這一歷史事件的真相,那一次刺殺事件的具體執(zhí)行人,除了王麻子和周老五之外,還遺落了一個(gè)重要的人物,這就是那位后來(lái)下落不明了的“地下黨”陶大文。多年來(lái)一直以訛傳訛的歷史事實(shí)真相是,這位名叫陶大文的“地下黨”,不僅全程介入了刺殺事件,而且還親手殺死了罪大惡極的孫鐸。
實(shí)際上,陶大文這一人物形象在《彼岸》中的重要性,還不僅僅體現(xiàn)在是他,最終刺殺了頑敵孫鐸,而是因?yàn)檫@一人物形象,與小說(shuō)中的第三條,也即以小芙的母親李玉茹為核心人物的這一條結(jié)構(gòu)線索,存在著格外緊密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李玉茹,原本是上海一個(gè)教會(huì)大學(xué)圣約翰大學(xué)的學(xué)生。或許與教會(huì)大學(xué)有關(guān),臨到畢業(yè)的時(shí)候,學(xué)生全部被要求離開(kāi)上海去工作。李玉茹就這樣來(lái)到了S縣工作。先是當(dāng)鄉(xiāng)村中學(xué)教師,后來(lái)調(diào)入群藝館:“在接連拒絕了幾個(gè)‘老游擊隊(duì)員的求婚后,李玉茹曾因‘思想意識(shí)問(wèn)題被縣里主要領(lǐng)導(dǎo)點(diǎn)名,在群藝館的內(nèi)部會(huì)議中遭到幾次批評(píng)。1957年,李玉茹理所當(dāng)然地被打成右派,發(fā)配到長(zhǎng)江北岸的勞改農(nóng)場(chǎng)。”到了勞改農(nóng)場(chǎng)后,李玉茹結(jié)識(shí)了另一位詩(shī)人右派杜子明。因?yàn)椤氨环胖鸬哪信畟儯瑯O容易在夕陽(yáng)西下的蘆葦叢中讓內(nèi)心變得柔軟,又極容易在寒冷的冬日渴望著別人的溫度”,所以,他們兩位很快就相好并結(jié)合了。但此后卻又因?yàn)槎抛用魈貏e花心的緣故,不斷地分分合合。到了“文革”后期,在與李玉茹的交談過(guò)程中,“他”的母親才了解到,李玉茹當(dāng)年之所以狠下決心,選擇到S縣來(lái)工作,其實(shí)與陶大文這一人物緊密相關(guān)。原來(lái),李玉茹在解放前夕曾經(jīng)在上海交了一個(gè)各方面都才華橫溢的年齡比自己大了好多歲的男朋友。雖然這位既名季炳余又名陶大文的男友在解放后神秘失蹤,但他卻給李玉茹留下了極深的印象。這樣,等到李玉茹畢業(yè)選擇的時(shí)候,她自然而然也就近乎本能地選擇了陶大文的故鄉(xiāng)S縣。
但李玉茹根本就不可能料想到,到最后,自己竟然會(huì)因?yàn)檫@樣的一種人生選擇而付出生命的代價(jià)。這個(gè)時(shí)候,時(shí)間已經(jīng)到了1975年的3月:“春天到來(lái)之后,安謐的群藝館大院,突然呈現(xiàn)出緊張的氣氛。有一天清晨,突然來(lái)了一批白衣藍(lán)褲的公安,直沖入李玉茹的家里,撞壞了大門,把里面的門閂都撞斷了。公安當(dāng)即將正在熟睡的李玉茹銬上了手銬,帶去了公安局。”至于李玉茹被逮捕的具體罪名,公安部門給出的說(shuō)法是:“李玉茹受叛徒陶大文命令,秘密潛伏于S縣,多年來(lái)一直向國(guó)民黨方面提供情報(bào)。”那么,告密出賣李玉茹的到底是誰(shuí)呢?經(jīng)過(guò)一番追問(wèn)后,“他”才搞清楚,原來(lái),自己也脫不了干系。首先是“他”的母親,無(wú)意間把李玉茹和陶大文的交往故事講給了群藝館圖書(shū)室的管理員俞美芹。然后是“他”因?yàn)樵趫D書(shū)室“竊書(shū)”被俞美芹發(fā)現(xiàn),結(jié)果俞美芹遭到了“他”母親一番伶牙俐齒的搶白。滿肚子不高興的俞美芹,到最后一怒而舉報(bào),這樣也才不僅釀成了李玉茹的一場(chǎng)牢獄之災(zāi),而且也還最終把她逼上了絕路。李玉茹被逼上絕路且不說(shuō),關(guān)鍵是她的一上吊,就使得小芙和大頭姐弟倆一下子便失去了生活的來(lái)源。也因此,李玉茹自殺引起的一個(gè)連鎖反應(yīng),就是小芙男友小玉為了女友的鋌而走險(xiǎn)。如此一位革命者的后代,那么一位特別熱衷于各種閱讀的思考者,到最后,竟然在黃山頂上不惜半路搶劫,最終在打斗中不慎身亡。我們注意到,在寫到小玉意外身亡的時(shí)候,小說(shuō)中曾經(jīng)有過(guò)這樣一段充滿命運(yùn)感的沉痛文字:“一切都是陰差陽(yáng)錯(cuò)。最終睡進(jìn)這一副棺材的,不是‘革命母親洪春花,而是他的孫子,作為一個(gè)搶劫犯的小玉。如果從一開(kāi)始就將這一切聯(lián)系起來(lái)的話,那么,這似乎是命中注定,更帶有宿命的意義。它就像是命運(yùn)的有意安排,是命運(yùn)的詛咒,也是命運(yùn)別出心裁的回饋,帶有某種神秘的旨意。”認(rèn)真地想一想,何止是小玉和洪春花?小說(shuō)中先后出現(xiàn)的“我”/“他”、小芙、大頭、父親、李玉茹、黃源、周老五等一眾人物形象,到最后無(wú)不都落在了命運(yùn)的落網(wǎng)之中,無(wú)不令人嘆息。更進(jìn)一步說(shuō),掩藏于這種命運(yùn)感背后的,其實(shí)是作家趙焰難能可貴的一種悲憫情懷。
我們注意到,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談中,趙焰曾經(jīng)專門談到過(guò)佛家的專用語(yǔ)“般若”:“般若,經(jīng)常躲藏于文字中。有般若的文字,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會(huì)意。你不知道,卻會(huì)懂得。”“文字的般若性,一直是我追求的。般若性,往往表現(xiàn)為平和,口語(yǔ)化、哲思化。沒(méi)有口語(yǔ)化,沒(méi)有平和的氣息,沒(méi)有哲思化,很難有般若性。”“般若,背后仍是空寂。作品有般若性,是以有限連接無(wú)限;沒(méi)有般若性,文字只是文字,背后沒(méi)有虛空,也沒(méi)有藍(lán)天白云清風(fēng)明月。”那么,到底何為“般若”呢?查閱百度漢語(yǔ),得出的說(shuō)法是:“智慧。佛教用語(yǔ)。通過(guò)直覺(jué)的洞察所獲得的先驗(yàn)的智慧或最高的知識(shí)。”雖然沒(méi)有從趙焰那里得到過(guò)應(yīng)證,但我想,他很大程度上應(yīng)該是在這種意義上使用“般若”這一語(yǔ)詞的。就此而言,“般若”一詞,其實(shí)帶有不容忽視的哲學(xué)上的先驗(yàn)性,也帶有某種生命超度的意味。從這個(gè)意義層面上來(lái)說(shuō),趙焰這部由三條結(jié)構(gòu)線索組構(gòu)而成的頗具復(fù)雜性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作家一種深度諦視個(gè)人與歷史記憶中的生命苦難的“般若”性文字。
王春林,山西文水人。中國(guó)小說(shuō)學(xué)會(huì)副會(huì)長(zhǎng),山西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第八屆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評(píng)委,第五屆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評(píng)委。系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中國(guó)小說(shuō)排行榜評(píng)委、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會(huì)理事、山西省作家協(xié)會(huì)全委會(huì)委員。主要從事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曾在《文藝研究》《文學(xué)評(píng)論》《當(dāng)代作家評(píng)論》《小說(shuō)評(píng)論》《南方文壇》《文藝爭(zhēng)鳴》等刊物發(fā)表學(xué)術(shù)論文200多萬(wàn)字。出版有個(gè)人批評(píng)文集《話語(yǔ)、歷史與意識(shí)形態(tài)》《思想在人生邊上》《新世紀(jì)長(zhǎng)篇小說(shuō)研究》等。先后榮獲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第9屆優(yōu)秀成果獎(jiǎng)(2004年度)、山西新世紀(jì)文學(xué)獎(jiǎng)(2002年度)、趙樹(shù)理文學(xué)獎(jiǎng)(2004-2006年度)、山西省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優(yōu)秀成果獎(jiǎng)等獎(jiǎng)項(xiàng)。
責(zé)任編輯? ?丘曉蘭 韋毓泉
特邀編輯? ?張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