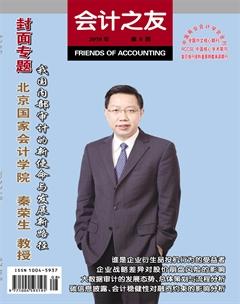R&D外包、自主研發與綠色技術創新
黃文炎 向麗


【摘 要】 中國工業企業在加大自主研發力度的同時,有效發揮R&D外包優勢,加快推進綠色技術創新,對于工業行業綠色轉型升級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中國27個工業行業的面板數據,運用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實證分析了自主研發對工業企業兩種類型的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以及R&D外包對自主研發與不同類型的綠色技術創新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研究結果表明,自主研發與工業企業綠色產品創新之間存在顯著的U型關系,但自主研發與工業企業綠色工藝創新之間具有顯著的倒U型關系;R&D外包正向調節自主研發與不同類型的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在R&D外包的不同區間內,自主研發對工業企業綠色產品創新和綠色工藝創新的邊際量不同。
【關鍵詞】 自主研發; R&D外包; 綠色產品創新; 綠色工藝創新
【中圖分類號】 F27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9)08-0050-06
近年來,隨著中國研發投入的持續增長,自主研發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問題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作為企業技術創新的首要途徑,自主研發會顯著地正向影響企業技術創新,并有助于增加企業創新績效[1]。但自主研發具有研發周期較長、成本較高、風險較大等劣勢,因而企業僅僅通過自主研發來實現所有創新技術的獲取是非經濟的[2]。在環境規制背景下,綠色技術創新日漸成為企業增強自身競爭優勢的路徑選擇。部分學者的研究驗證了自主研發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企業通過R&D外包能夠獲得更先進的技術知識以及更多的技術機會,有助于實現競爭資源的互補。但現有文獻中仍缺少對R&D外包在自主研發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關系的影響研究。中國工業企業在加大自主研發力度的同時,如何有效發揮R&D外包優勢,推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從而實現綠色轉型升級仍有待探究。本文嘗試運用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實證研究自主研發對工業企業兩種類型的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應,并考察R&D外包在自主研發與不同類型綠色技術創新的關系中的調節作用。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自主研發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
綠色技術創新可劃分為綠色產品創新和綠色工藝創新兩種類型。其中,企業在產品生命周期的各階段均按照環保要求進行綠色化產品的設計、開發和生產等活動屬于綠色產品創新;企業通過改造工藝技術、更新工藝設備、廢物回收利用等方式以降低污染物的產生量和排放量,從而減少工業活動對環境的危害的活動屬于綠色工藝創新。原毅軍等[3]的研究結果表明,自主研發通過促進企業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進而正向影響我國制造業技術升級。宋維佳等[4]通過研究得出,研發資金投入對我國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在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水平超過一定門檻值以后,研發資金投入會更顯著地正向影響綠色技術創新。尤濟紅等[5]通過研究發現,R&D投入有利于促進中國工業的綠色技術進步,但這種促進作用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并認為自主R&D投入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萬倫來等[6]的研究也表明,自主R&D投入能夠對工業企業綠色技術效率產生積極影響,但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業綠色技術進步水平,且低R&D投入行業企業受到的抑制作用更明顯。王惠等[7]的研究結果顯示,高技術產業R&D投入強度與綠色創新效率之間存在顯著的非線性關系。當企業規模較小時,研發資金匱乏使得企業持續性創新難以開展,且綠色創新研發人才流失加速,從而導致綠色創新效率偏低。但當企業具備一定規模后,R&D投入強度對企業綠色創新效率產生顯著的正向作用,這是因為“知識外溢”效應使得企業研發人員更容易獲得交流機會,其通過學習綠色創新理念能夠更快積累研發經驗,進而推動企業綠色產品研發和綠色工藝創新。據此提出假設1、假設2。
H1:自主研發與綠色產品創新之間具有非線性關系。
H2:自主研發與綠色工藝創新之間具有非線性關系。
(二)R&D外包的調節作用
R&D外包是指發包方通過契約方式提供資金給外部專業研究機構等,以此獲得新產品、新工藝或新思路等技術成果的創新過程[8]。學者們一致認為R&D外包能夠對企業技術創新產生正向影響。企業將部分研發工作進行外包,有利于降低研發成本,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使其能夠在擅長的領域培育獨特的技術優勢,并在提升新產品研發速度的同時,有效降低研發風險,進而增加創新績效。在R&D外包過程中,企業應不斷地改進自身狀況來盡快適應外部異質性知識和技術,并持續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以充當一個有效的外部選擇。Katila[9]的研究指出,企業通過對內外部知識資源進行整合、消化和吸收,并轉化為自身的知識體系,有助于其內部研發能力的提升,進而促使企業加快開發新技術和新工藝。也有學者指出R&D外包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隨著內外部研發力度的不斷加大,企業因為R&D外包而增加的企業固定交易成本可能會下降[10]。陳啟斐等[11]的研究表明,R&D外包促進了中國制造業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和創新效率的提升,但R&D外包的自主創新效應受到企業人力資本存量的影響。在開放式創新背景下,企業應處理好自主研發與外部研發的關系。對于關鍵技術,企業應保持自主研發;而對于一些外圍技術,企業應進行適度的R&D外包以實現技術轉換和技術追趕。據此提出假設3、假設4。
H3:R&D外包正向調節自主研發與綠色產品創新的關系。
H4:R&D外包正向調節自主研發與綠色工藝創新的關系。
二、計量模型、變量與數據說明
(一)計量模型構建
基于前文的理論分析,并借鑒學界研究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的通常做法,本文分別構建了自主研發對企業綠色產品創新和綠色工藝創新影響的計量模型。為減少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本文對除ird和rdo外的變量均取自然對數。構建基本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i、t分別代表行業和年份;α0、α1、α2表示待估參數;βi為系數向量,μi為不可觀測的行業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被解釋變量中,Ln gpti,t表示行業綠色產品創新水平,Ln gpri,t表示行業綠色工藝創新水平。解釋變量中,irdi,t表示行業自主研發強度,ird2i,t表示自主研發的平方項。Xi,t為控制變量。具體表達為:
其中,α3、α4、α5表示待估參數;調節變量rdoi,t代表各工業行業的R&D外包強度,rdoi,t×irdi,t、rdoi,t×ird2i,t分別表示R&D外包與自主研發、R&D外包與自主研發的平方的乘積項,體現了R&D外包在自主研發與企業綠色產品創新和綠色工藝創新關系中的作用。
(二)變量的測度
1.被解釋變量:綠色產品創新、綠色工藝創新。現有研究對綠色產品創新的測算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采用新產品單位能耗,即能源消耗量與新產品產量的比值來衡量;二是采用新產品銷售收入與能源消耗量的比值來測度。綠色工藝創新的測算方法可分為三類:一是采用綠色工藝專利數、有毒氣體排放量等單一指標來測度;二是采用R&D經費內部支出與技術改造經費投入之和作為綠色工藝創新的衡量指標;三是通過構建多指標綜合評價體系對綠色工藝創新績效進行測算。本文基于數據的可得性,綠色產品創新(gpt)采用能源消費量與新產品產值的比值進行測算[12];綠色工藝創新(gpr)采用R&D經費內部支出與技術改造經費投入的總和來衡量[13]。
2.解釋變量:自主研發。學界有關自主研發的測算方法包括三種:一是將企業內部R&D支出作為衡量指標,通過永續盤存法對各行業的R&D存量進行估算,再采用研發指數做價格平減;二是使用人均內部研發支出進行測度;三是采用R&D經費內部支出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來測度。本文采用R&D經費內部支出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來測度各工業行業的自主研發強度(ird)[14]。為考察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關系,將自主研發的平方項(ird2)作為解釋變量引入回歸模型。
3.調節變量:R&D外包。學界對R&D外包的測算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借鑒外包強度測量指標,使用R&D外包廣度與R&D外包深度的乘積作為R&D外包強度的替代指標[15];二是采用測算服務外包的FH指數法,以及Daveri et al.提出的DJ指數來測度R&D外包率[16]。但FH指數法測度行業中間品進口容易出現偏差,也不能對行業進行區分,且存在“相同比例假定”的缺陷。相較FH指數法,DJ指數法對于分行業研發外包強度的測算更為精準。借鑒陳啟斐等[11]的做法,本文運用DJ指數法測度各工業行業的R&D外包強度。具體計算方法如下:
rdoi,t=mji,t /yi,t=(mj,t×bi,j)/yi,t? (8)
其中,i、t表示行業和年份,rdo為R&D外包強度,mji,t為第j種中間投入品進口,yi,t表示中間投入品總量,mj,t、bi,j分別表示第j種中間投入品的總進口量和完全消耗系數。
4.控制變量。企業規模(sca)選取大中型工業企業總產值與企業數量的比值作為衡量指標;所有制結構(str)使用國有企業在各行業工業總產值中所占比例進行測算;企業績效(epr)采用大中型工業企業利潤總額與總資產的比值計算得到[17];技術復雜度(tc)沿用馬晶梅[18]的做法進行測算;行業競爭強度(icn)通過計算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總產值、企業數量、資產總值、銷售收入4項指標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相同指標之間的比值的算術平均值得出[19];環境規制(eri)沿用王杰等[20]的做法計算得到各工業行業的環境規制強度;外商直接投資(fdi)以外商和港澳臺商企業的工業總產值占比來衡量;融資環境(fie)以金融機構貸款占科技活動經費的比重表示。
(三)數據說明
本文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兩位數工業行業分類,將2002年和2007年《中國投入產出表》中相應部門的投入產出表數據進行合并,并設定27個代表性行業為研究樣本。由于我國新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從2003年開始實施,且現有的工業細分行業總產值數據截至2011年,因此本文的樣本區間為2003—2011年。研究所需的相關數據由《中國投入產出表》(2002、2007年)、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庫(UNCTAD),以及《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4—2012年)直接得出或根據公式計算求得。并通過對部分變量的原始數據作價格平減,以此消除物價變動因素的影響。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變量描述性統計及相關性分析
表1是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及相關性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值均低于0.7。從方差膨脹因子檢驗結果(限于篇幅未列出)來看,所有變量的VIF值均低于10,表明本文構建的模型均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回歸檢驗結果分析
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本文采用HT檢驗法驗證了面板數據的平穩性,并通過F檢驗、LSDV法檢驗和Hausman檢驗判定,應采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本文最終運用STATA/MP13.1軟件的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進行模型參數估計,檢驗結果見表2。
模型1反映了控制變量對綠色產品創新的回歸分析結果。企業規模、技術復雜度、行業競爭強度和外商直接投資4項指標均對綠色產品創新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所有制結構、環境規制和融資環境3項指標均顯著正向影響綠色產品創新。企業績效對綠色產品創新具有不顯著的正向影響。模型2引入了自主研發和自主研發的平方項,其結果表明自主研發顯著負向影響綠色產品創新(β=-1.170,p<0.01),單純地依靠自主研發難以促進綠色產品創新水平有效提升。自主研發的平方項的系數顯著為正(β=0.164,p<0.01),表明自主研發與綠色產品創新間具有顯著的U型關系。這驗證了假設1。
模型3引入調節變量后R&D外包的系數不再顯著(β=-4.929,p>0.1)。模型4加入了R&D外包與自主研發的交互項,以及R&D外包與自主研發平方項的交互項。由回歸結果可知,自主研發和自主研發的平方項均對綠色產品創新產生顯著影響,且呈U型關系。R&D外包與自主研發平方的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正(β=66.731,p<0.1),說明R&D外包與自主研發兩者之間相互影響作用,且自主研發影響作用于綠色產品創新時,需要企業具備一定的R&D外包水平。在R&D外包的不同區間內,自主研發對綠色產品創新的邊際量不同。這驗證了假設3。
模型5是控制變量對綠色工藝創新的回歸檢驗結果。企業規模、所有制結構、外商直接投資和融資環境4項指標顯著正向影響綠色工藝創新,技術復雜度對綠色工藝創新起到顯著的負向作用。但企業績效、環境規制、行業競爭程度對綠色工藝創新影響均不顯著。模型6引入了自主研發和自主研發的平方項兩個解釋變量,其結果顯示自主研發顯著正向影響綠色工藝創新(β=1.784,p<0.01),說明工業企業的綠色工藝創新水平將隨著其自主研發程度的提高而上升,加大自主研發力度是促進業綠色工藝創新的有效路徑。自主研發的平方項的系數值顯著為負,表明自主研發強度存在一個最優值,自主研發與綠色工藝創新之間有顯著的倒U型關系。這驗證了假設2。
模型7引入調節變量后R&D外包的系數不顯著(β=-51.561,p>0.1),說明R&D外包與綠色工藝創新之間的關系仍有待探究。模型8引入R&D外包與自主研發的交互項,以及R&D外包與自主研發平方項的交互項。可見,自主研發和自主研發的平方項均對綠色工藝創新產生顯著影響,且呈倒U型關系。R&D外包與自主研發平方的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負(β=-66.350,p<0.05),說明只有當工業企業具備一定的R&D外包水平時,自主研發才能影響作用于綠色工藝創新,且在R&D外包的不同區間內,自主研發對綠色工藝創新的邊際量存在差異。這驗證了假設4。
為確保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先將占比5%的自主研發強度最高和最低的樣本去掉,然后對各模型重新做了回歸檢驗,并在樣本區間內選取2003—2008年作為新的觀測期,再對各模型進行重新估計。回歸檢驗結果(限于篇幅未列出)表明,本文的基本結論仍然成立,研究結果的穩健性較好。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通過實證研究得出:(1)自主研發與工業企業綠色產品創新之間存在顯著的U型關系。隨著自主研發程度的提高,工業企業的綠色產品創新水平呈現“先降后升”的發展態勢。(2)自主研發與工業企業綠色工藝創新之間具有顯著的倒U型關系。隨著自主研發程度的提高,工業企業的綠色工藝創新水平也將得以提升,但自主研發存在一個最優值。(3)R&D外包對自主研發與兩種類型的綠色技術創新之間關系起到正向調節作用。R&D外包是自主研發影響工業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基本條件。R&D外包與自主研發兩者之間相互影響作用,且自主研發影響作用于企業綠色產品創新和綠色工藝創新時,均需要企業具備一定的R&D外包水平。在R&D外包的不同區間內,自主研發對企業綠色產品創新和綠色工藝創新的邊際量不同。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認為中國工業企業應充分發揮R&D外包的成本節約和技術創新效應,適度加大R&D外包力度,并進一步強化企業自主研發,進而有效提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績效和市場競爭力。地方政府應從創新項目開發、創新市場開拓、創新資金支持及創新機制構建等方面加快推進創新生態系統建設,引導更多的創新要素向工業企業聚集,為工業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提供強力支撐。應根據企業技術創新需求制定形式多樣的扶持政策和融資貸款優惠政策,引導規模較小的企業適度擴大規模,激勵已經具備一定規模的企業做大做強。此外,還應不斷完善稅收和R&D補貼政策,鼓勵工業企業將非核心的研發業務外包給第三方企業,并對綠色技術創新效果較好的企業予以獎勵或稅收減免,激發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促進企業綠色轉型升級。
本文的理論貢獻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本研究的結果表明自主研發與工業企業不同類型的綠色技術創新之間均具有顯著的非線性關系。自主研發與工業企業綠色產品創新之間存在顯著的U型關系,但自主研發與工業企業綠色工藝創新之間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可見,過低或過高的自主研發強度均不利于中國工業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回歸檢驗結果也表明規模較大、技術復雜度較高、行業競爭較激烈的工業企業的綠色產品創新水平并不高,但規模較大、企業績效較好的工業企業的綠色工藝創新水平相對較高。這有助于學界深化對自主研發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關系的認識,是對自主研發領域理論研究的補充。第二,本研究發現R&D外包正向調節自主研發與工業企業不同類型綠色技術創新的非線性關系。該發現深化了對R&D外包在自主研發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關系中的作用的認識,有利于相關領域后續研究更為深入地認識R&D外包在企業自主研發及其綠色技術創新過程中的重要性,并有助于中國工業企業進一步探索破解自主研發現實困境的實施方案。但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中僅將R&D外包作為調節變量,未來研究可以通過引入新的調節變量對自主研發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關系的其他因素進行更為全面的識別與分析。
【參考文獻】
[1] 楊詩煒,張光宇,鄧彥,等.基于密切值法的我國區域工業企業創新績效評價[J].會計之友,2018(8):60-66.
[2] 王文寅,劉硯馨.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效率評價研究[J].會計之友,2017(8):100-103.
[3] 原毅軍,孫大明.FDI技術溢出、自主研發與合作研發的比較——基于制造業技術升級的視角[J].科學學研究,2017(9):1334-1347.
[4] 宋維佳,杜泓鈺.自主研發、技術溢出與我國綠色技術創新[J].財經問題研究,2017(8):98-105.
[5] 尤濟紅,王鵬.環境規制能否促進R&D偏向于綠色技術研發?——基于中國工業部門的實證研究[J].經濟評論,2016(3):26-38.
[6] 萬倫來,朱琴.R&D投入對工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來自中國工業1999—2010年的經驗數據[J].經濟學動態,2013(9):20-26.
[7] 王惠,王樹喬,苗壯,等.研發投入對綠色創新效率的異質門檻效應——基于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經驗研究[J].科研管理,2016(2):63-71.
[8] CHIESA V,MANZINI R.Organizing for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s:a managerial perspective[J].R&D Management,1998,28(3):199-212.
[9] KATILA R.New product search overtime:past ideas in their prim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2,45(5):995-1010.
[10] GARCIA-VEGA M,HUERGO E.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R&D outsourcing:the role of trade[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1,15(1):93-107.
[11] 陳啟斐,王晶晶,岳中剛.研發外包是否會抑制我國制造業自主創新能力[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5(2):53-69.
[12] 李婉紅,畢克新,孫冰.環境規制強度對污染密集行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基于2003—2010年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J].研究與發展管理,2013(12):72-81.
[13] 畢克新,楊朝均,黃平.FDI對我國制造業綠色工藝創新的影響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1(9):172-180.
[14] 傅曉霞,吳利學.技術差距、創新環境與企業自主研發強度[J].世界經濟,2012(7):101-122.
[15] 伍蓓,陳勁,吳增源.企業R&D外包的模式、測度及其對創新績效的影響[J].科學學研究,2009(2):302-308.
[16] DAVERI F,JONA-LASINIO C.Off-shor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Ital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Cesifo Economic Studies,2008,54(3):414-450.
[17] 戴小勇,成力為.研發投入強度對企業績效影響的門檻效應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3(11):1708-1716.
[18] 馬晶梅.技術復雜度與我國外包企業技術優勢及技術溢出效應——基于增加值的實證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6(9):1397-1403.
[19] 肖文,林高榜.政府支持、研發管理與技術創新效率——基于中國工業行業的實證分析[J].管理世界,2014(4):71-80.
[20] 王杰,劉斌.環境規制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的經驗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14(3):4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