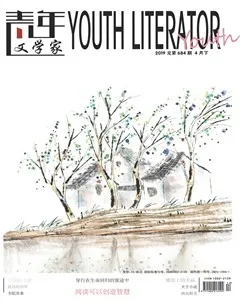《圣經》漢譯原則初探
摘? 要:自唐代以來,漢譯《圣經》一直是中國傳教士的一項重要工作。本文討論了三個階段的《圣經》漢譯,即唐代的景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和晚清的新教,揭示了漢譯《圣經》與中國翻譯理論的發展關系。
關鍵詞:漢譯;《圣經》;中國翻譯理論
作者簡介:秦瑞瑞,女,1995年6月出生,山西省呂梁市人,上海海事大學外國語學院2017級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生,研究方向:航運與經貿文獻的翻譯。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12--01
1、引言
基督教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人類發展史上一直有著極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和深遠影響。而《圣經》作為基督教的重要經典,其讀者之多,發行量之大,翻譯語種之多,都可謂為世界之最。英國翻譯理論家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更認為,《圣經》翻譯的歷史就是西方文化歷史的縮影。《圣經》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而中國的《圣經》翻譯作為世界《圣經》翻譯史上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為中國基督教話語體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2、唐代景教的漢譯《圣經》
景教士的翻譯,一方面,他們有《圣經》相關背景知識,在《圣經》漢譯過程中加入了一些他們自身的理解和體會,很多時候,中國的讀者都不能理解;另一方面,他們對中文目標語的理解和使用也不能達到翻譯需要的語言水平。結果導致:
(1)大量音譯詞的出現,如耶穌被翻譯為“移鼠”。(2)對佛教和道教的依附,譯文的文風十分接近于佛經翻譯。這種與翻譯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的特殊翻譯方法通常只限于早期的宗教典籍翻譯。
3、明末清初天主教的漢譯《圣經》
近代的中國,對外沒有開放政策,對內實行文化專制。在這種非常不利的條件下,中國《圣經》翻譯在景教之后又開始了另一次努力。16世紀末、17世紀初開始的天主教著作漢譯與早期的漢譯類似,也是由傳教士口授或者初譯,再由中國文人進行潤色與調整,譯文大致可以傳達出原文的意思,但無法觸及文本的精髓。
3.1 巴設譯本
約1700年,巴設將通俗拉丁文本《新約》的大部分譯為漢文。巴設的翻譯材料有限,然而,許多現代學者認為,其翻譯對后來的中國《圣經》翻譯有著深遠的影響。
3.2賀清泰譯本
賀清泰根據哲羅姆“通俗拉丁文本”翻譯的《圣經》,幾近全譯,1803年取名《古新圣經》,但未出版發行。他強調翻譯應注重忠實和流暢,卻沒有充分考慮歷史時代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制約和需要。
3.3利瑪竇譯本
這一時期最成功的耶穌會士無疑是利瑪竇。他充分認識到自己作為翻譯家的特定的歷史條件和地位,并對目標讀者有了明確的認識,進而確定了與特定時期相一致的翻譯原則,以服務于《圣經》漢譯。他和羅明堅一起出版了《天主圣教實錄》,《天主實義》等信仰著作。
4、晚清基督新教的《圣經》翻譯
自十九世紀以來,《圣經》漢譯又開啟了一頁新的篇章。基督教中文《圣經》翻譯史,通常從1807年馬禮遜來華起。這一時期主要譯本有馬士曼譯本、馬禮遜《神圣天書》、委辦譯本、施約瑟“二指版”、楊格非譯本、官話和合本等。
經過馬禮遜,麥都思和許多翻譯人員近半個世紀的努力,確立了《圣經》翻譯的基本原則,即:(1)翻譯語言必須是國語,不適用于地區方言;(2)翻譯語言必須簡單,使所有社會背景的人都可以明白;(3)詞語必須忠實于原文,并應具有漢語韻律和聲調;(4)隱喻應直接翻譯。
筆者認為,根據上述翻譯原則,這一時期的《圣經》翻譯已經打破了傳統的牢籠,在翻譯方法上,它從單純堅持文本的準確性轉變為同樣重視意義的準確性。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中國《圣經》翻譯實踐了尤金·奈達的“動態對等”翻譯原則。
5、結論
漢譯《圣經》是中國翻譯理論和實踐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所反映的許多問題也是中國翻譯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中國《圣經》翻譯的巨大理論成果不應因基督教教義與中國本土文化的巨大差異而被忽視甚至抹殺。隨著歷史時代的發展,中國的《圣經》漢譯研究也將永不止步。
參考文獻:
[1]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The Third Edition),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
[2]任東升.《圣經》漢譯文化研究[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