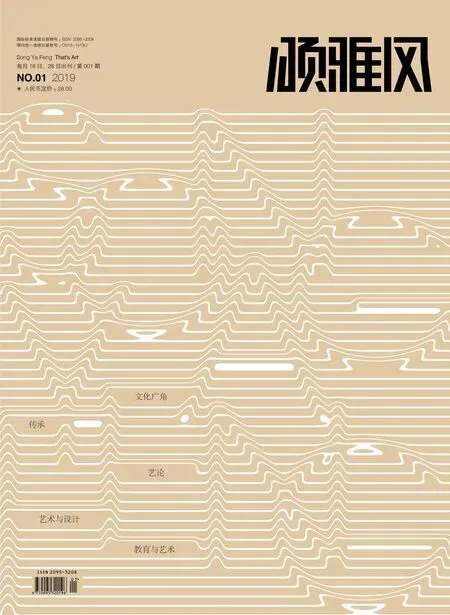怎一個“哭”字了得
——胡適《我的母親》文本探微
◎任偉
胡適的母親馮順弟于16 歲光緒十五年(1889)嫁給大她32 歲的胡鐵花,23歲時便成了寡婦,胡適時年3 歲。而馮順弟是胡鐵花的第三任妻子,胡適父親的前妻曹氏留下三兒三女,胡適大哥比胡母大七歲,胡適的二哥、三哥、三姐也只比胡母小兩三歲。處于華年的馮順弟便被迫做起了這個特殊家庭胡氏大家的主母,自然就成了這個復(fù)雜家庭矛盾沖突旋渦中生活的女子。這個沒有文化、沒有娘家支持,又失去丈夫這唯一靠山的農(nóng)村婦女,用古代女子獨特的視角、手段、方法——哭,教育兒子、維護(hù)家庭團(tuán)結(jié)、捍衛(wèi)清白,緩和解決矛盾,讀來令人心酸、心痛,更讓人稱贊、佩服。
一、“哭”教子中的嚴(yán)慈與悲苦
認(rèn)知“母親”的第一次“哭”——無聲之哭:
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xué)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出丑。)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
胡鐵花去世,留下孤兒寡母,并留下遺言:“令他讀書。”胡母在教子上身擔(dān)雙重角色,在中國傳統(tǒng)教育中通常是嚴(yán)父慈母。而胡母教育兒子很有方法,做到柔中有剛,剛?cè)嵯酀?jì),以慈為本,嚴(yán)字當(dāng)頭。
1.她總是在每天天剛亮叫醒兒子胡適,“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甚么事,說錯了甚么話,要我認(rèn)錯,要我用功讀書。”提醒胡適反思昨天的言行,知其錯在何處,避免犯同樣的錯誤;“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時才教訓(xùn)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guān)了房門,先責(zé)備我,然后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犯錯必定受到懲罰,懲罰的輕重以犯錯的大小來定,賞罰分明;
2.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xué)他,不要跌他的股。”既表達(dá)了“對亡夫的思念和敬愛”,又樹立父親在兒子眼中心中的高大形象和重要地位,還對兒子提出了目標(biāo)和鞭策,同時寫出了一位母親對兒子的慈愛和期盼;
3.“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沒有了丈夫,教子如此艱難,自然“傷心”,教育兒子矯正言行“令他成材”是一項艱巨而漫長的任務(wù),無疑悲苦常在,自然經(jīng)常流淚,所以“往往掉下淚來”;
4.再說,在這么一個大家庭中對兒子的教育是憂心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無疑增加了教育的難度和變數(shù),更令胡母憂心忡忡;
5.“掉下淚來”是無聲的哭,因為“她教訓(xùn)兒子不是藉此出氣叫別人聽的”,就是哭也不想讓別人聽到,有苦也不想讓別人知道,可見內(nèi)心之“苦”有多重;
6.“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作為母親教育兒子是以尊重為前提,決不以犧牲兒子的自尊為代價。
這樣的教育近期結(jié)果是“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xué)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養(yǎng)成了早期勤學(xué)的好習(xí)慣,而且“文縐縐的”“像先生的樣子”“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yán)厲眼光,便嚇住了”;長期的結(jié)果是對母親尊重、感激,做人謙虛、感恩,學(xué)有所成,擁有36個博士頭銜,成為北大教授、校長。
在教育兒子的無聲之哭中,有嚴(yán)慈、尊重,有方法、生存策略,有美好的追憶和期盼,有憂慮、傷心和悲苦,還有教子不斷達(dá)成既定目標(biāo)之欣慰與藝術(shù)。
二、“哭”維護(hù)家庭團(tuán)結(jié)中的忍讓與無助
認(rèn)知“母親”的第二次“哭”——輕聲之哭:
我母親只忍耐著,忍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這一天的天明時,她便不起,輕輕地哭一場。她不罵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她先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
在胡氏大家庭中,胡適的母親還有另一個尷尬的身份——丈夫前妻子女的后母,他們同胡適的母親年齡相仿,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難,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事實上,令胡母苦痛的還有一點——“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jīng)營調(diào)度”,作為年輕的“當(dāng)家后母”,在失去丈夫這一有力的后盾之后,她沒有德高望重的年齡優(yōu)勢,也沒有當(dāng)家人應(yīng)該掌控的財政大權(quán),也沒有娘家強(qiáng)有力的支持,更為要命的是“大哥從小便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很能干而氣量很窄小的人。她們常常鬧意見”,對此胡母總是默默地堅韌地忍受著——
首先是自己“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表現(xiàn)出“氣量大,性子好”;其次,讓胡適事事讓著大嫂的女兒,如果有爭執(zhí)也總是責(zé)備胡適,就連敗家的大哥,給家里帶來的“麻煩”,“母親”也是“從不罵他一句。并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胡母對處理家庭矛盾一是“忍”,二是“讓”,大有“大人不記小人過,宰相肚里能撐船”之風(fēng)范;第三,胡母對進(jìn)一步升級的“胡鬧”,“母親只裝作不聽見。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后門到后鄰度嫂家去閑談。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到了實在忍無可忍的時候,于是就在某一天的早上“輕輕地哭一場”,“剛哭時,聲音很低”,這是胡母對壓抑許久的委屈的一種釋放,接著“漸漸哭出聲來”,作為“當(dāng)家后母”,要化解家庭矛盾,既不能大聲哭——家丑不可外揚(yáng),進(jìn)而還會引來長舌婆搬弄是非,激化家庭矛盾,也要哭出聲來讓家人——大嫂、二嫂知道心中的委屈。
正如胡適說,這是一種法子。胡母的“哭”是對無理鬧事嫂子的一種回應(yīng),而且是一種示弱性的回應(yīng)。但這卻是一種智慧的回應(yīng),這也是一種以退為進(jìn)的無助無奈之法。胡母這一“哭”,讓鬧事者看到自己的“胡鬧”有了收獲、結(jié)果,獲得了勝利感,自然愿意順勢停止折騰。胡母還“哭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是呀,如果“丈夫”在,有丈夫當(dāng)家做主,兒媳們還敢這般鬧嗎?如此一“哭”,戲劇性的一幕出現(xiàn),那個鬧氣的嫂子“捧著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面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默默地?zé)o聲地承認(rèn)錯誤,向胡母道歉。至此,“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胡母用自己寬容的德行,成功地化解家庭矛盾,用“忍”和“讓”,用智慧控制自己的情緒,用寬容、仁愛與智慧,化千斤重壓于無形,維護(hù)丈夫留下來的表面風(fēng)光的大家庭的團(tuán)結(jié)和氣,也以言傳身教影響兒子并為兒子爭取到盡可能好的成長環(huán)境。

(圖片來自于網(wǎng)絡(luò))
三、“哭”捍衛(wèi)名節(jié)中的剛氣與無奈
認(rèn)知“母親”的第三次“哭”——大聲之哭:
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yè)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里發(fā)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甚么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里,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dāng)面質(zhì)問他,她給了某人甚么好處。直到五叔當(dāng)眾認(rèn)錯賠罪,她才罷休。
胡母還有一個社會性身份——寡婦,俗話說:“寡婦門前是非多。”尤其像胡母這樣年輕長相還算貌美的寡婦,更是如此。然而,胡母的“是非多”卻來自自家的五叔之口。有一天,浪蕩無業(yè)的五叔在煙館發(fā)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甚么好處給他。” 胡母深知對待這一矛盾處理至關(guān)重要:1.關(guān)系到自己的名節(jié);2.以后如何掌管胡氏大家庭;3.兒子的社會地位和前程,如果處理不當(dāng),所有的一切皆會化為泡影。可是,這一矛盾還必須由她自己出面處理,她沒有外援,無人相助,一位身單力薄的寡婦對陣“浪子五叔”純屬逼上梁山的無奈之舉!
怎么辦?胡母主動憤怒出擊,“她氣得大哭”“當(dāng)面質(zhì)問”,胡母不怕、不藏,敢于直面的態(tài)度,讓大家都知道“我是被人誣陷的”。于是,胡母“請了幾位本家來”,一則可以借家族權(quán)威力量將私事公辦;二則便于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有利于大范圍消除影響。要五叔當(dāng)眾說出“給了某人甚么好處”,一則體現(xiàn)自己的正直與清白,維護(hù)自己的尊嚴(yán);二則借此告誡甚至震懾是非之徒;三則讓胡適的兩位嫂子看清自己的另一面——剛性的一面,她不是一個軟弱之人。最終以“五叔當(dāng)眾認(rèn)錯賠罪”,完美收官,達(dá)到預(yù)期目的。
在捍衛(wèi)名節(jié)的大聲之哭中,有剛強(qiáng)與智慧,也有苦楚與無奈!
“哭”是胡母解決問題矛盾的方法、手段,對象不同、矛盾不同、目的不同,“哭”之方法不同,展示性格不同,透過不同的“哭”,我們能體會到一個農(nóng)村婦女、一位母親、一位后母、一位寡婦的智慧,簡單與藝術(shù),平凡與偉大,更能感受到“哭”中的嚴(yán)慈與悲苦、忍讓與無助、剛氣與無奈。正可謂,怎一個“哭”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