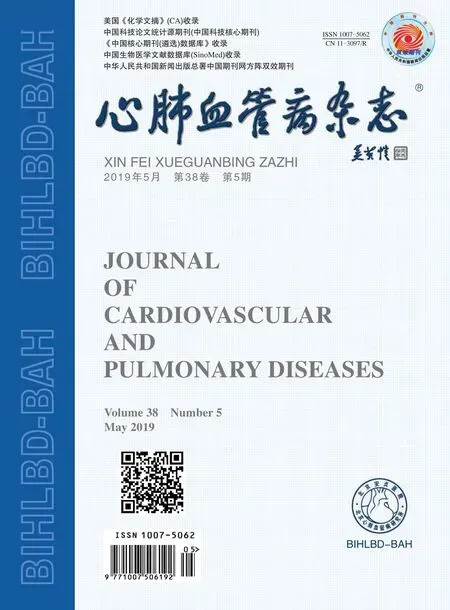雙導絲球囊治療股腘動脈病變的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
閆昌葆 張杰 趙 亮 王艷陽
下肢動脈硬化閉塞癥(arteriosclerosis obliterans,ASO)指由于動脈硬化造成的下肢供血動脈內膜增厚、管腔狹窄或閉塞,病變肢體血液供應不足,引起下肢間歇性跛行、皮溫降低、疼痛、乃至發生潰瘍或壞死等臨床表現的慢性進展性疾病,常為全身性動脈硬化血管病變在下肢動脈的表現。下肢ASO的發病率隨年齡增長而上升,>70歲人群的發病率在15%~20%[1]。股腘動脈硬化閉塞癥是其中最常見的病變之一。
經皮動脈成形術(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PTA),是治療股腘動脈疾病的一種有效方法和基本方法[2]。與開放手術相比,經皮入路的主要優點是并發癥少(0.5%~4%)、高技術成功率(90%)和較低的手術相關發病率[3]。雖然PTA的技術成功率很高,但是其再狹窄、再閉塞和癥狀復發的發生率很高,可以達到40%~60%[4-5]。目前,補救性支架置入可以減少一些早期問題,例如彈性回縮、殘余狹窄和限流性夾層[6-7]。然而,支架的缺點在于血管內永久存在異物導致的并發癥,如支架斷裂,支架血栓形成和后繼治療選擇的限制[8-9]。所以,臨床醫生都在尋找減少支架置入的方法,我中心應用雙導絲球囊進行股腘動脈病變的治療,效果顯著,安全可靠。報道如下:
資料與方法
1.一般資料 選取2016年11月至2017年10月,我中心住院股腘動脈硬化閉塞癥患者,均為初次病變,Rutherford分級2~5級,隨機分為兩組,剔除失隨訪患者,共計67例。A組(實驗組)為雙導絲球囊組,共計患者35例;B組(對照組)為普通球囊組共計患者32例。
(1)納入標準:①年齡>18歲,<80歲;②下肢缺血癥狀為Rutherford 2~5級;③影像學檢查顯示股淺或腘動脈近端動脈病變;④均為初次病變;⑤靶病變為原發單一或聯合病變,狹窄程度70%~99%,或合并完全閉塞;⑥預期壽命至少1年。
(2)排除標準:①不能按要求隨訪患者;②懷孕哺乳期女性;③存在抗凝抗血小板禁忌,及造影劑過敏;④既往1個月內發 生急性心內血管意外;⑤嚴重腎功能不全(血清肌酐清除率<30 ml/min)或嚴重肝功能損害(Child評分C級以上);⑥合并嚴重心腦血管及其他系統疾病無法耐受手術;⑦既往同側下肢動脈手術史。本研究已經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見表1,兩組間性別比例、年齡、術前踝肱指數(ankle brachial index,ABI)、Rutherford分級2/3/4/5、病變長度、吸煙比例、以及合并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心功能不全、腎功能不全、高脂血癥比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n(%),M(QR)]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n(%),M(QR)]
項目 A組(n=35)B組(n=32) P值性別/(男/女) 19/16 17/15 NS年齡/歲 65.9±8.4 69.2±10.1 NS術前ABI 0.61±0.15 0.65±0.17 NS Rutherford分級(2/3/4/5) 10/20/3/2 9/19/2/2 NS病變長度/mm 107(73,152)104(69,141) NS吸煙史 20(57.1) 19(59.4) NS糖尿病 29(82.9) 28(87.5) NS高血壓 27(77.1) 24(75.0) NS冠心病 25(71.4) 23(71.9) NS心功能不全 4(11.4) 3(9.4) NS腎功能不全 7(20.0) 7(21.9) NS高脂血癥 19(54.3) 16(50.0) NS
2.治療方法 本組患者術前均給予阿司匹林(100 mg/d)+硫酸氫氯吡格雷(75 mg/d)抗血小板治療。手術均采用局部麻醉,術前行CTA及下肢動脈彩超評估下肢病變情況,所有操作在導管室DSA下完成,選用逆行穿刺對側股動脈后“翻山”至患肢股動脈,或者選擇同側股動脈順行穿刺,置人6F股鞘,推注肝素(100 U/kg)全身肝素化后,行DSA常規的下肢動脈造影,導絲通過靶病變回到遠端真腔后,先選用直徑小于把血管1~2 mm普通球囊預擴張靶病變,之后再選用與目標血管相同直徑(參考病變段近遠段相對正常的血管管徑決定)的球囊對病變段進行擴張[A組應用雙導絲球囊(vascutrak BARD)],以30 s/atm速度充盈至命名壓,維持3 min,如果到達命名壓未擴開病變,則繼續升壓至爆破壓/B組應用普通球囊快速充盈至命名壓,維持3 min,如果到達命名壓未擴開病變,則繼續升壓至爆破壓,如圖1所示病例),再次造影若遺留狹窄>30%或出現限流性夾層,則置入補救性支架(lifestent BRAD)。若缺乏流出道,同期處理流出道病變,保證至少1支膝下動脈血運到達足部(圖1)。
術后均予以予阿司匹林(100 mg/d)+硫酸氫氯吡格雷(75 mg/d)抗血小板治療雙聯抗血小板治療+瑞舒伐他汀鈣片10 mg/d治療,6個月后根據病情減少為單抗。
3.隨訪及終點 于術后1、3、6、12個月對患者進行電話隨訪并指導其藥物治療及飲食生活習慣調整,于6個月及12個月來院進行下肢動脈彩超及ABI檢查。隨訪項目:①狹窄率,彩超測量靶病變管腔狹窄>50%;②術后6個月及12個月,靶病變區管腔晚期丟失(late lumen loss,LLL),手術后與隨訪時點管腔最小值的差值。③盧瑟福分級改善率及ABI增加值。終點事件:臨床驅動的靶病變再次血運重建(target lesion revascularization,TLR),手術后臨床癥狀復發或惡化,而需要再次在原病變部位行血運重建、治療側截肢以及隨訪期間死亡。

圖1 右股動脈造影圖像 患者女性67歲,診斷為右股淺動脈閉塞 A:術前造影可見股淺動脈閉塞,側枝循環顯影;B:術中應用雙導絲球囊擴張病變段;C:再次造影可見病變段血流通暢無明顯殘留狹窄及限流性夾層,未置入支架
4.統計學方法 數據處理采用SPSS 20.0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非正態分布資料采用中位數(M)及四分位數間距(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率)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治療結果 本研究納入的所有患者技術成功率及血流動力學成功率均為100%,圍術期未發生嚴重并發癥,雙導絲球囊組支架置入率為62.9%低于普通球囊組的84.4%,術后即刻患者癥狀均改善(表2)。
2.隨訪結果 1年隨訪結果顯示,雙導絲球囊組ABI增加值、盧瑟福分級改善率均大于普通球囊組,而再狹窄率、LLL及TRL均小于普通球囊組,差別有統計學意義;兩組的截肢率及全因死亡率差別無統計學意義。其中共10例再閉塞患者中4例自行停藥,3例未戒煙,3例血糖控制不佳,其中1例盧瑟福5級患者因患足全足壞疽予以大腿中段截肢術,其余患者再次行介入治療,均予以補救性支架置入。兩組患者共計死亡9例均為合并冠心病且盧瑟福分級4~5級。所有病例均未發生支架斷裂及移位(表2)。

表2 兩組患者隨訪1年數據比較[n(%),M(QR)]
討 論
隨著人口老齡化及糖尿病發病率的升高,ASO癥發病率持續增長[10],股腘動脈是最常見的累及部位之一,可導致間歇性跛行,嚴重的肢體缺血,潰瘍和壞疽。而25%未進行血運重建治療的跛行患者將在4~7年內發展為慢性嚴重的肢體缺血(critical limb ischemia,CLI), 每年截肢率約為10%[1]。 因此,ASO患者的有效血運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臨床意義。
在目前的臨床實踐中,腔內治療已成為多數股腘動脈ASO患者的首選,由于對于高危患者腔內治療可能是唯一選擇[12]。指南推薦的最基本和首選方法是PTA,或者支架置入,而第二代鎳鈦合金自膨式支架的上市,使股胭動脈段病變的治療效果得到改善[13]。雖然支架的應用提高了近期效果,但是遠期效果和保肢率并沒有比單純的PTA有優勢,這主要由于大腿的反復運動對支架的擠壓導致支架斷裂、再閉塞等問題,以及在再次處理的困難[14]。在一項研究中,PTA+支架1年、3年、5年通暢分別為75%、66%、55%可以看到其遠期通暢率并不很高;另外的研究中,Wallstents支架內再狹窄率在1、2和3年分別為46%、66%和72%,而鎳鈦支架分別為20%、36%和53%,Wallstents支架10%、15%和18%的患者在1、2和3年出現臨床惡化,而鎳鈦支架的臨床惡化率分別為4%、5%和5%。Wallstents斷裂率為19%,鎳鈦合金支架斷裂率為28%[14]。可以看到支架存在很嚴重的問題。
目前越來越多的治療方法,均立足于降低支架置入率,“介入無置入”新理念越來越被重視[15],例如生物可降解支架、機械性斑塊切除術、激光血管成形術,冰凍球囊成形術等由于各種原因,都沒有在臨床中廣泛普及。雖然,紫杉醇涂層球囊血管成形術(drug coated balloon,DCB)與標準的PTA相比,對股腘動脈初次病變和支架內再狹窄均有較好的治療效果,主要在于其降低了再狹窄率,并且具有良好的臨床結果[16]。Tepe等的一項股腘動脈閉塞治療的隨機試驗的12個月結果顯示,DCB的通暢率82.2%,TLR率也明顯低于普通球囊組[17],另有一項研究,對119例接受DCB血管成形術或普通球囊治療的患者進行隨機對照試驗,其結論是DCB血管成形術較少復發,再狹窄率(DCB為15.4%,普通球囊為44.7%),在免于TLR和盧瑟福類別的改善方面,其臨床效果更好。在安全方面沒有明顯的差別[18]。但是,DCB球囊可能存在的問題有:藥物涂層轉運過程中泄漏到循環系統導致全身藥物吸收及遠端動脈藥物聚集,并且可能增加血栓概率并需要延長抗血小板時間,從而增加出血風險以及不可重復使用,增加治療費用等。雙導絲球囊在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的治療中得到很好的應用,但其在下肢ASO的應用才剛剛開始。我們的研究中,應用雙導絲球囊組的支架應用率為63%明顯低于對照組的85%,更接近“無置入”理念。而且可以反復使用,并且無藥物殘留。
雙導絲球囊具有以下特點:①低壓擴張,腔外雙導絲實現球囊擴張時壓力聚焦,使球囊達到理想的擴張效果時所需壓力更低,減少血管壁損傷;②可控擴張,擴張作用沿著兩條導絲開始,實現對病變的可控擴張,病變斑塊規則分離,減少血流受限夾層;③聚焦擴張,更有效斑塊成形,減少彈性回縮,獲得最大的管腔,提高遠期通常率和臨床療效,對于鈣化病變尤其適用,可使病變充分擴張,斑塊高效轉化。擴張病變時,雙導絲球囊的固有導絲和標準導絲在小壓力的狀態下聯合使用,明顯促進斑塊斷裂,同時又保證球囊在擴張時不易移位。此球囊同時具備了切割球囊和普通球囊的優點,即在規則切開斑塊組織時,對內膜的損傷較小。并且,臨床上雙導絲球囊造成血管撕裂的機會較少,且多為A、B兩型,嚴重撕裂極為罕見[19]。本研究中,正是由于雙導絲球囊擴張對內膜損傷更小,彈性回縮以及限流性夾層的減少而降低了支架置入率,并且雙導絲球囊組ABI增加值為0.31(0.16,0.39)、盧瑟福分級改善率88.6%均高于普通球囊組,而再狹窄率17.1%、LLL 0.5(0.1,0.9)mm及TRL 11.4%均明顯低于普通球囊組,說明其臨床效果更優,但是,在保肢率方面兩組無明顯差異,有待增加樣本含量及隨訪時間進一步研究。
我們手術中的經驗有以下幾方面:①按照球囊與管腔直徑1∶1選擇球囊;②球囊長度以覆蓋整個病變為宜,盡量避免同段反復擴張;③壓力緩慢擴張,增長速度1ATM/30S;④低壓擴張,不超過爆破壓;⑤擴張病變,尤其鈣化嚴重處,可適當延長擴張時間;⑥緩慢釋放球囊壓力。期待更多中心分享更多經驗。
本研究中,1例大腿中段截肢患者及9例死亡患者均發生于盧瑟福4~5級患者,并且均合并冠心病。有研究標明,CLI患者截肢率為14.3%~46.4%[20],并且泛大西洋協作組織回顧研究證實診斷為CLI的患者6個月后有20%死亡,40%截肢生存,只有40%不截肢生存,而導致死亡的主要是心血管事件[21]。這更加說明,ASO僅為全身動脈硬化的外周血管表現,心腦血管不良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下肢動脈ASO患者的預后。因此,充分評估患者健康狀況和預期生存時間,制定個性化治療方案,盡可能地減輕治療對心腦血管的影響,在不影響總體生存率的同時提高保肢率和通暢率,是血管外科醫師應遵循的原則[1]。
10例再閉塞患者中4例自行停藥,3例未戒煙,3例血糖控制不佳,都是由于對疾病預后認知差以及監護不足引起,Jayakody的研究中也提示同樣的問題,所以術后隨訪和敦促患者藥物治療及生活方式治療仍有待提供[22]。
總之,我們的研究表明,雙導絲球囊操作簡便,治療股腘動脈硬化閉塞臨床效果顯著且安全,但仍然需要增加隨訪時間,總結遠期效果。加強院外隨訪及生活干預對于術后患者療效的鞏固意義重大。對于嚴重肢體缺血患者,更加應該重視其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