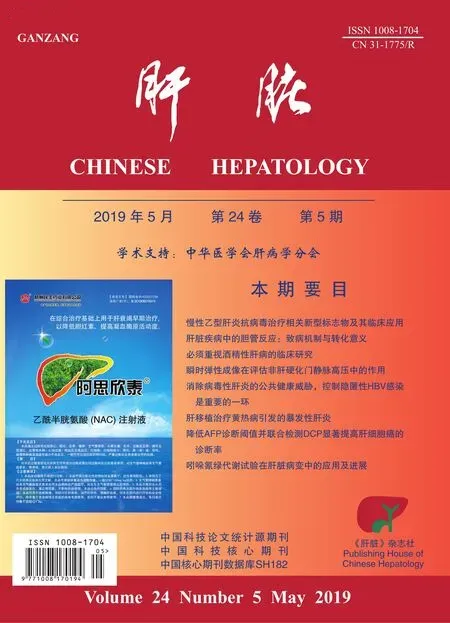降低AFP診斷閾值并聯合檢測DCP顯著提高肝細胞癌的診斷率
周宇辰 袁國盛 胡承光 劉俊維 任彥瑜 唐淬蓉 于樂成 楊定華
大多數肝細胞癌(HCC)病例在初始階段無癥狀,難以早期診斷,是其預后極差的關鍵因素[1]。血清甲胎蛋白(AFP)診斷HCC的準確性和特異性近年來不斷受到質疑,加上釓塞酸二鈉(普美顯)增強磁共振等影像學檢查的逐漸普及,在最新的歐洲肝病學會(EASL)和美國肝病學會(AASLD)的相關指南中已不再將AFP作為HCC診斷和監測的首選[2-3],但目前在我國,AFP聯合腹部超聲仍然是最常用的篩查HCC的方法和早期診斷標準[4]。雖然有學者提出降低AFP的診斷閾值可提高其對接受抗病毒治療患者的早期HCC診斷率[5],但AFP用于HCC早期診斷的特異性和敏感性均不能令人滿意。臨床上亟需其他高效簡潔的監測指標和診斷策略用于早期發現HCC患者。脫-γ-羧基凝血酶原(DCP),又稱維生素K缺乏或拮抗劑誘導的蛋白質(PIVKA-II),目前被認為是HCC早期診斷的“新希望”,已被列為HCC腫瘤標志物[6]。本研究測定HCC組和非HCC組血清中AFP、DCP濃度,探討降低AFP診斷閾值并聯合DCP檢測的診斷策略在早期診斷HCC中的臨床應用價值。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以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肝膽外科和肝病中心就診的128例患者為研究對象,其中男112例、女16例,年齡18~75歲。根據《原發性肝癌診療規范(2017年版)》[4]對患者進行分組:HCC組(均由肝組織病理檢查結果確診為HCC)75例;非HCC組(慢性乙型肝炎15例、乙型肝炎肝硬化25例、慢性丙型肝炎2例、健康人群11例)53例。所有研究對象留空腹靜脈血3 mL,立即送往實驗室分離血清,并在6 h內完成所需血清標志物的檢測。操作過程嚴格按照儀器和試劑說明書進行。
二、檢測儀器試劑和方法
DCP檢測采用富士G1200分析儀,試劑盒購自富士瑞必歐株式會社,采用電化學發光法檢測;AFP檢測采用羅氏Cobas e 601全自動電化學發光免疫分析儀,試劑盒由瑞士羅氏診斷產品上海有限公司提供,采用電化學發光法檢測。
三、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18.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描述,采用t檢驗進行組間比較;計數資料用比例(%)表示,采用卡方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分別繪制AFP、DCP、AFP聯合DCP時的ROC曲線,根據其曲線下面積,計算其對應的靈敏度、特異性評估不同診斷閾值的AFP、DCP及其組合對HCC的診斷效能。
結 果
一、HCC組和非HCC組基線特征比較
HCC組和非HCC組在年齡、性別、ALT、AST、總膽紅素、血小板(PLT)、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標志物、丙型肝炎病毒血清標志物等基線特征上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1。

表1 HCC組和非HCC組基線特征比較
二、ROC曲線分析不同診斷閾值的AFP及DCP對HCC的診斷效能
以非HCC組為對照,繪制ROC曲線,計算得出AFP、DCP曲線下面積分別為0.789、0.882,根據約登指數最大為最佳的原則,得出用于診斷HCC的血清AFP最佳濃度為22.6 ng/mL(P<0.001)、DCP最佳濃度為39.0 mAU/mL(P<0.001),此時AFP對應的診斷靈敏度為66.7%、特異性為88.7%;DCP對應的診斷靈敏度為72.0%、特異性為94.3%。如果兩個血清學標志物獨立進行HCC的診斷時,無論是靈敏度還是特異性,DCP的功效均比AFP高。見圖1。

圖1 早期肝細胞癌患者分別檢測AFP和DCP的ROC曲線
三、聯合檢測AFP和DCP的ROC曲線分析并與單項檢測時比較
以HCC組為研究組,非HCC組為對照組,繪制ROC曲線,計算得出聯合檢測AFP和DCP的曲線下面積為0.906(P<0.001),此時對應的診斷靈敏度為77.3%、特異性為90.6%,診斷HCC的功效性均高于單獨檢測血清中AFP或DCP的濃度。見圖2。

圖2 早期肝細胞癌患者聯合檢測分析AFP和 DCP結果時的ROC曲線
四、AFP和DCP的相關性分析
分別對全部研究對象(128例)和HCC組(75例)做AFP和DCP的相關性分析。在全部研究對象中,AFP和DCP的Pearson相關系數r=0.058,P=0.260,表明兩者無相關性。在HCC組中,AFP和DCP的r=0.025,P=0.446,表明兩者無相關性。
討 論
HCC是我國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目前其總體5年生存率不足15%,位居惡性腫瘤相關死亡的第三位[7]。AFP在國內被廣泛用于篩查HCC,其診斷標準為AFP≥400 μg/L,漏診率通常在40%左右。研究表明,較多HCC患者僅有AFP輕度升高,特別是小肝癌(腫瘤直徑<3 cm),其AFP水平可無變化[8-10]。而其他肝臟疾病,如部分慢性肝炎、肝硬化及肝臟良性疾病中AFP水平可有不同程度升高,若增加診斷閾值會進一步降低HCC的檢出率。為給出HCC發生的早期預警,有學者提出可通過降低AFP診斷閾值來提高早期HCC的診斷率。本研究發現,單獨的AFP定量診斷HCC的ROC曲線下面積為0.789,進一步分析發現當AFP診斷閾值降為22.6 μg/L時,靈敏度和特異性之和最大(1.554),對應的靈敏度為66.7%、特異性為88.7%。上述結果與田州[11]、丁國華等[12]的報道一致,提示若單獨依靠AFP篩查,其較低的敏感度和特異性容易造成HCC漏診或誤診,但通過適當降低AFP診斷閾值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診斷效能。
近年來血清DCP濃度檢測逐漸應用于臨床診斷HCC,DCP是一種異常凝血酶原,最早于1984年被發現[6]。有研究認為,早期HCC患者體內DCP升高的原因為:①維生素K在體內含量減少或利用功能下降;②肝癌細胞內的γ-谷氨酰羧化酶出現功能紊亂;③肝癌細胞在增殖過程中凝血酶原前體過度生成。本研究結果顯示,單獨DCP診斷HCC的ROC曲線下面積為0.882,進一步分析發現DCP診斷HCC的最適臨界值為39.0 mAU/mL,對應的靈敏度為72.0%、特異性為94.3%,均高于AFP。提示DCP可作為獨立診斷HCC的血清標志物,且有較高的診斷價值。更重要的是,當聯合AFP和DCP用于診斷HCC時,其ROC曲線下面積高達0.906,靈敏度和特異性均明顯提高,與國內外研究結果[13-15]一致,提示DCP結合AFP檢測可作為輔助診斷HCC的血清標志物組合。
此外,DCP和AFP之間沒有基因表達上的相互關聯,兩者在HCC檢測中能起到良好的互補作用。本研究中,對全部研究對象進行相關性分析,AFP和DCP的Pearson相關系數r=0.058,P=0.260,表明兩者無相關性。在HCC組,AFP和DCP的r=0.025,P=0.446,亦表明兩者無相關性。
綜上所述,DCP可作為獨立診斷HCC的血清標志物,靈敏度和特異性均較高,對早期發現HCC具有較高的診斷價值,能鑒別診斷其他肝臟疾病;并與AFP有很好的互補作用。通過降低AFP診斷閾值并聯合DCP檢測可以提高診斷的靈敏度和特異性,較大程度地避免臨床上單一使用AFP指標及采用較高診斷閾值所引起的漏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