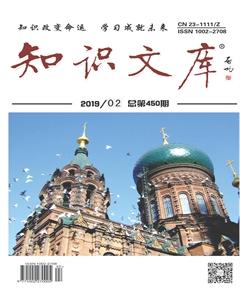張愛玲創作的審美意識表達
邢瀟月
三十年前的曹七巧因兄長包辦婚姻,葬送了一生的幸福;三十年后身為人母的她,運用同樣的手段扼住長安的生命,剝奪長安的自由,使長安不得不重蹈其母一生缺愛的覆轍。張愛玲說:“傳統的本身增強了力量,因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人,新的事物與局面上。”“只有在中國,歷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維持活躍的演出。”無論哪個時代,孩子身上總會存留著父母親或多或少的痕跡,并于生命運行中變本加厲地展現出來。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金鎖記》中看似最主要的主人公是“活招牌”成為被金鎖禁錮成“瘋婆娘”的曹七巧。然而在文末落筆之時,我們可以分明地感受到張愛玲想講述的并不僅僅是這個反人母的形象,同時所慨嘆的還有身為女兒——長安的悲劇命運。三十年前的故事完不了,七巧最終橫在煙鋪上離開了人世,可她的兒女還在,兒女也許還會有兒女。
1 《金鎖記》中長安悲劇性格的塑造
長安和哥哥長白的出場就是由母親在與姜家人財產糾紛時,口中哭號的“孤兒寡母”開始的。分家之后,長安一直過著深宅大院的生活,出行前后有仆人相隨。然而長安到了十三四歲的年紀,因為身材瘦小,看上去像個七八歲的孩子。她身體不好,任仆人再怎么認真照顧,都換不來那個守著金枷鎖發瘋的母親的一點點關心。和表哥在家里玩耍闖了禍,七巧就滿口胡言地指責她那個十幾歲的侄子將要贏取長安以達到搶占她們家財產的目的。教育長安:“天底下的男子都一樣混賬,誰不想要你的錢?”叫她提防“男人們”。這也許是這個本該在青春期懵懂的女孩子,第一次對異性的一點有“教育意義”的認識。母親要“看住”長安,不讓女兒破了 “男女授受不親”的舊俗,便“依照老法規矩”為長安裹起腳來。雖然當時已進人“放足”盛行的時代,但是,新勢力如何敵得過宗法制度下父母對子女的絕對權威。十四歲的長安,儼然是一位毫無獨立人格的“兒童”,注定是父母的附屬品,受母親掌控;在男性霸權的社會中,“女童”生來便是個悲劇,不得不依照男性設定的標準來成長,為的是長大后成為柔順的妻子,規矩的兒媳。長安生在守舊而沒落的大家族中,那里沿襲著許多傳統陋習。長安似乎比現實中這些悲慘的女孩幸運一些,她的腳“裹了一年多,七巧一時的興致過去了,又經親戚們勸著,也就漸漸放松了”。然而,心受形體所役,在她的心靈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疤。以致每當長安向不公的命運反抗時,這塊心中的疤便隱隱作祟,悲涼地說,這便是你的宿命,無法改變。
自經歷了裹腳之后,長安以自我放逐的方式瘋狂地吸鴉片,在自我擬構的幻境中,她吸掉了身體內的病痛,抽掉了令她精神窒息的母親,吸掉了不斷啃食靈魂的孤獨。心理學家弗洛姆指出,為了擺脫孤獨,人們沉溺于“不同形式的縱欲:自我引起或借助于毒品的恍惚狀態就是一種形式的縱欲……但在縱欲以后他們的孤獨感卻加劇了,所以不得不更經常地,更強烈地去重復縱欲行為”。長安深受宿命的捆綁,她曾是一位天真善良的女孩,可那個時代竟容不下這樣的女子。在與命運的斗爭中她一次次慘敗,她委屈、孤獨、恐懼,只好把自己封閉起來,向過去的美好記憶尋求撫慰。
2 人物性格與時代背景
長安所生活的時代,正處于“舊的東西在崩壞,新的在滋長中”的一種狀態。幸運的是,她于茫茫人海中遇見了海歸紳士童世舫,一位愿意娶她為妻的男人。然而,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世界里的長安與世舫之間,很難產生真愛。同時母親曹七巧的詭計直接毀掉了長安的婚事,其母曹七巧正是無愛婚姻的犧牲者,她失去了所有愛與被愛的權利與資格,并于不知不覺中把這種犧牲延續到子女身上。 “長安靜靜地跟在他后面送了出來,臉上顯出稀有的柔和。世舫回過身來道:‘姜小姐……她隔得遠遠地站定了,只是垂著頭。世舫微微鞠了一躬,轉身就走了。”長安傾盡所有,面對愛人離去的背影,她遠遠地跟在后面,最后再看他一次,何等凄涼。
長安,雖然沒有像曹七巧那樣“瘋得徹底”,但長安卻是最有力的“時代的負荷者”,在她的身上,反映出那個時代以及千百年來中國傳統女性的歷史宿命。宿命,是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主宰人的一生,它才是造成長安悲劇命運的真兇,而歷史以及那個時代的傳統是宿命中最堅不可摧的部分。張愛玲正是透過七巧、長安來控訴傳統女性的宿命,并從長安身上看當時與當下的女性又遭受著怎樣的磨難,并透過歷史循環的“蒼涼的啟示”,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人生哲學,來實現自我解脫。
3 現實生活對審美創作的影響
記得一開始讀張愛玲,她筆下的那份陰郁氣質像件灰色的披風,籠罩在我的思維里,間隔多日都揮之不去,不懂這種壓抑的筆觸意義何在,女性角色的悲劇命運更使身為女性的我感到悲憤、蒼涼,向被扼了喉嚨,難以吞咽;墜著墨綠色小絨球的絲絨窗簾經風吹過才得以讓七巧的起坐間見得隱約的天光,感覺自己都被那繚繞的煙霧所嗆到。以至于很久都不再碰這些讀物,情愿投身“青春文學”,反倒會覺得讀起來實際。
如今再讀張愛玲,又零零星星了解了作者本人的身世,發現其作品并沒有之前淺薄涉獵時所感受得那么晦澀。現實生活中的張愛玲,這位傳奇女子,亦是長安宿命的投影。因與后母關系不和,父親竟對張愛玲拳腳相加,并將她關入空屋子里。期間,張愛玲生了嚴重的痢疾,生宛攸關,可父親沒有為她請醫生,讓女兒受病痛折磨了整整半年。張愛玲把這種抹不掉的傷痛真切地注人到長安的身上,加之以精道的歷史書寫,將那個宗法制度下的吃人社會揭露出來。
從周冠生的審美創造的自我社會價值實現需要說來看,作者的創作源自于自我宣泄需要、自我認同需要和自我奉獻需要。1941年,在被母親拒絕了求助之后,沒有選擇結婚,拒絕依附男人安穩度日。追求自立的張愛玲開始在報紙上發表一些小文章賺取稿費糊口。我想一開始她的創作需要也許是自我宣泄的需要,民國只有一個張愛玲,正是她宣泄了自己不幸的遭遇,加以藝術化的創造,才誕生了這些形形色色的女性角色。然而在那個年代,使第二層自我認同的需要并沒有得到太多實現。當看到文學大會上整齊劃一的中山裝讓張愛玲感到害怕,她害怕自己在這樣的環境中迷失自己,于是她放棄去尋找“知音”、對她有認同感的人,只身前往美國。當大陸在度掀起張愛玲熱的時候,她已經在美國安家。《審美心理學》中認為最高層的創作需要,自我奉獻需要,是建立在對國家、對社會的奉獻之上的。我倒認為這個出發點過于龐大籠統。張愛玲的創作并不是像貝多芬一樣,在失聰的情況下創作出《第九交響曲》,但不并不能就此斷言她是沒有自我奉獻需要的,雖然身體上的痛苦沒有深重到如此地步,但精神上受到的傷害足以讓她刻骨銘心。而張愛玲正是忍痛揭開了這些鉆心的痛,以瑰麗奇異的文筆從一個女性的角度記錄了當時的中國,才讓現在的我們看得到,思考得到。
4 結語
《金鎖記》中的長安這一個人物形象是悲劇的,她的命運被視財如命又尖酸刻薄的自私母親所掌控,然而漸漸長大的長安開始覺得犧牲是不值得的,她放棄上進的思想,安分守己起來,學會了挑是非,是小壞,干涉家里的行政。她時不時和母親慪氣,可她的言談舉止越來越像她母親。這種輪回讓我想起最近一個綜藝辯論節目中,關于“我們終將成我自己討厭的人是壞事嗎?”的討論。辯手并沒有提及中國傳統女性悲劇命運的輪回,但有一句話讓我十分認同:“跳出輪回的人才是偉大的。”面對命運的輪回,曹七巧從抗爭走向了墮落,其女長安稍有不同,她看到了命運的反復,卻選擇安之若命。而張愛玲卻截然不同,悲劇的命運并沒有打倒她,一些發生在長安身上、零零星星的事也是她的生活經歷,與書中人物的怯懦不同,張愛玲不愿受到暴虐的父親、刻薄的后母、只在乎金錢的母親的影響,她背負著痛苦,利用自己的所學和才華,努力地去跳脫出這個悲劇的輪回,不惜揭開自己的疼痛,好清楚地讓世人看到這悲劇的所在。所以張愛玲才可以稱之為偉大的作家,她的作品才可以稱之為偉大的作品。
(作者單位:西安電子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