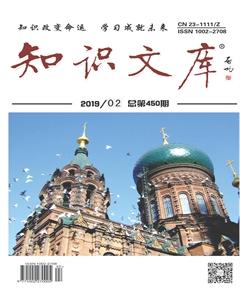中古蘇州三種方志考論
祖胤蛟
中國的地方志編修,自以明清為盛。朱明以前,方志流傳至今極少,一緣刊刻不多,二緣厄難不存。中古典籍,十不存一。故中古的傳世方志,極為后人所重。而江南兵燹較北方為少,故存世方志較北方為多。然其亡佚錯亂,脫訛舛誤,致歷代爭議考證不絕。本文特擇中古較為重要的三種蘇州地區方志,試考其流源,論其疏訛。
此三種志書分別為《吳郡記》一卷(晉顧夷撰)、《吳地記》一卷(晉張勃撰)、《吳地記》一卷、又附后集一卷(唐陸廣微撰)。
1 晉顧夷所撰《吳郡記》一卷。《隋書經籍志》有著錄。原書已佚,清王謨《漢唐地理書鈔》有輯本,張國淦《大典輯本》有輯本。
《隋書·經籍志》著錄顧夷《吳郡記》有兩條,一條為“一卷”,一條為“二卷”。后人多有考證。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言:“是書隋志凡兩見,前作一卷,后作二卷,當是復偽。”張國淦先生《中國古方志考》:“《隋志·吳郡志》一卷,系據齊陸澄《地理書》,《吳郡記》二卷,系據梁任昉《地理書》,《隋志》類此者不一。”后多以張國淦先生之說為準。
然考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其言“《吳郡記》一卷。顧夷撰。《后漢書·楚王英列傳》注: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引顧夷《吳地記》。《史記·高祖本紀集解》:‘顧夷曰:余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漢書·伍被列傳》注:‘吳闔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后漢書·彭修傳》注:‘延陵漢改曰毗陵。《北堂書鈔·酒食部》:‘長城若下出美酒。《初學記·地部》:‘山東兩嶺相趨,名曰銅嶺。并引《吳地記》,不著顧夷名。”時人所引皆作《吳地記》,而非陸澄、梁昉《地理書抄》所著錄《吳郡記》。唐宋人相關著述亦是引《吳地記》多于《吳郡記》,在此不贅錄。故丁氏所言兩種《吳郡記》乃重復著錄,是著眼于時人后人所引皆為《吳地記》。然仍有另一種可能,便是《隋志》著錄的兩卷本《吳郡記》實則是顧夷所著的《吳地記》,與一卷本《吳郡記》實系兩書。
后人撰述姑蘇地方著作,幾乎必引顧夷之作,可見其要。
2 晉張勃所著《吳地記》一卷。原書已佚。《舊唐書·經籍志》有著錄。
此書與顧夷《吳地記》不同,非是記述姑蘇地志,而是記述三國東吳州郡,故其所述及“交趾”、“蒼梧”等地。因此便引出一則公案——張勃《吳錄》與《吳地記》的關系。
《文選》卷二十八吳注引張勃《吳錄》,陸廣微《吳地記》引張勃《吳錄》,文廷式以此《吳錄》乃《吳地記》。而王謨《漢唐地理書鈔》輯有張勃《吳地理志》,并于敘錄中稱《吳地記》為《吳錄地理志》之一部分。此兩種說法尚未定論,而學界亦未對此作出相關考證。
私以為王謨所言更為妥當。按《隋志·吳紀》九卷下注云“晉有張勃《吳錄》三十卷,亡”,而至《唐志》著錄,《吳地記》僅為一卷,并未著錄“殘余一卷”,可見《吳地記》至唐代乃完整一書,極有可能是《吳錄》三十卷中的一卷。
3 唐陸廣微所撰《吳地記》一卷、附后集一卷。兩《唐志》皆不載,《直齋書錄解題》始著錄,后《宋史·藝文志》亦著錄。
其正書流傳,由于兩唐書無載,后世多有所疑。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多記古吳國事。唐末有秀州,天禧中始割嘉興縣置,故此記合二郡為一。”言下之意陸廣微乃天禧后人。而此書中諸多疑亂,《四庫總目提要》辨之甚力。《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三》“吳地記”條:
舊本題唐陸廣微撰。《宋史·藝文志》作一卷,與今本合。書中稱周敬王六年丁亥,至今唐乾符三年庚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則廣微當為僖宗時人。然書中“虎疁”一條,稱唐諱虎,錢氏諱镠,改為滸墅。考《五代史·吳越世家》,乾符二年,董昌始表錢镠為偏將。光啟三年,始拜镠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景福二年,始拜镠為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始加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始封镠為彭城郡王。天祐元年,封吳王。至朱溫篡立,始封镠為吳越王。安得於乾符三年以董昌一偏將能使人諱其嫌名?且乾符三年亦安得預稱吳越?至錢俶於宋太平興國三年始納土入朝,當其有國之時,蘇州正其所隸,豈敢斥之曰“錢氏”?尤顯為宋人之辭。則此書不出廣微,更無疑義。王士禎《香祖筆記》嘗摘其語兒亭,馮驩宅,公孫挺、陳開疆、顧冶子墓三條,又摘其“琴高宅”一條。於地理事實,皆為舛繆。又案乾符三年歲在丙申,實非庚申。上距周敬王丁亥,僅一千三百九十年,實非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於年數亦復差誤。觀其卷末稱“纂成圖畫,以俟后來者添修”。而此本無圖,前列吳、長洲、嘉興、昆山、常熟、華亭、海鹽七縣,而后列吳縣、長洲縣事為多。殆原書散佚,后人采掇成編,又竄入他說以足卷帙,故訛異若是耶!以今世所行別無善刻,故姑仍吳琯此本錄之,以存梗概,而附訂其牴牾如右。又《吳地記后集》一卷,蓋續廣微之書者,不著撰人名氏。前有題詞,稱“自唐王郢叛亂,市邑廢毀,或傳記無聞,或廢興不一。謹采摘縣錄,據圖經,選其確實者列於卷后”。所記建置年號,止於祥符元年,疑北宋人作。舊本附錄,今亦并存備考焉。
《總目》以“今唐乾符三年”斷定陸廣微為僖宗時人;“避錢鏐諱”“預稱吳越”“妄斥錢氏”三條,佐證此書為宋人所作而非陸廣微;又以訛異頗多,為后人采掇成編。
《總目》此論不確。此書中有諸多唐代舊語,而非宋代時語。
如天禧年間始割嘉興置秀州,而《吳地記》只載嘉興,未載秀州,可見此處為天禧前文字。又如“永定寺”“流水寺”等地名,至宋已改,而書中仍用,可見亦是唐人文字。
北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岝崿山”條:“在吳縣西南一十五里。……《吳地記》云:吳王僚葬此山。山旁有寺,號曰思益,樂天嘗游之。”今本《吳地記》云:“岝崿山,在吳縣西十二里。吳王僚葬此山中。有寺號思益,梁天監二年置。”兩者相合。
然而此書中確有諸多兩宋人后入文字。
除卻《總目》所提三條,又如卷首“續添”吳江縣一條,乃五代所置,當是宋人添補。《后集》則更為宋元人所撰,自無疑義。
故《吳地記》一書當為陸廣微撰,而后人作注時散入正文,合而刊行,故其文字時唐時宋。
至于其版本流傳,最早可見為明本——萬歷年間吳琯刻《古今逸史》本、萬歷年間鐘仁杰、張遂辰輯《唐宋叢書》本、天啟年間《鹽邑志林》本與宛委山堂《說郛》本。其文字大同小異。其余版本不再贅述。又原書自言有圖,而今本無圖,蓋亡佚矣。
魏晉地書或專記輿地,或專記人物,至唐便有合并之勢。陸廣微《吳地記》便是如此。此書先記建置,再記沿革,人物史事穿插其中;后略記山川形勢,名勝橋寺,業已粗具后世方志框架。其名實淵源,多為后人所引。
此書又記古吳字,可備上古音韻文字參證。郝懿行作《方言》一文有言(此處用繁體):“吳人謂腌魚爲膎脼。《集韻》:‘《釋名》:鮓,滓也。以鹽米釀之如菹,熟而食之也。案:鮓同鮺。陸廣微《吳地記云》:‘闔閭思海魚,而難於生致,治生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鮺。讀如想‘《困學紀聞》四卷。案:王氏此讀,非也。鮺,從魚,差省聲,非從養省聲,讀如想,誤矣。(案:‘讀如想三字,是王伯厚語)。今俗讀想,以爲海魚之名,亦誤。《周禮·籩人》注:‘鱐者,析乾之,出東海。即《吳地記》所謂鮺也。”陸廣微《吳地記》記方字而不記方音,蓋陸廣微唐末人,言語全然不與上古音同,或加之學識有限,故難以切讀古音也。后世方志增“方言”條例,音、字皆記,是宋后方音定型,便于記錄矣。
然此書記輿地沿革處,舛誤甚多。今試舉二例。
王士禎《香祖筆記》卷四:“陸廣微《吳地記》所載,如語兒亭等,最為可笑。又多可疑者,如馮諼宅,謂在吳縣東北二里五十步,有彈鋏巷;又謂海鹽縣東十五里有公孫挺、陳開疆、顧冶子三墓,尤謬。”王士禎所舉“語兒亭”、“馮諼宅”、“彈鋏巷”、“三子墓”,皆陸廣微《吳地記》謬誤處。
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長洲縣建自唐萬歲通天中,非貞觀七年;常熟縣,梁以毗陵改置,非貞觀九年。”《吳地記》記長洲、常熟二縣建置年歲有誤。
故陸廣微此書,于體例,上承魏晉地書,下開宋元方志;于沿革,鉤沉扼要,多記上古吳國事。然訛誤甚多,后世著作若引證此書,讀閱時則須仔細辨別。
后世蘇州地區方志幾乎全部仿效引用此三種書。至兩宋,蘇州地區志書撰述興盛,有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范成大《吳郡志》等,體例內容皆與后世方志等量齊觀。乃至明清,江南為天下甲富,方志纂修更是蓬勃。而其源流上達中古地書,傳至今世者已然寥寥。故考察現存中古地書的版本源流,對其進行校勘訂正、輯佚補闕是無法繞開的。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