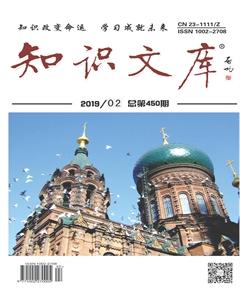淺談《百家講壇》與歷史知識傳播
趙靜
百家講壇以電視為媒介,其特點自然鮮明:畫面傳播,一看即懂;聲像并茂,視聽兼容;形象生動,優美感人;電視傳播的范圍廣闊,人數眾多。它們聲像兼備、視聽兼顧,具有雙通道視聽優勢和現場參與感。作為電視文化,屬于大眾文化的范疇。
從各個方面來看,“百家講壇”都是個奇跡:一個在“絕對睡眠時間”播出的節目,收視率曾經連續三個季度在央視十套綜合排名第一,CCTV網上點擊率第一;講稿書《易中天品三國》發行 130萬冊,于丹《論語心得》不到一周發行 80萬冊;影響所及,人人讀經,全民說史。一個人,一張講臺,沒有主持人,沒有話題,就是講故事,形式簡單到不能再簡單,成績優異到不能再優異---這是在七八年前。
最輝煌的時候顯然已經過去,但是,到目前為止,“百家講壇”仍然是歷史傳播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平臺。
“百家講壇”的口號是“電視使學者有為,學者使電視深刻”,意欲以電視為媒,使學者得以服務、影響社會。在電視節目娛樂化、信息碎片化的時代,這種追求尤為難能可貴。只是,學者如何在“有為”的同時保守其學術底線,而電視又如何在“深刻”的同時留住觀眾,這是一個大問題。在學者與電視的關系中,學者相對被動;在電視與觀眾的關系中,電視又相對被動。嚴謹的學者希望在服務的同時引導觀眾,傳遞真實的歷史信息,引發嚴肅思考,然而,觀眾可能早已換臺離去。學者上電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名利之外,有大義在,有傳播的責任,要守住學者的底線,也要學習講述的方法。作為一名中學歷史教師,我想表達以下幾點感想:
第一,嚴肅的學者應當有意識地與“說書人”劃清界限,這個界限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指內容上的“求真”。(一)要做到盡量一切從史料出發,從靠譜的史料出發。比如,講北宋事,用《續資治通鑒長編》肯定比《宋史紀事本末》靠譜得多。(二)盡量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做到我們談到的每個人、每件事、每種制度,言之有據。以上兩點,是歷史學的看家本領,是底線。只有守住這兩點,才能防止變成“說書人”.我國有悠久的史學著述傳統,然而史學著述多屬官方或士大夫個人行為,普通民眾對歷史也有濃厚的興趣,然而這種興趣往往不以“求真”為前提,整個社會習慣于接受戲說的、大線條式的、教化式的東西。我們缺乏非虛構性歷史閱讀傳統。歷史學家上電視講故事,應當樹立一種不一樣的“求真”的范式。講真實的故事,不故意夸張,嘩眾取寵,以真實取勝,慢慢地引導觀眾區分真偽,學習從真實中汲取力量。
第二,深入淺出不容易,上電視對大眾講歷史,需要更廣闊的專業知識面。目前大學的歷史學專業教育,是培養專家的路數,從本科、碩士以至博士,越向上走,越細致艱深,斷代中更分時代,時代中更分專題。這樣做能培養出專家,但是這樣出來的專家面對公眾必有種種“不適應”.我們習慣了對專家講內行話,也習慣了一篇文章只有三五讀者的小眾閱讀。而電視講述需要明白曉暢,說大白話,說人人都懂的話。然而能夠“淺出”者,必有非常“深入”之功。上電視,要對基本上甚至完全沒有背景知識的“外人”講歷史,需要相對廣博深厚的知識儲備,因此,它需要講述者在自己的狹窄專業研究領域之外,打開“面向”,廣泛關注,凡講述中所涉及之人、物、關系,都需要有深入了解,方可言之有物,才能把話說明白,講透徹。電視上看上去最輕松的侃侃而談---如果不是胡說的話,其背后必定有苦功夫在。
第三,要有永不熄滅的時代關懷。其實任何歷史研究,都是立足當代的研究,哪怕是避世者的研究,他避世的動機和理由也必定是來自“當下”的。能夠引發共鳴、打動人心的古代故事,必然有它的當代關懷。這不是歪曲歷史來將就現實,也不是庸俗的影射史學。錢乘旦先生就說,歷史學家都是有立場的,不可能存在沒有立場、徹底客觀的歷史學家。現實是從歷史中發展而來的,而我們---歷史學者是代表生活在“當下”的人回望過去,探究“所以然”的原因和過程。時代關懷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歷史,而我們的理解可以幫助今天的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唯其如此,學者才真正實現了“有為”。
第四,“專家”身份的維持問題。學者在電視上講歷史,公眾信賴其“專家”身份。這種身份來源于學者之前發表過的論文、著作,以及在專業領域內的科研、教學活動。當學者開始面向公眾講故事的時候,他的一只腳其實已經跨出了專業領域,接下來,必然面臨著“專家”身份的維持問題,換句話說,就是論著型作品的繼續生產問題。個人以為,為講故事而進行的閱讀是一種更全面的、更開放性的閱讀,它要求學者與史料進行更為密切、更無預設前提的對話。這種閱讀以及此后與非專業讀者的碰撞,都可能激發出新的想法、新的題目。
第五,經世致用,是千百年來中國學術史的優良傳統。而史學,幾千年來是強調以史為鑒,歷史家司馬遷說:“述往事,思來者。”著名的歷史家司馬光的史書之名標明“資治通鑒”,即以史為鑒,欲以益世,以歷史為鏡子。當今受眾所期望的,還是以史為鑒,即在新時期里如何學歷史、照鏡子,有益于今世和未來。宣講歷史和研究歷史一樣,創新是不竭的源泉。在新的歷史時期新的歷史條件下,要有新思路、新觀點,但要科學謹慎,在除舊布新方面,有益于世,切忌簡單而浮躁。
“百家講壇”自 2001年 7月開播,至今已歷 12寒暑,就欄目本身而言,已經創造了歷史,也曾鑄就輝煌。觀眾的口味從來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這樣一個難得的老牌歷史傳播節目,如何持續,恐怕也不僅僅是央視百家講壇一家的事情。從歷史學者的角度看,將歷史文化發揚光大,更加益世利民,“百家”的貢獻不容無視,它在那里,我們就多一個傳播歷史知識、歷史觀念的有效平臺,可以批評,更需建設。
(作者單位:余慶縣他山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