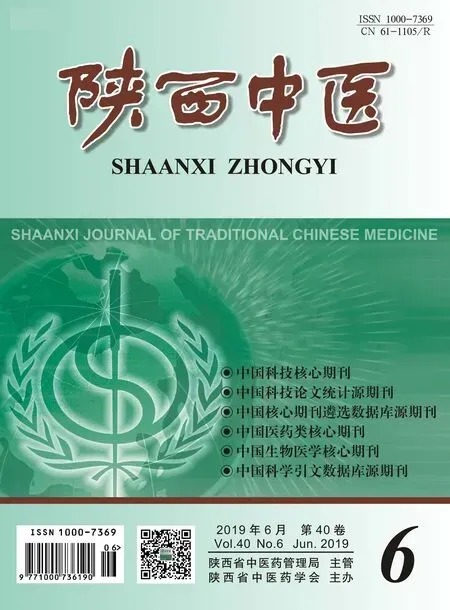增液承氣湯聯合西藥治療脾胃病療效研究*
徐艷琴,李 進,曾慶松,朱海超,王建華
1.南陽醫學高等專科學校第一附屬醫院(南陽 473000);2.河南省南陽市中心醫院(南陽 473000)
脾胃病屬祖國醫學“胃脘痛”、“呃逆”、“痞滿”、“噎隔”等范疇,可對應西醫慢性胃炎、消化性潰瘍等疾病,是消化內科常見病,其發生與不良飲食、生活習慣、心理狀態及社會環境等相關[1]。當前西醫治療脾胃病以抗幽門螺桿菌(HP)感染、抑制胃酸分泌、保護胃黏膜、改善胃動力為主,但有時療效并不盡如人意,且治療后患者存在對HP耐藥性上升、復發率高等問題[2]。中醫認為,脾虛胃熱、陰液虧耗、氣滯血瘀在脾胃病發生發展中起重要作用,治療宜健脾益氣、養陰生津、清熱導滯[3]。增液承氣湯是中醫著作《溫病條辨》中經典良方,有滋陰增液、瀉熱通便等功效,在內科、皮膚科、婦科等多學科疾病治療中均有應用,且被證實多有良效[4]。本研究將增液承氣湯聯合西醫治療脾胃病,旨在觀察其療效如何。
資料與方法
1 一般資料 研究選取本院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收治的120例脾胃病患者。按住院先后順序編號,采用奇偶數法將120例患者分為觀察組與對照組各60例。觀察組:男35例,女25例;年齡29~70歲,平均(45.16±10.54)歲;病程9個月~7年,平均(4.62±1.31)年;西醫診斷慢性胃炎42例,消化性潰瘍13例,功能性消化不良5例,合并HP感染44例。對照組:男32例,女28例;年齡25~69歲,平均(44.38±9.25)歲;病程11個月~8年,平均(4.46±1.55)年;西醫診斷慢性胃炎39例,消化性潰瘍14例,功能性消化不良7例,合并HP感染41例。兩組性別、年齡、病程、西醫診斷、是否合并HP感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有可比性。納入標準:患者符合中醫熱結、陰虧、氣滯證脾胃病[5],對應西醫慢性胃炎或消化性潰瘍或功能性消化不良診斷,年齡18~70歲,入組前1個月內無相關治療,自愿接受并配合治療、研究。排除標準:患有胃癌或其他惡性腫瘤,精神、認知異常,存在嚴重心腦血管疾病、肝腎功能不全、血液疾病、免疫系統疾病。脫落標準:服藥依從性差,中途退出。
2 治療方法
2.1 觀察組:給予飲食調整、糾正不良生活習慣、心理干預等基礎指導,進行西醫基礎治療,包括口服法莫替丁(20 mg/次,2次/d)或奧美拉唑(20 mg/次,1次/d)抑酸,枸櫞酸鉍鉀膠囊(0.3 g/次,4次/d)保護胃黏膜,有膽汁反流者,可相應給予促進膽汁排泄(熊去氧膽酸)或中和膽汁藥物(消膽胺)治療;胃動力障礙者給予促胃動力藥(多潘立酮或莫沙必利)治療;合并HP感染在質子泵抑制劑、膠體鉍劑使用基礎上,增加阿莫西林或克拉霉素治療。患者均符合陰虧氣滯證,給予自擬增液承氣湯加減治療。藥劑組成:玄參30 g,麥冬、生地各24 g,生大黃(后下)9 g,芒硝(沖服)4.5 g,當歸15 g,厚樸、半夏、香附、陳皮各10 g,甘草6 g。神疲頭暈嚴重者可加黨參、白術各10 g;腹中堅實、疼痛拒按者可加桃仁、川芎各10 g;口干、口臭嚴重者可加菊花、知母各10 g;脹滿、噯氣嚴重者可加木香、柴胡各10 g,每日1劑。和水煎煮,每次取湯汁200 ml,早晚飯后1 h服用。連續治療4周,觀察療效。
2.2 對照組:只進行基礎指導和西醫基礎治療,方法同觀察組,連續治療4周,觀察療效。
3 療效評價標準 癥狀評分標準參照《脾胃病癥狀量化標準專家共識意見(2017)》[6]中胃系癥狀標準,共19條,根據癥狀頻率、持續時間,部分癥狀評估包括程度、對生活工作影響、藥物干預,分為無、輕度、中度、重度,分別計0分、1分、2分、3分;療效根據治療后癥狀積分減少情況評定,其中癥狀積分減少≥95%為臨床控制,>70%但<95%為顯效,癥狀積分減少30%~70%為有效,癥狀積分減少<30%為無效。血液流變學指標:治療前后采集患者外周靜脈血5 ml,采用全自動血液流變分析儀檢測全血低切/高切黏度、血漿黏度、紅細胞比積。免疫功能:治療前后采集外周靜脈血5 ml,采用放射免疫γ計數器測量T細胞亞群CD4+、CD8+值(先用單克隆抗體免疫光法使CD4+、CD8+為單克隆抗體),并計算二者比值。HP清除率:治療前、治療結束后1個月,采用C14呼氣試驗檢測HP,計算HP清除率。
結 果
1 兩組治療前后癥狀積分及療效比較 治療前,觀察組癥狀積分(25.48±5.65)分與對照組的(24.87±5.42)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觀察組癥狀積分(6.12±1.47)分低于對照組的(9.54±2.33)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總有效率96.67%,高于對照組的81.67%,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 兩組治療前后血液流變學指標比較 治療后,兩組全血低切黏度、全血高切黏度、血漿黏度、紅細胞比積均較治療前降低(P<0.05),且觀察組各指標降低幅度大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例(%)]

表2 兩組治療前后血液流變學指標比較
3 兩組治療前后免疫功能比較 治療后,兩組CD4+、CD4+/CD8+均較治療前升高(P<0.05);CD8+較治療前降低,且觀察組各指標升高或降低幅度大于對照組(P<0.05)。見表3。

表3 兩組CD4+、CD8+、CD4+/CD8+比較
4 兩組HP清除率比較 觀察組44例HP合并感染者,治療后1個月,HP檢測陽性4例,HP清除率90.91%(40/44)。對照組41例HP合并感染者,治療結束后1個月,HP檢測陽性11例,HP清除率73.17%(30/41);兩組HP清除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討 論
中醫認為,脾胃同居中焦,乃人體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人體精氣血津液充足,依賴脾胃化生,脾胃不調,氣血、津液、痰濕相關病理產物也隨之而生[7]。脾胃病以脾胃運化、升降、受納、統攝功能失調為病理表現,是臨床常見病癥,中醫對其病因、病機、治療均記載頗豐,漢代張仲景《傷寒論》中有“胃家實”、“脾家虛”記載,認為其主要病機在于燥熱傷津、太陰虛寒;金元四大家之一李東垣《脾胃論》中治療脾胃病主張益氣瀉火、升清降濁,倡導“補脾胃”、“泄陰火”、“甘溫除熱”等治法;明代王綸認為“胃火旺”、“脾陰虛”在脾胃病中占重要地位;清代葉天士認為素體陰虛、外感溫熱燥邪與脾胃病發病有關[8-9];可見熱結、陰虧與脾胃病密切相關而采用清熱瀉火、滋陰增液治法古已有之。
本研究自擬增液承氣湯在原方基礎上根據患者辨證加減而來,本方劑中,玄參有滋陰清熱、瀉火解毒功效,麥冬有養陰生津、清心除煩作用,生地能清熱生津、滋陰養血,大黃可瀉實熱、破積滯、行瘀血,芒硝有瀉下、清熱、軟堅功效,當歸能補血活血、潤燥滑腸,厚樸有燥濕消痰、下氣除滿作用,半夏有燥濕化痰、降逆止嘔功效,香附有行氣解郁、調經止痛功效,陳皮能理氣健脾、燥濕化痰,甘草可清熱解毒、調和諸藥;縱觀全方,諸藥并用,共奏清熱燥濕、益氣養陰、行瘀導滯等功效,符合中醫治療熱結陰虧氣滯證脾胃病之則。現代藥理研究表明,玄參有抗菌抗炎、抗血小板聚集、增強免疫活性等作用;麥冬可提高機體免疫功能,對多種細菌有抑制作用;生地有抗炎、增加免疫功能作用;大黃可抗消化性潰瘍,促進腸蠕動,還有抗菌、抗炎、抗氧化、免疫調節作用;芒硝可促進腸蠕動,對多種細菌有抑制作用;當歸有調節免疫、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菌抗炎等作用,厚樸對多種細菌有抑制作用,其主要成分厚樸酚對實驗性胃潰瘍有防治作用;半夏可以鎮吐,香附有抗菌、抗炎、增強活血化瘀作用,陳皮能促進胃腸蠕動、抗菌、抗胃潰瘍,甘草有抗菌、抗炎、改善胃黏膜抵抗力、抑制胃酸分泌等多種功效;縱觀現代藥理,諸藥可發揮抗菌、抗炎、增強免疫、保護胃黏膜等功效,與西醫治療慢性胃炎、消化性潰瘍等原則相通。
研究表明,脾胃病患者其微循環狀態明顯異常,表現為微血流速度減慢、紅細胞聚集,血液黏度增加,而血液高凝狀態是胃黏膜細胞萎縮變性的重要因素之一[10-11]。還有研究發現,脾胃病患者細胞免疫功能較正常人降低,可表現為輔助性T細胞降低、抑制性T細胞相對增高[12]。現代醫學認為,HP感染在脾胃病病情發生、發展中占重要地位,長期HP感染會誘發癌變,清除HP應成為脾胃病重要治療目標[13]。本研究結果顯示,治療后觀察組(增液承氣湯加西藥治療)癥狀積分、療效、血液流變學指標、免疫指標、HP清除率等改善均優于對照組(西藥治療),說明增液承氣湯不僅能提高脾胃病臨床療效,減輕患者癥狀,還對改善患者血液黏度、調節免疫功能、清除HP有積極意義,與方劑中多種藥物有活血化瘀、抑制血小板聚集、增強免疫功能、抗菌、抗炎作用有關。金麗萍等[14]也發現采用中西醫結合治療胃痞病較單純西藥治療效果更好;張陽[15]采取加味黃芪建中湯聯合西藥治療脾胃病患者,發現能提高臨床療效、改善癥狀;上述研究與本研究類似。
綜上所述,增液承氣湯聯合西藥治療脾胃病患者,可以更好地緩解癥狀、提高療效,對改善患者血液黏度、增強免疫功能、提高HP清除率均有積極意義,效果較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