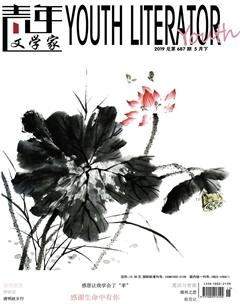敬畏生命
陳欣怡
深邃的筆觸,壓抑的色調以及那聲將群鴉驚飛成漫天烏云的槍聲,那幅《責田群鴉》無疑是梵高留給世界的警告——“敬畏生命!”
“如果生命中沒有某些無限的、深刻的、真實的東西。那么我將不再眷戀這個人間。”他向來對生命充滿敬畏,無論是那如陽冶艷,如土濃烈的向日葵還是那掩面哭泣的老工人,每個個體都在他筆下莊嚴地活出了生命的質感,梵高也以舉槍的手勢捍衛了他那顆蓬勃生光的敬畏心--舉槍,是對人生統一疆域的堅守;舉槍,是對自我意識的成功捍衛;舉槍,更是在眾的一聲聲“瘋子”中對自己生命之光輝的敬畏。
然,在現代人的精神的圖譜中,“敬畏”已然流散于指尖。狂妄之心如對自我精神鱗片無端地燃燒,在這個“欲望大得驚人的掘金時代”,征服一切的狂妄終讓現代人陷入吊詭爍爍的生存棋坪。榨干自然,豬殺動物,忽視個體的價值與尊嚴,在目空一切地占有、剝奪與漠視中,我們已然忘卻那句“敬畏生命”。
阿巴斯詩云:“對士兵來說/山頂是用來征服的地方/對那座山來說/它是下雪的地方。”對自然生命的敬畏無疑在我們的靈魂深處注入一抹不滅的詩意,當我們摒棄對自然生命的價值估量,走過的路必步步生蓮,清風自來。
君不見劉亮程“對一朵花微笑”,對生命的敬畏嵌入他的筆尖;君不聞王小波沉吟“長安城存在的理由,就是等待冬天的雪”,對生命敬畏為他唱起低回的挽歌。他們洗去自然萬物的金粉與銀飾,只求任萬物來沐浴他們充溢敬畏的目光,成為歲月大幕上的一縷不忘的魂。
敬畏生命,亦是在時代洪流中洗刷出個體的生命價值,唯有詮釋了“個”的尊嚴,我們才能在人生之境里秋水長天,在靈魂高地兀自風雅,社會也因此如鯨向海、如鳥投林,矢志不渝地走向光明。
木心先生懷揣對生命的敬畏,在獄中寫下65萬字,沒有抱怨憤怒,沒有血淚控訴,有的只是對哲學與藝術的思考,先生說:“文革以來,絕不死。”先生以內心的性靈與高蹈煥發了敬畏生命的價值光輝,這光輝終究詮釋了先生活下去的尊嚴,正因敬畏生命,先生終成“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
梵高以死維護尊嚴,本心生用活下去給以死殉道者們一個響亮的耳光,這些,終究都散著敬畏生命的光輝。
而我們眾生,并非人人都敢如此般堅守絕對自我,懷有一份敬畏——于自然,于個體,于一切生命,向所有莊嚴有活的生命致敬。
(指導老師:王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