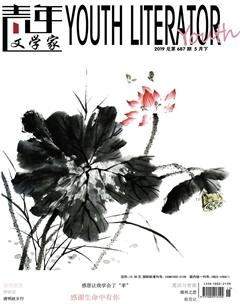拾荒記
王文紅
在我小的時候,在我的家鄉,拾荒是一道在那個年代特有的亮麗風景。
拾荒的內容很豐富,秋收后的麥穗,沒有摘干凈的豆角,埋在地里的沒有挖完的土豆……當然這是指秋后。春天呢,主要是鏟草,將大地上一切能吃的曲曲菜、苜蓿和一切牲畜吃的草全鏟了去。冬天,主要是牲畜拉在莊稼地里的糞便,一個芨芨編的筐,用半截扁擔一頭挑著筐,一頭空著搭在肩膀上,一手拿一個長把的鏟,這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有些人技術成熟,看起來順眼,有些人功夫不到,姿勢就不好,這半截扁擔一頭筐的挑法還真不好弄,我就屬于后者。
零碎的秋貨拾來供養人,綠草拾來供養豬羊,樹枝拾來用來生火,糞便拾來供養自留地,廢鐵拾來還能賣幾個錢……拾荒成了我童年、少年時期不可或缺的生存與生活方式。
拾荒也是有規矩的,比如,你就不能越過自家生產隊的地盤去拾別的生產隊地盤上的東西。有一次鄰隊的一個小伙子,就因為在我們隊的地里拾了幾泡牛糞,被我們的生產隊長派人抓了回來當眾一頓打。這樣一來,拾荒也就有了可以遵循、不成文的章法,眼看別的生產隊的地里有可拾的東西,但你不能越過地界,唯一的辦法是白天看好,晚上去拾,其實也就是去偷,十有八九晚上去,那該拾的東西早被人家拾走了。有一年中秋過后,我白天看好有幾個沒有摘干凈的玉米,決定晚上去拾,等到月亮西沉,我出發了,回來時,筐里是幾只小小的玉米棒子,可以說是我一天的口糧,母親知道我是去“拾”的,也沒有說什么,只是輕輕地哎了一聲。
一般情況下,母親是不反對我們去拾的。但那時農村生活困難,所有拾荒的人便變著法兒帶了偷的色彩。背一只芨芨筐,拿一把小鐵鏟,便是拾荒的象征,便是拾荒的樣子,光明正大地拾,見縫插針地偷,我如此,和我一塊兒拾荒的伙伴如此,大家如此,全社會如此,人們便也認可,便也不說什么,也就成了一種那個年代農村特有的潛規則。
但是我的母親還是常常告誡我盡量去拾,不要偷。拾荒的人太多,以至于拾荒成了一種生活,一種習慣,一種生存的方式,誰家不拾荒,誰家的生活就捉襟見肘,誰家的豬兒羊兒就沒草吃,誰家的地里就沒肥施,因此,拾荒便也成了一種追求甚至是一種美。不偷,拾荒的效果就出不來,光靠拾,那是遠遠不夠的,我嘴上答應,可拾起來的時候,還是要偷的。我至今都認為拾就是偷,偷即是拾。
全社會都在拾,農村的地盤是不夠的,于是,也不知是哪個高人帶頭便拾進了城里。城里有什么可拾的?我第一次跟同伴進城拾的時候就帶著這樣的疑問。在我的印象里,城里干凈,整潔,井井有條,什么東西都藏在城里人的屋子里……可是我錯了,城里拾的東西比農村還要豐富。比如,城里人的糞便,便集中在露天的茅廁里。再比如,城里廢棄的垃圾,里面的寶貝多著呢。還比如,你拾著拾著,城里人便邀請你去干一些重活粗活臟活,那時不像現在這樣要算工錢,那時興的是貨物交易,于是,城里人穿過的舊衣裳破皮鞋爛襪子等等,對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對拾荒的人來說,這都是寶啊。當然,有時正巧城里人的飯熟了,大方的人家還可以賞你一碗飯吃呢,我就吃過幾次,城里人的飯就是香!
我在城里拾荒,倒不是拾那些破衣爛衫和糞便垃圾,而是那些舊書舊報紙,而這些,偏偏又是我的同伴們忽視甚至不要的東西。久而久之,同伴們便知道我有一個愛拾舊書舊報的習慣,便把他們拾來的舊書舊報換我筐里的其他東西,有好幾次我回家的時候,筐里除了破舊的書報,別無他物,母親只是看上一眼,什么也不說。也正是這些破舊的書報,成就了我以后在語言文字上的優勢。
最有意思的是,上學去的時候,用來拾荒的筐里就放著書包,進校門的時候,把筐和鐵鏟一放,誰是誰的位置,一排排,放的也很整齊。下課了,誰拿誰的,不亂不搶不爭。回家的時候,筐里便有了東西,有時我們還要比一下誰拾的東西多,東西好,假如誰拾了滿滿一筐糞便,我們也根本不覺得臟,不覺得臭,臉上流出來的是羨慕和嫉妒。
我上初一那年,新來的校長見校門口一排排的筐又臟又臭,很不雅觀,就下令再不準在校門口放置這些臟不拉幾的東西,結果,第二天,這些一邊上學一邊拾荒的學生都不來上課了,校長無奈,只好在學校后邊的空地上專門騰出一塊地來,這才將準備專門拾荒而不去學堂的學生拉了回來。
八十年代的時候,拾荒的越來越少,到了現在,在農村拾荒的幾乎絕跡了。去年,我去外縣一個極其偏遠的村子工作,忽見一老翁肩挑芨芨筐,手拿鐵鏟在拾垃圾,一下子就勾起了我的拾荒思緒。我問大爺,為什么要拾荒,大爺回答我說,悶得慌,用來消遣。還是他的老伴說了實話,什么悶得慌,他這大半輩子就是靠拾荒生活過來的,他現在拾,純粹是在回憶和享受過去的生活……
奧,我明白了,拾荒是一種生活更是一種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