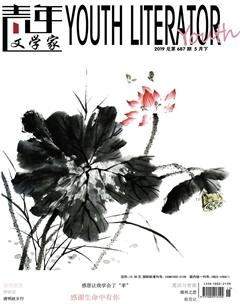香
陳馨竹
屋里的四季蘭悄悄地開花了。
花香淡淡的,好像很遙遠。
兒子推開門,一陣帶有泥土味的穿堂風驟然吹進屋里。
啪。
門關上了。
啪。
兒子書房的門也關上了。
坐在沙發上的父親,咽回喉嚨中正要發聲的字眼,合上了張開的嘴巴。
他推了推厚厚的眼鏡,把身子縮回柔軟的靠背上。
他皺皺鼻子。
“奇怪。哪兒來的香味兒。”
他再仔細聞時,那香味兒又沒了。
時鐘滴滴答答地跑著。
打盹兒的老貓吸了吸鼻子,樓上的小胖子在滾皮球。
屋里靜止著,靜止了好久。
媽媽回來了。
她風風火火地在屋里走動,時鐘的滴答聲才走一下,衣服已經在洗衣機里擠壓著擁抱在一起。
廚房里傳來叮叮咣咣剁肉的聲音,接著是油炸的滋滋聲。
“開飯了,開飯了!別讓我說第二遍!”
兒子推開門,慢慢地挪過來。
父親從沙發上慢慢站起來,伸伸腿,向餐廳走來。
嗒。嗒。一樣懶懶的腳步,一個輕些,一個重些。
接著是嚼菜的聲音,攪湯的聲音。
餐桌上一片沉默。
兒子開口想說點什么。
他不知道說什么。
父親開口想說點什么。
他不知道說點什么。
看,無聊的意義的在此刻顯現出來了,無聊比沉默要活潑。
兒子剛想說說球賽的事兒——他是球隊的骨干,今天又贏了一場比賽。
但父親不知道。
父親的手機突然鈴聲大作。
“喂?……哦……行吧……成……我就過去。”
父親看了看他的妻子和兒子,說:“公司的賬表出岔子了,大家都等我過去呢。”
邊說他邊快步走向衣架,披上大衣,抓起公文包。
父親關上門。
兒子咽回喉嚨中正要發聲的字眼,合上了張開的嘴巴。
吃完飯,兒子回房間寫作業。
奇怪。兒子皺皺鼻子。
“奇怪。哪兒來的香味兒。”
他再仔細聞時,那香味兒又沒了。
他暗想,真奇怪,不是四季蘭的香味兒。
父親合上電腦。
已經深夜十二點了,但這片商業金融區的高樓大廈里卻都是燈盞齊明。
他揉揉酸痛的眼睛,嘀咕道,這眼睛今年估計又得漲度數了,都是這該死的公司鬧的。
他想,就是這樣,兒子還是不知道自己的辛苦。真盼望他出息一點兒。
不過兒子至少踢得一腳好球,父親有些欣慰。今天他匆忙趕去去看兒子的比賽,真帶勁兒。不過可惜,中場就又被公司的手下急召回去開會了,沒來得及跟兒子說個話。
得提醒他注意別扭到膝蓋骨,不知道自己那玩意兒好不好用。
身邊的小王打斷了他的思緒,“總兒,眼睛又累了吧,把我這盆小四季蘭送您,明目的,又香。”
父親道聲謝,接過來。
那株小小的四季蘭散發出熟悉的淡淡的香味兒。
第二天,父親和兒子腳前腳后回到家,媽媽在做家務。
正當父親走向柔軟的沙發,兒子走向他的房間時,媽媽突然嘀咕一句:“今兒個打掃屋子時,客廳里不知道哪兒多出盆四季蘭。兒子桌子上還有個活筋膏,也不知道哪兒冒出來的,一聞,嘿,都挺香。”
父親停下他走向沙發的腳步。
兒子停下走向房間的腳步。
他們先是張張嘴,又咽回喉嚨中正要發聲的字眼,合上了張開的嘴巴。
四季蘭的花香還是淡淡的。
但這次聞得清楚了——那花香好像隔的那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