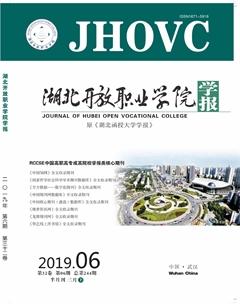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對萊辛《野草在唱歌》譯本的啟示
王婷婷 侯書華
[摘要]20世紀80年代的翻譯研究領域,翻譯活動已由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發展為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本文從全新角度把女性性別結合后殖民的社會背景,用女性主義翻譯視角對王蕾和一蕾的翻譯文本從語言和心理角度都進行了對比,探討男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性別差異所體現出不同的翻譯角度,同時也有助于中國讀者對萊辛作品閱讀品鑒和理解。
[關鍵詞]多麗絲·萊辛;女性主義翻譯理論;《野草在唱歌》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9)06-0153-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9.06.068 [本刊網址]http://www.hbxb.net
一、研究背景
多麗絲·萊辛這名多產的英國女作家,國內對萊辛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1981-1992和1992-2010。其中小說(長篇10部,短篇70多篇),戲劇2部,詩歌1本,若干論文集和回憶錄,如“The Grass is Singing”(1950),“Children of Vio-lence Series”(1952-1969),“The Marriages Between ZonesThree,Four and Five”(1980),“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1971)。萊辛被譽為繼弗吉尼亞·伍爾芙之后唯一獲得諾貝爾作家的女性,其作品風格類型大致可以分為四類:(1)黑人追求自由平等的社會、民族斗爭和政治問題;(2)指出了現代婦女面臨的困境并給她們指明了解放道路,如膾炙人口的作品"TheGolden Notebook”(1962);(3)用寓言和幻想形式來展示人類所面臨的危機和借此預言未來的世界,他的代表作“Memoirs of aSurvivor”(1974),特別關注個人身份的認定和人的結合甚至人類的命;(4)萊辛回到現實主義敘事風格,如“The Fifth Child”(1988)。
早在20世紀50年代,其作品被各國譯者和文學愛好者爭相翻譯,如陳才宇和劉新民翻譯了The Golden Notebook(1962),韓剛和韓少功翻譯“Five Short Novels”(1963),范文美翻譯的“A Man and Two Woman”(1963),彭倩文翻譯的“Partic-ularly Cat”(1967),朱子儀翻譯了“Memoirs of a Survivor”(1974),王容譯的“The Good Terrorist”(1985),朱鳳余“Walkingin the Shade”(1997)。
國內萊辛小說研究主要采用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心理分析等理論視角探討萊辛的藝術創作形式以及她的殖民主義立場。本文以《野草在唱歌》(“The Grass is Singing”)為例,從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視角來梳理和回顧中國譯者對萊辛的作品及相關策略的運用。隨著2007年萊辛諾貝爾文學獎的頒布,國內外研究學者才重新開始對其作品進行研究,但是大多數學者的研究目前只停留在殖民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等層面。對女性主義翻譯視角研究甚少,因此本文作者從西蒙的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指導下對比了《野草在唱歌》的中英文譯本。這部小說展現了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南部非洲的殖民現實,生動形象地反映了白人殖民統治下殖民地黑人生活的艱辛。作者從三個方面對小說進行了全面的分析:(1)通過對原文和譯文中的對話和敘事特征的對比,還原了小說中人物性格;(2)作者再用男女譯者翻譯版本進行對比,得出相應結論男權角度的用詞都是對女主人翁的批判,用否定的消極的詞匯來描寫瑪麗悲慘的處境,而女性角度翻譯更多的對瑪麗的同情,對于很多帶有性別歧視的詞語進行了修改、增加或刪除;(3)關于翻譯策略,作者結合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對小說中的詞匯、句子進行原語和譯語的對比,按照男女譯者不同的翻譯習慣采用了不同的翻譯方法,目的都是為了使譯文更富有譯者自己的風格。
二、研究內容分析
Sherry Simon的重要譯學專著“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1996),是全球第一本從女性主義視角就翻譯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的著作。這也是首次系統討論翻譯種的女性性別政治。本文著重討論女性主義運動作為一種政治和文學運動給翻譯理論和實踐帶來的影響。翻譯不僅僅是傳統方式的機械語言轉換,而是通過文本和語篇間符號不斷的轉換來發展和延續跨文化交際活動。只有在特定的歷史,文化、社會等問題背景下,排除意識形態、社會文化環境和譯文讀者對譯者主體性的制約,翻譯是不斷強調譯者創作主體的改寫行為。持女性主義知識結構的譯者通過語言與翻譯的關系,尋找兩種關于性別的文化交流方式,后天建構翻譯過程并大膽的重讀、改寫、重寫女性的歷史。翻譯完全以一項國際性的政治活動視角來審視多麗絲·萊辛的處女作《野草在歌唱》,譯者將萊辛的這部作品中圍繞瑪麗這一角色追求自由的主題而展開,瑪麗生活在男權社會惡劣的生存環境中,從她開始決定接受世俗的婚姻開始,她悲劇的一生已埋下了伏筆,無論是婚后的生活還是面對黑人摩西的曖昧關系,瑪麗都缺乏主動的思考。從未真正理解過她一直追求向往的自由的含義到底是什么?瑪麗始終被動地接受命運的安排,雖然為此做出過抗爭最終卻難逃悲慘結局,本文站在譯者角度結合女性主義角度來解讀了這部小說,并指出了女性在殖民主義制度下追求實現自我價值的主題。
《野草在歌唱》的創作基于非洲殖民地南非,在這片廣袤的國度由高到低把人根據種族和階級等級可以分為三類:英國白人,生活在南非的白人和土著黑人。小說《野草在唱歌》中的主人翁瑪麗恰好就是生活在南非處在中間階層的白人,瑪麗為了建構自己的身份地位,被迫嫁到鄉下當起了奴隸主。可現實卻也無法確立起她在父權社會的真正地位,黑人奴摩西雖然能給瑪麗的生活帶來一絲光明,他們卻還是無法越過種族階級這層障礙。瑪麗始終徘徊在外部父權社會與內部自身無意識的種族歧視之間,內外矛盾無法妥協最終造成了瑪麗的心理走向畸形,這恰恰反映了殖民文化帶來的悲慘結局。萊辛選擇用白人瑪麗的悲劇來描述白人殖民給黑人所帶來的種族壓迫和產生種族沖突,該文以犀利的筆鋒對女主瑪麗進行細膩的人物刻畫,賦予她悲劇色彩的命運描寫,從而真實剖析了殖民下統治對不同種族、不同階層之間種族意識,深刻地揭示了最終造成瑪麗悲慘結局的社會根源。為讀者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南非殖民統治下的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的場景,使讀者身臨其境地感受到了生存在種族主義以及父權社會下背景下白人女性難以言表地痛苦和無奈,也展現了被白人文化扭曲了的黑人人性,并借此諷刺了白人殖民下的殖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