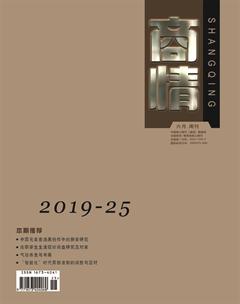“智能化”時代勞動法制的調整與應對
歐春江 周高云 陳玲玲

[摘要]“智能化”時代不僅對勞動力市場造成重大沖擊,而且給傳統勞動關系帶來新的挑戰:實踐中用工關系的性質難以確認、新型“勞動者”的實體權利難以保障、僵化保守的維權渠道難以滿足社會需要。本文在分析現實困境的基礎上,借鑒他國勞動法制經驗進行反思,對我國勞動法制的調整與應對制定出綜合系統性的對策,以期助推共享經濟的長遠發展和國家“智能化”的戰略方向。
[關鍵詞]“智能化”時代 勞動關系 勞動法制
在以網絡、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為核心的現代信息技術推動下,人類社會正藉由“智能革命”而步入以智能科技、數字經濟、信息社會為表征的“智能化”時代。自從1999年提出“物聯網”概念以來,2006年《紐約時代》宣稱“智能時代”已到來,而2017年被認為是中國的“人工智能元年”。國家對于“人工智能”的未來目標與政策扶持,昭示著我國已步入“智能化”時代的春天:
但不容忽視的是,“智能化”時代以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智能化方案將會使傳統的勞動關系遭受巨大沖擊,使現有的勞動法制面臨深遠的新問題。本文正是基于此進行深入思考,其意義不僅賦予諸多新型“勞動者”以“基本權利保護網”,更期待于創新產業用工規范化的基礎上進而助推國家智能化、多元化發展的戰略方向。
一、“智能化”時代對勞動力市場的沖擊
隨著“智能化”時代的到來,勞動力行業和勞動力類型由單一化轉變為多元化、勞動力需求從“量的需求”轉向“質的需求”,同時勞動硬性條件更為復雜化、勞動力短期化頻率增強。勞動力市場在持續更新與加速碰撞中,正發生和經歷著重大的格局變化:
1、共享經濟市場規模擴大,引發勞動群體多元化。“智能化”戰略的大背景下,2017年我國共享經濟市場規模約為52850億元,增長率為43.81%。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約為49205億元,同比增長25.7%。“智能化”亦促發新型勞動群體,參加共享經濟的人數比上年增添1億人,整體人數已超過6億人,依靠分享經濟平臺就業人數接近600萬人。不難發現,共享經濟市場規模的擴大帶來新的就業機遇,引發勞動力格局的變動,也必須導致勞動群體的多元化。
2、“智能化”替代性的成本優勢,促發勞動力結構傾斜。以“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為主要技術流的“智能化”時代,人工智能將逐步替代人的“體力勞動”“腦力勞動”及“智力勞動”,其典型的專家系統、知識工程所帶來的創新效應對個人思維器官的替代已逐漸成為可能。人工智能的函數化遞增帶來行業與產業的變化:一些行業將被淘汰,新的產業應運而生。人工智能技術已能替代眾多工種,導致現有的勞動力結構已然發生傾斜,甚至可能迫使并加劇勞動力市場的割裂狀態。
3、傳統勞動者不適應性突顯,催發職業轉移典型化。“智能化”時代的大背景下,低層次就業被取代,諸如高級數據分析師等新興崗位出現并“走紅”驅使勞動者向更高級的、更適合于發揮創造能力的職業轉移,這必然要求勞動者具有更高的技術水平和文化水平、較強的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無疑,傳統的勞動者還不足以適應數據性、智能性的大數據和云計算等科技環境,其單一的知識體系和技能結構,已無法滿足“智能化”時代的實際需求。
4、企業與勞動者信息更對稱,主體地位更平等。“智能化”的推進為傳統行業的營銷經營提供更多選擇,線上與線下的協同,企業不僅僅能為勞動者提供精準、個性化的服務,也提供信息平臺。這種來自互聯網的開放性、包容性,使得工作關系的雙方主體地位更加平等并且自由。
二、“智能化”時代,傳統勞動關系遭遇新的挑戰
(一)法律實踐中用工關系的性質難以確認
1.用工雙方的靈活性,是否影響用工關系的性質?
2018年9月7日的“閃送app案”中,李相國與北京同城必應科技有限公司發生勞動爭議。閃送員李先生因其在提供閃送服務時遭遇交通事故,請求享受工傷保險,同時還要求確認雙方存在勞動關系。該案中重要的事實要素包括:李某可自主決定是否接單、決定交通工具,不必考勤;同城必應科技有限公司不限定其工作所在、工作時間、工作量,也不提供勞動工具。此案中李某與公司間靈活的用工形式,正是“智能化”產業模式介入傳統勞動關系后所呈現出的新的工作崗位的特征。
后經北京海淀區人民法院判決,確認李相國與北京同城必應科技有限公司間存在勞動關系。法院認為,雙方關系的靈活性的特征,并不影響其勞動關系的形成。但法院也同時認為:此案勞動關系的認定,并不能保證其他類似案件也同時確認為勞動關系。該案代表性的說明了:在“智能化”時代的用工模式下,用工者與互聯網平臺間能否成立勞動關系的新型糾紛,值得探求。
2.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是否影響用工關系的性質?
“閃送app案”中法院確認勞動關系,其重要的一點原因就是對李相國使用勞動法保護之必要性。該案中李相國只能獲得初次手術的費用理賠,其后續兩次手術費用無法支付,且治療期間的工資等待遇無法得到保障,顯然救濟嚴重不足。法院認為:同城必應科技公司從李相國給予的勞動中獲利,則應當負擔起相應的法律責任及“企業之社會責任”。若默許其低成本用工,則必然缺乏防范用工風險之主動性,對尋求勞動安全保護措施的積極性不高,因此帶來社會問題必定增多。互聯網企業不能因其采用了新的技術手段與新的經營方式而不承擔本應由其承擔的法律責任與社會責任。可見,正是基于“企業社會責任”法院才確認了李相國與同城必應科技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問題是,如果不是因為本案工傷案件的特殊性,或是勞動者面臨人身傷害的極端情節,企業的社會責任承擔是否能決定勞動關系的成立?
3.法律實踐中或回避模糊處理,或裁決各異
“智能化”產業模式,導致用工關系的判定非常復雜。法律實踐中類似爭議更多是通過調解處理的,其中對新型用工關系往往是回避性的模糊處理。這是因為在沒有法律明確規定或最高院對此未做出司法解釋的情況下,法院很難確定雙方間的用工關系性質。如:年北京朝陽區勞動仲裁委員會關于某廚師到家APP企業平臺和從業者勞動爭議,通過調解,企業補償給從業者部分款項而結案,并未對雙方是否存在勞動關系進行認定,采取了回避模糊處理的做法。而在2013年“北京孫某訴億心宜行公司案”、“上海代駕員訴億心宜行公司案”中,法官裁決分別為:明確判定不存在勞動關系,以及僅認定是雇傭關系。回避模糊處理或是裁決不統一的結果會造成更多的社會矛盾,譬如直接影響勞動者的權利與義務、造成提供服務者人心不穩乃至直接影響司法的公信力與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