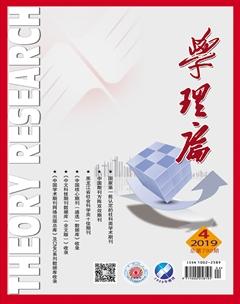明末佛教之世俗化轉向及意義
盧忠帥 杜希英


摘 要:明末佛教之世俗化轉向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僧人關注政治及民生社會,二是佛教日益深入民間,與老百姓關系密切。明代后期,佛教世俗化轉向明顯,這與佛門內部僧伽制度的變革和明政府倡導的諸宗融合政策有關。明末之佛教世俗化轉向,對當今中國佛教的發展具有借鑒價值。
關鍵詞:明末;佛教世俗化;原因;當代價值
中圖分類號:B248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19)04-0055-02
佛教的世俗化是指它日益關心此岸的人間世俗生活,而不再專注于彼岸佛的世界。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我國內地,其世俗化即已開始,至明末,這種世俗化更是加速進行。梳理明末佛教世俗化轉向的表現,并深入分析其原因,具有一定的現實借鑒意義。
一、明末佛教世俗化轉向的表現
1.“四大高僧”關注政治及民生社會。云棲■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被稱為明末“四大高僧”。他們積極踐行大乘菩薩道精神,關注政治及民生社會,掀起復興晚明佛教的浪潮。從另一個角度講,這正是明末佛教世俗化轉向加速的表現。
首先,“四大高僧”關注政治,與官府聯系廣泛。■宏雖對僧人結交官場頗有微詞,但他并未與官場絕緣。時任南京禮部尚書的沈三洲曾在南京瓦官寺救過■宏的命,此后二人交往甚密。“四大高僧”中與官府關系最為密切者,當屬德清。為振興佛教,德清廣交權貴,上至皇太后、中央各級官僚,下至各級地方官吏。他認為:“沙門所作一切佛事,無非為國祝厘,陰翊皇度。”[1]46因此,萬歷九年(1581),當得知李太后欲建祈儲道場于五臺山時,德清馬上將其正在籌劃的《華嚴經》無遮法會轉為祈儲無遮法會,以回應李太后所建祈儲道場。德清此舉,雖贏得李太后歡心,但也因此構怨于神宗,被發配充軍廣東雷州。在雷州,德清并未中斷與官府的聯系,相反,他借用官僚和太監們的力量,復興曹溪祖庭,使之“一歲之間,百廢俱舉”[1]79。德清只是因為結交權貴被流放,而另一高僧真可卻因此丟掉性命。萬歷二十年(1592)后,隨著“三大征”的進行,國庫困竭,為了斂財,神宗派遣宦官為礦監稅使,四處搜刮,為害一方。萬歷二十八年,神宗派太監李道到南康催繳礦稅,太守吳寶秀因拒不奉命而被劾入獄,其妻哀憤投繯而死。真可得知后,義憤填膺,親赴京師營救。到達北京后,真可奔波于達官權宦之間,并向李太后痛陳礦監稅使之害,經多方營救,最終使吳寶秀獲釋。然而,真可的行為遭到一些宦官的嫉恨,最終在“妖書案”中被誣陷入獄,不久坐化獄中。而智旭的儒釋融通思想,則是他積極參與現實政治的精神之源。
其次,“四大高僧”關注民生社會,積極救護百姓。隆慶五年(1571),■宏至杭州云棲時,恰逢當地虎患嚴重,每年死于虎口者數十人。■宏分析到,虎傷人主要是因饑餓所致,只要給它們足夠的食物,自然也就不再傷人。村民們照做后,果然“虎患遂寧”。上述真可因營救吳寶秀、反對礦監稅使獲罪而死,既是其結交權貴的表現,也是其關注民生社會、救護百姓的表現。“四大高僧”中關注民生社會最具代表性者,當屬德清。萬歷十二年(1584),山東發生災荒,隱居嶗山的德清矯詔將李太后賜予修建庵居的三千金散施于災民,得到李太后與神宗的肯定。萬歷二十一年(1593),山東再次發生災荒,死者載道,德清將海印寺中儲存的所有齋糧分賑近山之民,但仍然不足,他又拿出寺中錢財親自乘船到遼寧買回大豆,救濟附近山民,“由是邊山四社之民,無一饑死者”[2]570。在充軍雷州的路上,德清見道路崎嶇不平,行人走的艱難,于是囑咐他的隨行者修道路、建茶庵,以方便行人。抵達雷州后,正逢當地大旱,瘟疫肆虐,死者的骸骨遍布城內城外。德清見此景象,雖然旅途勞累,但他立即勸說群眾收拾、埋掩尸骨,并為死者建普濟道場超度七晝夜。在雷州充軍期間,德清見廣東采使李敬信佛,于是利用這一契機說服他約束采珠船,以拯救當地百姓。智旭也利用一切時機,勸說世人積德行善,并發以己身代眾受苦的大愿:“所有一切惡業,應受報者,智旭悉皆代受,令得解脫;所有一切善業,應受報者,普施法界眾生,同成正覺。”[3]8-9應該說,這是對社會民生更深層意義上的關注。
2.“四大名山”成為信眾朝拜的主要圣地。山西五臺山、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和安徽九華山并稱中國佛教“四大名山”。明末,佛教與民間信仰和民俗節日進一步融合, “四大名山”成為信眾朝拜的主要圣地,這正是明末佛教世俗化轉向的最好例證。
首先,“四大名山”成為信眾朝拜的主要圣地。明末五臺山香火旺盛,朝山進香者“四海云涌”,而列宰名臣也“屢有思真之詠”[4]。峨眉山佛教在明末達到鼎盛時期,“四方緇白朝禮者無虛日。乃其盤道曲折險峭,登涉艱難。雖大士神力,善士之信力,往返上下,頓忘其苦”[5]。明代中后期,普陀山佛教空前發展,佛事十分旺盛,朝山進香者超過了五臺山和峨眉山,“上自帝后妃主、王侯宰官,下逮緇侶羽流、善信男女,遠近累累,亡不函經捧香,博顙繭足,梯山航海,云合電奔,來朝大士,方之峨眉、五臺有加焉”[6]。明末的九華山佛教發展十分迅速,香客“或南自浙江、徽郡,北自山、陜遠來”,“日牽連如蟻而下,每隊不下數十人,無冬無春,摩肩不絕于道”[7]583-584,“歲不下十萬人,佛號連天,哀求冥福”[8]。
其次,“四大名山”僧人從事商業活動。隨著“四大名山”香客、游人的增加,為之服務的設施如店鋪、廟棧等也相繼興建并日趨完善,僧人經商者不在少數。這其中,尤以九華山最具代表性。由于地藏信仰的內容深契中國傳統文化最基本的人文精神,所以九華山成為佛教名山的時間雖晚于其他三座名山,但在明末的發展速度卻是最快的,最能代表明末佛教世俗化轉向的特點。隨著香客、游人的增加,九華山商業逐漸繁榮起來,僧人也參與經商,“山門經商遠集,珍品畢致,肴食甲于官府;凡城市所無,常從僧人售得之”。官府雖明文禁約,但卻禁而不止。香客、游人的增加,勢必促進廟棧的增多。至明萬歷年間,九華山專事接待香客游人的廟棧,僅化城寺東、西兩序就有百余間,“高棟層樓,邃戶曲房,明窗凈牖,雕欄畫檻,爭極宏麗,以招邀四方香客”。除化城寺僧房以外,分布全山各處的僧房亦不下百間。通過開設廟棧,寺院收取香客游人的食宿費,“每歲所獲不下萬金”。為了獲取更多利益,寺院僧眾總是想盡辦法爭取客源,特別是地藏法會期間,香客云集,僧人們忙于接待,“各攜茶酒下山,中途邀迎。其至舍也,張筵唱戲以待”[7]584。
二、明末佛教世俗化轉向的原因
1.佛門內部僧伽制度的變革。針對明初寺廟混亂的狀況和民間顯密法事盛行的現實,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下令分天下寺院為禪、講、教三類,僧人也相應分為禪、講、教三類,并要求他們各務本業,“其禪不立文字,必見性者,方是本宗;講者務明諸經旨義;教者演佛利濟之法,消一切見造之業,滌死者宿作之愆,以訓世人”[9]58-59。僧伽團體分工的細化,使得關于佛教義理的研究大為減少。特別是將從事世俗法事的教僧獨立成類后,世人基于孝敬之心,多邀請教僧為其先人度亡,加之法事的商品化,教僧有可靠的經濟收入,致使佛教內部出現了向教僧傾斜的趨勢,“甚至連本應從事禪修、研究經綸的禪、講僧,欲分沾經懺之利者亦大有人在”[10]282。教僧團體的興盛,使得明末佛教趨向“死人佛教”“經懺佛教”,故以關注人死后事宜著稱的九華山佛教,在明末“四大名山”中發展速度最快。同時,這也是明末“四大高僧”掀起復興佛教浪潮的原因。
2.明政府倡導的諸宗融合政策。明初,太祖詔令講僧專門講習《心經》《金剛經》《楞伽經》三經,但這些并非各宗派的根本經典,于是講僧“多以融合諸宗學說為特色,專弘某一派或某一經的人極少”[11]277。政府的這種變革要求,加速了禪宗與其他流派、特別是凈土宗的融合,故永樂以后,“念佛之法門風靡天下,禪師之兼凈業者多”,并“形成一代風潮”[12]734。凈土宗簡便易行的特點,也促進了佛教在民間的傳播,使得社會上的佛教信仰氣氛濃厚,正如明末文人謝肇■所說:“今之釋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宮,盛于黌舍,唪誦咒唄,囂于弦歌。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婦人女子,每讀禪拜佛,無不灑然色喜矣。”[13]227明末佛教“四大名山”格局的形成,正是佛教在民間廣泛傳播的具體體現。
三、明末佛教世俗化轉向及意義
1.為當今中國佛教的發展提供借鑒。任何宗教的創立,不管其營造出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如何,但終究是為了“解決”現實世界的人的需求和關切。佛教世俗化,為民眾提供宗教服務,滿足他們的宗教需求和關切,應是佛教創立的根本宗旨。沒有世俗化,佛教很難獲得更多民眾信仰,從而獲得發展,其神圣性勢必難以持久。
2.給當代人以精神的撫慰和心靈的超越。當代社會,人們生活節奏加快,競爭壓力大,精神容易焦慮,內心容易痛苦,心理疾病也隨之而來。另外,由于長期忙碌,人們接受的文化潤澤不夠,導致心靈的枯萎和荒蕪,易迷失自我。所有這些,都極大影響了人們的生活質量。佛教一定程度上能給人以精神的撫慰和心靈的超越。隨著世俗化,佛教走進人們的生活,對疏解人們的煩惱心情、減輕人們的思想壓力具有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釋福征.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M].上海:國光印書局,1934.
[2]憨山德清.憨山老人夢游集[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3]■益智旭.靈峰宗論[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4]釋鎮澄纂修、釋印光增修.清涼山志·鎮澄序[M].中華大藏經續編(漢文部分)本.
[5]釋印光.峨眉山志·峨山修改盤路記[M].中國佛寺史志匯刊本.
[6]許琰.普陀山志·補陀洛迦山記[M].續修四庫全書本.
[7]光緒青陽縣志·九華山供應議,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8]吳文梓.建東巖佛典碑記,載光緒九華山志·雜記[M].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9]葛寅亮.金陵梵剎志·欽錄集[M].何孝榮,點校.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
[10]陳玉女.明代的佛教與社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1]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12]忽滑谷快天.中國禪學思想史[M].朱謙之,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謝肇■.五雜俎[M].北京:中華書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