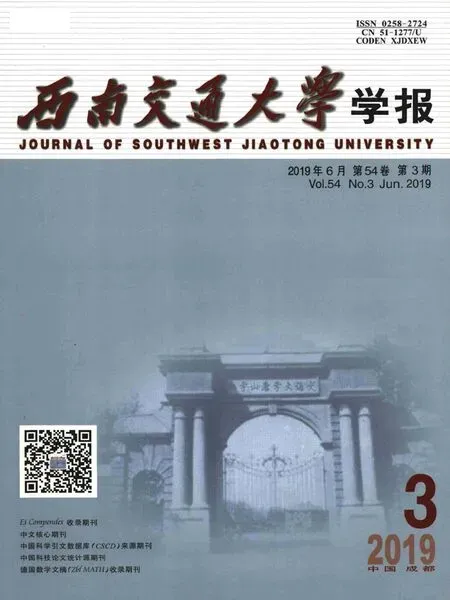深切峽谷橋址區高空風特性現場實測研究
張明金 ,李永樂 ,余傳錦 ,吳聯活
(西南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院,四川 成都 610031)
山區風是我國西部橋梁工程設計論證中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山區的風特性參數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橋梁工程的造價,又嚴重影響著工程結構的安全性.現代超大跨度橋梁和柔性結構的抗風研究除了關注平均風速外,通常脈動風引起的結構抖振和渦振等效應更引起工程領域的高度重視.因此,山區高空風特性是進行山區橋梁工程抗風研究的基礎.
目前針對深切峽谷地形地貌區風場特性的研究主要有:理論推導、數值模擬、模型實驗及現場觀測等方法.其中:理論推導是對復雜地形進行一定的簡化,建立空氣運動方程和熱傳導方程,通過求解微分方程組得到相關的風場特征[1],數值模擬通常是以理論推導公式為基礎,借助計算機求解的一種分析方法[2],無論是理論推導還是數值模擬均采用了一系列的假定邊界和計算模型,而這樣的簡化會導致一定程度的失真[3].模型實驗是借助風洞實驗室,對關心的地形地貌進行模擬實驗,但實驗室中的風場模擬也具有一定的挑戰性.因此,現場觀測是目前比較有效也是采用較多的一種研究手段.宋麗莉、朱樂東、韓艷、劉明、李永樂、黃國慶、何旭輝等[4-13]通過在山區橋位處建立風觀測站,對復雜山區地形中的風場特性進行了實測.譚波、李永樂等[14-15]發現在西部高海拔高溫差山區每天下午均會出現規律性波動的大風,部分地區風速可以達到10 m/s,但相關文獻中亦沒有對這種風場的風特性進行討論.截至目前,業界對山區橋梁橋址區風特性的認識還未達成統一的認識,特別是高空的風特性現場實測報道還較為少見.本文以龍江特大橋為工程背景,對橋址區高空的風特性進行現場實測與分析.
1 觀測概況
龍江大橋是保騰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大橋為主跨1 196 m 單跨懸索橋,錨跨為320 m,跨徑組合為320 m + 1 196 m + 320 m,龍江大橋橋型布置如圖1所示.大橋的橋塔采用混凝土組合圓形截面,橋塔橫梁采用箱形梁截面,保山岸索塔(東塔)與騰沖岸索塔(西塔)的高度分別為178.7 m 與137.7 m.大橋設計線距離河谷底大約為285 m,河谷呈“V”型,橋址區地形地貌復雜,風環境惡劣,加之該橋跨度大、橋塔高,結構較為柔性,對風的作用非常敏感.

圖1 龍江大橋橋型布置(單位:m)Fig.1 Arrangement of Longjiang Bridge (unit:m)
在大橋貓道跨中位置處布置了三維脈動風觀測點,觀測點離地高為295 m.該觀測點從2015年7月開始采集數據,對大橋加勁梁吊裝過程中的脈動風數據進行了實測.本文以10 min 平均風速大于3.4 m/s(陣風風速達到4 級大風的標準)為基本條件對原始數據進行篩選,共篩選出7 899 條有效的風速時程數據,圖2為三維脈動風傳感器現場照片.

圖2 現場實測照片Fig.2 Field measurement photos
2 風特性分析
2.1 平均風速、風向及風攻角
貓道上跨中處典型大風天3 個方向上(U1為南北方向,U2為東西方向,U3為豎向)的風速時程見圖3,從圖3中可以看出,橋位處從凌晨一直到中午12:00 風速均較小,中午12:00 以后風速開始逐漸增大,最大風速在8.0 m/s 附近波動,大風一直持續到晚上18:00 左右.橋址區大風的起風規律與文獻[13]和文獻[14]中的報道較為一致.

圖3 風速原始數據(2015-07-14)Fig.3 Raw wind data (2015-07-14)
貓道上跨中處的平均風速、風向及風攻角的分布規律如圖4所示.

圖4 風速、風向及風攻角Fig.4 Wind velocity,direction and attack angle
從圖4(a)中可以看出,橋位跨中處的風向以沿河道方向西南風為主導,其它方向上出現大風的概率相對較小,這是由于深切峽谷地區風場受到兩側山體的影響較為明顯.圖4(b)為風攻角和風速的聯合分布,從圖中可以看出,跨中處隨著風速的增加風攻角的分布范圍明顯減小,風速越低時風攻角的分布范圍也越廣,但絕大部分風攻角均在-10°~10° 之間.圖4(c)為風攻角的概率分布,從圖中可以看出,風攻角的概率統計均值為 -1.4°,標準差為3.9°,在95%保證率的情況下,風攻角的分布范圍為-9.0°~6.2°.
2.2 紊流強度
圖5為順風向(u)、橫風向(v)及豎向(w)紊流度隨風速的變化情況.從圖中可以看出:風速較低時3 個方向上的紊流度均較大,隨著風速的增加紊流度明顯減小;風速在10.0 m/s 時3 個方向上的紊流度分別為9.0%、8.6%、8.5%,它們的比值為1.00∶0.96∶0.89;高風速時(風速大于8 m/s)3 個方向上紊流度的變化不再明顯,橫風向紊流度和豎向紊流度均較規范推薦的比值1.00∶0.88∶0.50 要大.

圖5 紊流度Fig.5 Turbulence scale
2.3 紊流積分尺度
對貓道上跨中處的紊流積分尺度進行統計,如圖6所示,從圖中可以看出:順風向紊流積分尺度均值為284.6 m,標準差為198.1;橫風向紊流積分尺度均值為223.6 m,標準差為130.5;豎向紊流積分尺度均值為240.3 m,標準差為150.6.紊流積分尺度均值比規范推薦值要大.3 個方向上的比值為1.00∶0.79∶0.84,這表明在觀測點處3 個方向上漩渦的尺度是基本相當的.由于跨中處的觀測點離地高達到了295.0 m,離兩岸山體的距離也均大于600 m,觀測點處受到地表山體的影響有所減弱,因此紊流積分尺度明顯變大.

圖6 紊流積分尺度概率分布Fig.6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turbulence integral
2.4 功率譜
貓道上跨中處典型大風天功率譜(2015年7月6日)如圖7所示,從圖中可看出,該段風速時程在順風向和橫風向上的功率譜與Simiu 譜有所不同,特別是順風向功率譜的低頻部分要明顯高于Simiu譜,豎向功率譜高頻部分明顯低于Panofsky 譜.

圖7 典型大風天功率譜Fig.7 Power-spectrum densities of a typical windy day
分別采用式(1)、(2)和式(3)對所有順風向、橫風向和豎向的實測功率譜進行獨立擬合,然后對Au、Bu、Av、Bv、Aw、Bw6 個擬合參數的概率分布進行統計,統計模型采用正態分布概率模型,結果表明:順風向的Au均值為12.0,Bu均值為21.4,橫風向Av均值為12.4,Bv均值為17.7,規范中推薦的A值為33.33,B值為50;豎向的Aw均值為3.1,Bw均值為4.1,規范中推薦的Aw值為4.0,Bw值為4.0.水平順風向、橫風向及豎向的功率譜較規范推薦值相比略有不同.

式中:Su(z,f)、Sv(z,f)、Sw(z,f)分別為脈動風水平順風向、橫風向和豎向的功率譜密度函數;σ2u、 σ2v、σ2w分別為順風向、橫風向和豎向脈動風速的均方差;f為頻率;fz為折算頻率;z為離地高度.
采用擬合均值為取定值可以得到橋址區高空處3 個方向的擬合功率譜,見式(4)~(6).
貓道上高空處擬合功率譜與Simiu 譜、Panofsky 譜的對比如圖8所示,從圖中可以看出:水平方向低頻部分較Simiu 譜低,而高頻部分比Simiu 譜大;豎向功率譜所有頻率上均比Panofsky 譜略小,在山區受到山體的影響,其能量往高頻部分轉移.


圖8 功率譜對比Fig.8 Comparison of power-spectrum densities
3 結 論
(1)風攻角與風速存在明顯相關性,風速越低,風攻角的散布范圍也越廣,在95%保證率的情況下,風攻角的分布范圍為-9.0°~6.2°.
(2)大橋高空紊流度均較規范推薦值要小,3 個方向上的紊流度比值趨于一致.
(3)大橋跨中受到地表山體的影響有所減弱,紊流積分尺度比規范推薦的山區紊流積分尺度略大,但仍小于平原地區.
(4)由于受到山體的影響,順風向和橫風向的功率譜比較接近,低頻部分較Simiu 譜低,而高頻部分比Simiu 譜大,豎向功率譜所有頻率上均比Panofsky 譜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