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空”求“滿”的生活哲學
克萊爾·勒菲弗爾

一張雙人沙發,一把扶手椅,一張茶幾,一盞落地燈……除此之外,這間屋子里空無一物。好在門口處擺放著書柜,房里的書桌上還散落著幾枚硬幣,電腦屏幕也還亮著——否則,進入房間的人一定會認為這間公寓沒有人住。房內的擺設之所以這樣簡潔,是因為公寓的主人戴維·舒姆伯特是一位極端的極簡主義者。在他的家里,每件物品的留存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舒姆伯特的衣柜里只有30多件衣服,碗櫥里也只有生活必需的一套餐具。還有他的床——實際上只是一張薄床墊——白天卷起來放在壁櫥里,到了晚上就鋪開在修道院一般的房間中。
為何他會對這樣一種近乎于禁欲的極簡主義感興趣呢?如今的舒姆伯特是一項計算機工程的總負責人,家住昂熱。面對這個問題,這位40多歲的單身漢解釋道:“要想更直接地得到幸福,就要將精力集中在最主要的東西上。當過多的物品圍繞在身邊時,我們最終會感到被壓得喘不過氣。這些物品中的大部分我們其實都已不再用得到,而我們繼續留著它們,或許是因為它們價格昂貴,因為我們覺得總有一天它們還會派上用場,因為我們已經擁有它們了,或是因為它們可以給我們帶來回憶,有關某個深愛過的人或有關某個難忘的瞬間……就這樣,無用的物品不斷堆積,為了給它們騰出空間、為了將它們分類、整理、清潔,我們感到抓狂不已。至于那些真正重要的東西,卻會被淹沒在這些毫無用處的玩意兒中間了!”

? 修道院般的環境:戴維·舒姆伯特,昂熱附近一項計算機工程的負責人,極簡主義者。在他的家里,每件物品的留存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 極簡主義 |
這些無用的物件兒會把人拖垮。對于宣傳極簡主義主題書籍《釋放空間》的作者雷吉娜來講,我們甚至可以算是“被淹沒在了‘充裕之中”。她書中提到的一項極具說服力的研究就可以證明這一點。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學院進行的該研究,對32個美國家庭作了調研。這些家庭平均每家儲存著39雙鞋、90張DVD、212張CD、139件玩具以及483本書和雜志。由于東西太多,90%的家庭都選擇將一部分物品囤積在車庫中。而這些車庫中有3/4因為囤積了過多雜物而無法再停汽車!從未用過的迷你食品攪拌機、再也不會去重新閱讀的大學課本以及很久之前就已不再與他們的手機配套的充電器……為什么人們還要留著這些東西?“一件物品,僅僅實用是不夠的。”巴黎第九大學管理學教授研究員瓦蕾西·吉亞爾解釋道,“它是個人的延伸。每件物品背后都藏著一個故事,它見證了我們人生的某些時刻并使我們與他人產生了聯系,所以依戀這些物品是很正常的。”就好像,我們的衣櫥里,有80%的衣服從來都不會穿。而只有少數人愿意將它們全部廉價出售。

? 日式極簡主義示例:作為曾經的購物狂,佐佐木文雄成為了東方奉行極簡主義的代表人物。

? 生活日常:佐佐木家的總面積為20平米,沒有臥室。每天晚上,他都會將床墊從衣柜中拿出鋪開,第二天早晨再重新收好。
如果在搜索引擎中輸入“極簡主義”這個詞,你會看到有大量相關的博客、Youtube頻道、Facebook群組、Pinterest和Instagram賬號在夸贊將房屋內部清理干凈的好處,并附上了實施清理活動的建議與類似于“少即是多”的口號。這些極簡主義者(大多是培訓師、演講家或是暢銷書作者)都在個人發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并聲名遠播。此外,這種極簡主義趨勢的影響甚至還延伸到了一些更為高端的領域:例如美國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臉書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賽格威車發明者迪恩·卡門、布里奇沃特投資公司創始人雷蒙德·達里奧、甚至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等人,他們衣柜中的衣物數量都是出了名地少,而生活年代比他們更久遠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也如是。
原因是什么呢?他們之所以會選擇將衣物數量縮減到最少,既是因為時間不夠用,也是因為不希望自己在清晨毫無意義地為了挑選一套衣服而耗盡心力。法國電視節目主持人蒂利·阿迪森,無論在生活中或是舞臺上,永遠都只穿同一種顏色的衣服,背后的原因也如出一轍。他說過:“我不喜歡在早晨給自己制造麻煩。我只需穿一套黑西裝、一件黑T恤以及一條黑褲子,這一切在3秒之內就能完成。”阿迪森也的確將這樣的裝扮維持了40余年;而作為極簡主義的靈魂人物,史蒂夫·喬布斯也曾表示:“每次出行時,我都只想穿一件看起來文雅、可以讓我被迅速辨認出來的衣服。我覺得這使我的生活變得更加簡單,目前也并不打算改變這種風格。”他的經典裝扮就是黑色上裝、藍色的李維斯牛仔褲、灰色的新百倫運動鞋,而他發明的產品則也使得我們可以脫離掉屋內很多東西的束縛:書籍、報紙、CD、DVD、記事本、信件、相冊,甚至是收音機、電視、音箱、相機等等。這是所有喜愛清理雜物的人的福音。
極簡主義的12條準則:
1
如果扔掉這件東西后,你不會再次購買它,那就快扔掉它吧。
2
不要再期待將來有一天你會重新用上你已經擱置很久的東西。
3
如果有件東西你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扔掉,就把它放進紙箱子里收好。如果放了一年你都沒有動過,就把它扔掉吧。
4
不要直接扔掉別人有可能會用到的東西,轉賣或贈送都是不錯的選擇。
5
請盡可能地利用電子設備:音樂、電影、書籍和照片都可以儲存為電子格式,報紙、電視和電臺也都可以在電腦上收聽、收看。相機的存在也不再必要:你的手機就可以照相。
6
請為自己搭配好一套舒適、固定的服裝:它可以讓你無需在早晨為今天應該穿什么而思考太久。
7
用不到的空間,就讓它保持空曠。
8
不要再瘋狂購物。留出時間來好好思考一下:這件東西是真的能為你帶來快樂,還是只能用來在別人面前塑造一番形象。
9
不要以不貴為借口買下并不需要的東西。
10
嘗試去租用或借用物品。
11
不要只將極簡主義應用在實物方面。其他方面也需要精簡:例如將郵箱中的郵件分類整理、精簡人際關系、減少網絡社交平臺的使用等。
12
不要為了削減而削減。極簡主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方法。它的目的是使你將精力集中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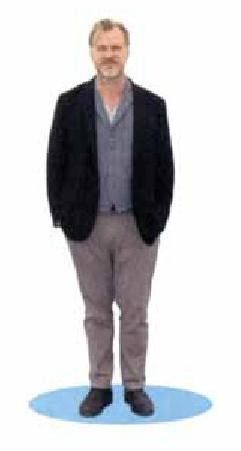
克里斯托弗·諾蘭
這位電影藝術家很久之前就認為“每天挑選一套新衣服穿是一件很浪費精力的事情。”(《紐約時報》雜志,2014年)

蒂利·阿迪森
“我不喜歡在早晨給自己制造麻煩。我只需穿一套黑西裝、一件黑T恤以及一條黑褲子,這一切在三秒之內就能作好決定。”

馬克·扎克伯格
“我希望我的時間可以盡量少用于作決定,尤其是那些與臉書集團無關的決定。”(2014年)

巴拉克·奧巴馬
“我只穿藍色或灰色的衣服,我試著將需要作的決定精簡到最少。”(出自《名利場》雜志,2012年)
| 一場地震帶來的轉變 |
如今39歲的日本男子佐佐木文雄可以算作踐行極簡主義的領袖人物之一。從事過編輯行業的他曾一度是一名購物狂,并且十分厭惡整理東西的過程。但自從接觸了禪學與道教文化后,他購物的頻率降低了。2011年,一場地震給日本太平洋沿岸地區造成了嚴重的破壞。“還未等被海嘯吞沒,這些平時被人們好生儲藏的物品竟已變成了殺人的元兇。”佐佐木在他的《丟掉不必要》一書中談道。他覺得所有這些不必要的物品都沒有多少存在的意義,隨即又扔掉了他的書、樂器和他那些為了自示聰慧而收藏的古董。他將衣柜幾乎完全騰空,還精簡了人際關系,從網絡社交平臺中抽身出來。此后,他身上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不知不覺地,他毫不費力地瘦了20斤。“減少物質財富可以激活我們感知滿足的能力。”他的這部作品在日本成為了暢銷書,被翻譯成了23種語言,在四大洲范圍內公開發售。然而這本書還是在發達國家的銷量最好。
“人們開始意識到購物不能帶來更多的快樂,甚至反而給他們帶來煩惱。因為無窮盡的購買會使他們受到束縛并且不斷滋生出新的欲望,這使他們不得不為了滿足自身欲望或償還信用卡而辛苦工作。”
“人們開始意識到購物不能帶來更多的快樂,甚至反而給他們帶來煩惱。因為無窮盡的購買會使他們受到束縛并且不斷滋生出新的欲望,這使他們不得不為了滿足自身欲望或償還信用卡而辛苦工作。因此,人們花在親情、友情、愛情上的時間越來越少。”佐佐木解釋道。除此之外,他還列舉了加利福尼亞大學積極心理學教授索尼婭·柳博米爾斯基在關于社會心理學科方面的研究成果:柳博米爾斯基認為,生活條件(物質財富、生活環境、健康狀況等)對人的幸福程度只起到10%的影響作用。其余的決定因素中,基因的作用占50%,人自身行為的因素占40%。佐佐木明確表示:“我們正是應該在這40%上下功夫。”因此,人們應該加強社交,多出游,增加體育鍛煉、多進行益智活動與思想實踐等等。另外,不要再留戀于那些完全用來逛街的午后時光了。
那些企圖通過買全新的或是自己極度渴望的物品來獲得快樂的人,也應注意。佐佐木對這種現象有完備的解釋(理論依據同樣是源于社會心理學):這種快樂是轉瞬即逝的。首先,因為社會消費是建立在人們長久的沮喪之上的。比如你剛剛買了一輛夢寐已久的車,但你可能會后悔沒有等到新款車發售。其次,我們的神經網絡本身就對事物(尤其是對積極的事物)有極強的適應能力,當你習慣了你的某件至愛的東西后,它就會失去對你的情感的影響力。為了重新獲得滿足感,人們便會再次消費。要想走出這個死循環,只有一個方法:與事物保持一定的距離。
巴黎第七大學經濟學教授、法國社會及消費觀察站的聯合創辦人菲利普·莫阿蒂認為極簡主義的流行也包含著這樣一種因素:“在一個物質積累已超出它所屬社會階層應有范圍的富裕社會中,或是在一個因反復出現丑聞(例如之前的健康危機、福斯集團汽車舞弊事件、計劃報廢等)而導致消費能力衰退的社會中,人們都會有一種追求與眾不同的渴望。”作為一名經濟學家與新興消費專家,莫阿蒂從2012年開始就發現這種現象正在逐漸蔓延:“那時,這種‘消費得更少,消費得更好的觀念才剛剛出現。而如今,大約已有1/4的法國人會這樣想。”但這個數目也只是冰山一角。莫阿蒂認為極簡主義者(或有極簡主義傾向者)的團體中未來將會有更多的年輕人、城市人口、高學歷者、富人、瑜伽運動或排毒果汁的愛好者,尤其是一些正感到迷茫的人。“他們當然關心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但是,這些對此其實并不懈怠、反而一直在為之戰斗的人群,他們最棘手的事情是當消費已不再能夠填補他們內心的空虛時,他們該如何慰藉自己的心靈。此外,‘準極簡主義者可能會冒著生活水平下降的風險,為從事一份喜歡的職業而去經受考驗。”
| 回溯本質 |
巴黎第五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多米尼克·戴澤將極簡主義當作一種典型的猶太基督教式的凈化。“這是一種在歷史、藝術史和宗教史上都曾反復出現的社會現象。就像新教承接了天主教的盛況,古典主義也作為洛可可藝術的延續而存在。極簡主義起源于當代藝術流派,以與流行藝術截然對立的形態誕生并存在。所有的這些流派都反映著一種回溯本質的意愿。”
前時尚博主、后成為職業培訓師的卡羅莉娜·德蘇蘭曾因擁有無數的名牌服飾而成名獲利。那時她用一整個房間來作衣柜,房里塞滿了衣服。而在某次戛納電影節上,她突然變了。“我曾每晚都站在紅毯上,帶著發飾,濃妝艷抹,穿得像個巨星一樣。這的確是某種榮耀。”她回憶道,但她也意外地感到了迷失,“后來,我發現了這個行業的荒誕之處。”之后,她花了3個月時間去印度旅行,只背著一個背包,里面僅僅裝著最基本的必需品。回來后,她對家里進行了徹底的清理。“舍棄的東西越多,我就越感到輕松。”慢慢地,30多歲的德蘇蘭感覺到持續已久的壓力消失了,她不再需要去強行了解每種流行趨勢,去時刻關注服飾的折扣情況或是擔心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因為她知道,她的生活并不是由這些因素決定的。如今她的衣櫥里,鞋、大衣、首飾之類的單品全部加起來也只有100件左右。這種轉變中最困難的是什么呢?是堅持。因為外界存在著很大的阻力:生活中不斷地有生日、父親節或母親節的慶祝聚會要參加,還有被極簡主義者視為噩夢的圣誕節。“要是有人問我什么東西可以使我感到快樂,我會選擇那些非物質的東西,例如去一間餐館吃頓飯、去看一場演出或是去旅行一次等等。”德蘇蘭解釋道。
而那些渴望經濟可以持續穩定地增長的人也大可放寬心:極簡主義思想的產生并不意味著消費型社會將就此停滯。“但隨著財富積累對消費的影響越來越小、支出情況越來越取決于個人感受,我們的確已進入到消費型社會的第二階段。”菲利普·莫阿蒂指出,他還發現人們越來越傾心于DIY、園藝以及其他具有創造性的活動,“這些活動都需要材料和裝備,因此還是會對地球產生影響,并不能解決環境問題。但這可以使人們變得更開心,僅憑這一點就已不算太差了。”
政客與名企業家的辦公室——表面上的極簡主義

政客和法國巴黎證交所上市的40家公司的老板們十分喜歡在煥新而清爽的地方工作。這當然是出于擔心形象問題的考慮。不管唐納德·特朗普愿不愿意接受——他的確是唯一可以在亂七八糟的辦公室工作還自得其樂的國家領導人。普林斯頓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的教授薩賓娜·卡斯特納已從事神經科學研究20余年,她論定:在一個堆滿物品的地方工作,的確會使人的專注力與感知能力減退。相反,另一研究顯示有秩序的工作環境則會使人更容易作出更加明智、合理的決定;對井井有條的空間的喜愛,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有責任心、勤奮等品格。總而言之,這樣的人會令人十分放心。而有些人,例如戰略咨詢機構愛德曼的女董事長馬里翁·達里烏托,就將極簡主義實踐得十分表面化。“在這個一切事物都可以在網絡上被監視、解讀、評論的時代,極簡主義風格的辦公室可以使我無需解釋太多事。但同樣,身處于十分整齊有序的環境也并不是萬全之策。因為這會顯得太過嚴肅或顯得你很少去公司。這樣也會帶來困擾。”她解釋道。就是在這種兩難的形勢下,達里烏托的交際名單中依舊有很多大公司(例如索迪斯、達能、中興、羅蘭貝格等等)的負責人。這種不純粹的極簡主義當然還出于對其他問題的“顧慮”,例如環境問題——在數字信息時代,使用成疊的紙質文件會顯得落后、不關注環保——和安全問題。達里烏托還補充道:“我們也不能忘記商務人士們隨時會出差,他們帶著裝有一切的筆記本電腦,可以隨時隨地進入工作狀態。總之,辦公室不再只是工作的地方,它越來越像一個展示自我的櫥窗,一種對企業管理文化的反映。人們會通過各種方法來讓它呈現出自己希望呈現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