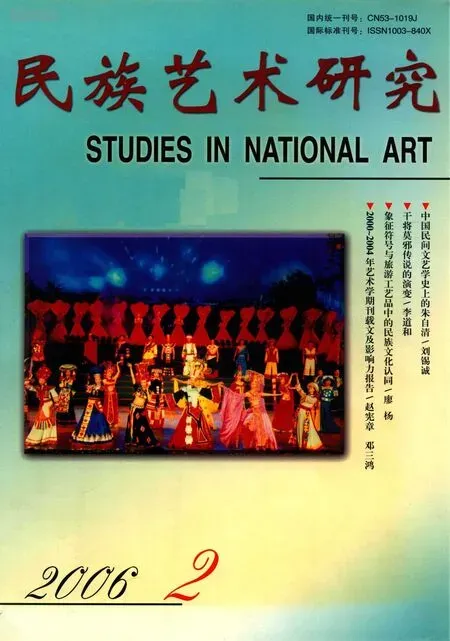文藝觀峰人與文藝高峰的甄別
劉涵之
這里的文藝觀峰人是指具有一定藝術素養和文藝鑒賞能力的普通公眾,他(她)們總是以自己的觀賞行為去實際地確認藝術作品的藝術高峰成就及其聲譽。可見,文藝觀峰人不是一般的社會公眾,而是能夠通過藝術活動利用自身藝術素養鑒別、欣賞文藝高峰的文藝接受者、文藝裁定者。在文藝作品的接受環節,他們往往慧眼識珠、披沙揀金,因而成為筑就文藝高峰不可或缺的主要力量。西諺云:“一千個讀者便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話相當樸實地道出了作為既普通又不普通的藝術欣賞者的文藝觀峰人之于文藝高峰筑就的作用。普通是指藝術觀峰人的大眾性、廣泛性,他(她)們來自社會不同階層,折射著藝術欣賞的最廣大群體的審美心理與審美認知,不普通是指觀峰人屬于審美的人,他(她)們完全能夠自由運用自己獨特的經驗(包括生活經驗和在生活經驗上形成的審美經驗)、情感對文藝作品做出具有個性化的審美判斷,并以之裁定藝術品質量的高低。在長達好幾百年的莎士比亞作品的閱讀和欣賞史上,藝術觀峰人的品鑒性參與不但持久地推動了莎士比亞戲劇的廣泛傳播,也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莎士比亞戲劇的總體藝術水準、藝術價值,甚至還能比莎士比亞更好地理解莎士比亞。這也證實了現象學美學大家杜夫海納的判斷是正確的,“不管藝術家多么自信,他完全明白,他不能既做裁判員又做當事人。他也知道,他永遠不是自己作品的不偏不倚的欣賞者,而唯一算數的是公眾的裁判。”[注][法]米·杜夫海納:《審美經驗現象學》(上冊),韓樹站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頁。
一、 文藝觀峰人與“文藝能力”
古往今來的文藝發展史表明,文藝高峰的筑就是一種歷史綜合力運作的結果,既有文藝大家的天才式貢獻,又有一定的社會環境和文藝傳播等機制的助力,同時還離不開文藝鑒賞與批評角色的積極參與。法國批評家蒂博代認為在文藝批評中存在三種批評,自發的批評、職業的批評和大師的批評。其中自發的批評通常由有教養的“公眾”來執行,批評形式則以“口頭”方式進行。[注][法]蒂博代:《六說文學批評》,趙堅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3-5頁。當我們稱文藝觀峰人是“以自己的觀賞行為去實際地確認藝術作品的藝術高峰成就及其聲譽”的普通觀眾時,其實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這樣的觀賞行為出自于觀峰人的自由選擇,內含自主性和自發性。王一川的《筑就文藝高峰的主體力量》一文,立足藝術創造者、藝術創造的物質和精神支撐、批評家、欣賞者、管理者的多重關系,梳理了筑就文藝高峰的五種主體力量(立峰人、造峰人、測峰人、觀峰人、護峰人)的貢獻維度,并指出觀峰人在其中的獨特作用:“只有經受住了高素養公眾的挑剔目光,真正的文藝高峰才可能得到時代和歷史的權威鑒定,而新的文藝高峰也才可能在這種權威鑒定所形成的優質文藝生態中繼續生成和涌現。”[注]王一川:《筑就文藝高峰的主體力量》,《光明日報》2017年3月8日。文藝觀峰人對文藝高峰的裁判是一種從欣賞者的審美體驗和情感滿足出發的裁判。按照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所建立的關于藝術品的藝術家、作品、世界、欣賞者四要素互動模式,文藝觀峰人可以歸屬到“欣賞者”一類,文藝觀峰人是文藝作品的聽眾、觀眾、讀者,文藝作品為文藝觀峰人創造,總是力圖能夠引發他們的關注。艾布拉姆斯認為,在西方傳統中,以欣賞者為中心的藝術鑒賞與批評體現出一種照顧欣賞者快感、需求的實用的傾向,“實用說”因之而命名。實用說這一理論“把藝術品主要視為某種目的的手段,從事某件事情的工具,并常常根據能否達到既定目的來判斷其價值”,“實用主義批評的視角,它的大部分基本語匯以及許多特殊的論題,都源于古典修辭理論。人們曾普遍認為,修辭術是勸說聽眾的工具,而大多數理論家都同意西塞羅的觀點,即為了說服聽眾,演說者必須贏得他們的好感,為他們提供信息,并感染他們的心靈。”[注][美]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酈稚牛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7頁。可見,在長久的經驗與意識中,人們總是從能否滿足欣賞者的愉悅這一心理與情感需求來考察、評判文藝作品的得失,并形成闡釋與批評文藝作品的種種理論。探討文藝觀峰人與文藝高峰之關系也不例外。我們可試舉批評大家約翰孫(亦譯為約翰遜)的名篇《〈莎士比亞戲劇集〉序言》為例。眾所周知,莎士比亞并非生而為文藝大師,更無法自證其偉大,他在英國文藝史上文藝巨匠崇高地位的樹立和約翰孫的重新發現息息相關,約翰孫的發現在相當程度上助益了其文學聲譽的攀升。約翰孫以理性和常識為標準來考評文藝家,認為文藝作品優劣由時間來檢驗,“有一些作品,它們的價值不是絕對的肯定的,而是逐漸被人發現的和經過比較后才能認識的;這些作品不是遵循一些論證的和推理的原則,而是完全通過觀察和體驗來感動讀者;對于這樣一些作品,除了看它們是否能夠經久和不斷受到讀者重視外,不可能采用任何其它標準……人們崇敬壽命長的著作并不是由于輕信古人較今人有更高的智慧,或是由于悲觀地相信人類一代不如一代,而是接受了大家公認的和無可置疑的論點的結果,就是大家認識最長久的作品必然經過最長久的考慮,而考慮得最周到的東西勢必被讀者了解得最深刻。”[注][英]約翰孫:《莎士比亞戲劇集》序言,楊周翰編選:《莎士比亞評論匯編》(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8頁。約翰孫斷言,莎士比亞是“自然的詩人”,反映的是“共同人性”“普遍人性”,這樣的共同性、普遍性只有從一代又一代讀者的閱讀體驗中才得到確認,也只有通過一代又一代讀者的閱讀體驗才能得以維系、拓展。自然,約翰孫指出的一代又一代的讀者絕非沒有鑒賞力的讀者,這樣的讀者以心體之、以血驗之,推動著莎士比亞作為文藝巨匠形象的建立,從而推動著人們對文藝高峰的認知——即是說,莎士比亞作為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藝高峰的代表性大師是離不開一代又一代數量頗可觀的文藝觀峰人的鑒賞、甄別。
值得注意的是,約翰孫在堅持時間標準的前提下還指出了“大家公認”和“無可置疑”這一必要條件。當我們稱文藝觀峰人為藝術接受的公眾,一方面是指文藝觀峰人數量之巨和隊伍之大,一方面是指公眾所代表的“公認”的心理與情感的社會群眾基礎。觀峰人之于文藝高峰的筑就,其作用恰恰表現在觀峰人“公認”的力量上。“公認”而非強迫承認說明,文藝高峰一旦筑就便獲得某種客觀性,這一客觀性有時雖然可以通過當代的觀峰人得到體現,但更需通過后來的觀峰人的集體認同,因此文藝高峰總是在一代又一代的廣大文藝欣賞者那里被證實,即約翰孫所看重的“大家公認”及時間檢驗。可見,“公認”之“公”既在其“公允”又在其“公共”,兩者皆備。如果說前述的“實用說”突出的是文藝家如何說服藝術欣賞者,那么藝術欣賞者如何去“公認”、為何會“公認”以及利用什么去“公認”則應該成為我們探討文藝觀峰人與文藝高峰之關系的突破口。顯然,缺乏觀峰人“公認”的文藝作品不可能成為文藝杰作,文藝杰作的裁判權也不是交由少數幾個文藝大師便可以決定的。“公認”作為觀峰人對文藝高峰的裁定既是方法也是目的,特別當“公認”是以一代又一代普通欣賞者的文藝素養為保障的時候。
美國學者喬納森·卡勒曾在《結構主義詩學》一書中提出“文學能力”的概念,認為具備“文學能力”的人能夠將文學“語法”內化,把“語言序列轉變為文學結構和文學意義”,“他事先對文學話語如何發揮作用一定心中有數,知道從文本中尋找什么,他必須把這種不曾明言的理解帶入閱讀活動。”[注][美]喬納森·卡勒:《結構主義詩學》,盛寧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頁。借用卡勒的說法,我們也可以稱文藝觀峰人是具備“文藝能力”的人。文藝觀峰人的優良藝術素養是一種能夠將文藝“語法”內化的能力,唯其如此,我們方可稱文藝觀峰人是通過文藝欣賞過程將文藝語言序列轉變為文藝結構和文藝意義并明了文藝話語如何發揮作用的理想接受者。如果面對文藝作品,不事先對文藝話語如何發揮作用有一定認識和一定敏感度,這樣的接受者就稱不上文藝欣賞者,更不用說文藝觀峰人。我們之所以稱文藝觀峰人是“以自己的觀賞行為去實際地確認藝術作品的藝術高峰成就及其聲譽”,強調的便是欣賞者把“文藝能力”自主、自發地發揮到最佳地步的欣賞效果、接受效果。就經驗和意識而言,這樣的“文藝能力”的發揮可能因為觀峰人的學養、氣質、心理的差異而不同。但真正的文藝高峰會使得觀峰人摒棄主觀臆斷只關注藝術——就具體的文藝作品的具體欣賞而言,文藝觀峰人則更能從文藝結構和文藝意義上把握文藝作品,從而可望不約而同地從眾多文藝作品中區別良莠,進而表現出真正品鑒文藝高峰的“文藝能力”。
二、公眾的“文藝能力”與文藝交往
自然文藝觀峰人的“文藝能力”不是某種天啟的、神秘的文藝欣賞力。馬克思說過:“只有音樂才激起人的音樂感;對于沒有音樂感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不是對象。”馬克思還說過:“如果你想得到藝術的享受,那你就必須是一個有藝術修養的人。”[注][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247頁。文藝觀峰人的“文藝能力”顯然和后天的文藝習得、熏陶、濡染緊密不可分。可以想象,一個毫無文藝準備的人不可能識別文藝高峰之本來面目,也不可能真正參與到筑就文藝高峰的整個環節。“文藝能力”釋放越多的欣賞越能促進觀峰人對文藝高峰的甄別。一部作品,越是能釋放公眾的“文藝能力”,它越是一部文藝作品,文藝作品的杰出、優秀取決于欣賞者和作品之間雙向交流的廣度與深度。缺乏廣度與深度的雙向交流,即便文藝作品多么優秀,即便文藝觀峰人多么有藝術修養,也不可能真正筑就文藝高峰。而文藝活動,一方面意味著每一個具備“藝術修養”的個體的文藝實踐地展開,一方面也意味著作為“公眾”的觀峰人與文藝高峰、文藝杰作之間自由對話地展開,文藝觀峰人是文藝杰作的期待知音,文藝杰作的創造者(文藝立峰人)總是期待著知音在鑒賞中走近藝術、進而甄別出文藝高峰。
不過,細究這樣的雙向交流并非一帆風順,它通常存在延宕、阻拒的可能。借用英國文化理論家斯圖亞特·霍爾關于傳播主體、受體之間的編碼、解碼的“主導-霸權的地位”“協商的代碼或立場”“對立碼”三種模式[注][英]斯圖亞特·霍爾:《編碼,解碼》,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358頁。,我們也可以稱文藝觀峰人對文藝杰作的甄別是在主導、協商、對立的路徑中不斷走向藝術交往的對話,走向對話化的藝術交往。“藝術品的特質在于它具有能激起人們的審美感情的固有的力量。可能正是感情的表達賦予了藝術品這種力量”,而“固有力量”要在“形式”上得到理解就是藝術家首先“應該把自己的感情輸導到某個確定的方面,把精力集中在某個確定的問題上。”[注][英]克萊夫·貝爾:《藝術》,周金環、馬鐘元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2-43頁。“把自己的感情輸導到某個確定的方面”“精力集中在某個確定的問題”自然是藝術家和觀峰人達成默契關系的必要條件。這個匯聚被疏導的情感的“確定的方面”不但規定著藝術成為藝術,同時也規定著藝術之所以被理解為藝術。一旦藝術作品遭遇觀峰人,一旦觀峰人面對藝術作品,這一雙向交流便由可能轉變為現實、由應然走向實然,轉變為現實中的藝術交往活動。正如斯托洛維奇說過的:“通過藝術的交往的這種驚人的效果是怎樣獲得的呢?這種效果的根源是生活本身,是人的交往的現實性,藝術創作再現人的交往的個性意義和社會意義。藝術作品概括地再現人們交往的形形色色的情境,模擬這種交往的過程。觀眾、讀者、聽眾同許多角色相結識……我們觀看倫勃朗或者克拉姆斯柯依的繪畫,同繪畫中所描繪的形象、并且通過這種形象同藝術家本人進行沉默的對話。形象進入我們的生活中,就像生活在我們周圍的人們的形象一樣,而有時更有甚者——作為肖像形象,它概括、豐富和擴展了我們的生活經驗。”[注][愛沙尼亞]斯托洛維奇:《藝術活動的功能》,凌繼堯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171頁。藝術杰作意味著藝術作品對觀峰人的感染力的豐沛,也同樣意味觀峰人為何會領悟這樣的感染力。不但文藝杰作和觀峰人之間存在一種對話關系,文藝杰作在觀峰人之間也能形成一種“對話”關系。美學大師康德告訴我們:“鑒賞判斷必定具有一條主觀原則,這條原則只通過情感而不通過概念,卻可能普遍有效地規定什么是令人喜歡的、什么是令人討厭的。但一條這樣的原則將只能被看作共通感……只有在這前提之下,即有一個共通感……只有在這樣一個共通感的前提下,才能作鑒賞判斷。”[注][德]伊曼紐爾·康德:《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4-75頁。審美判斷尤其是鑒賞判斷中的“共通感”決定了觀峰人和文藝杰作對話基礎的建立,觀峰人于此不但能夠裁定何種文藝為文藝高峰,而且還能想象類似的不分時空的每一個藝術欣賞者都能裁定何種文藝為文藝高峰。如此這般,雖然文藝欣賞的具體環節每每“眾口難調”,“文藝能力” 卻指向共同經驗的確認——結果,每一個觀峰人都必然地相信他的裁定是公允的、客觀的裁定,觀峰人“無可置疑”的權威亦源于此。
“作品在鼓勵人去充當見證人時,它在人的身上發展了人。”[注][法]米·杜夫海納:《審美經驗現象學》(上冊),韓樹站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頁。文藝觀峰人作為文藝杰作的見證人即使單獨出現也是公眾中的一員,文藝作品需要公眾,越是文藝杰作越是需要公眾,這是一種從“人的身上發展人”的雙重需要。文藝杰作的意義不可竭盡,這說明公眾永遠需要不斷擴大,公眾的隊伍永遠需要延續,以便開展新的藝術交往。“審美對象能使公眾構成人群,因為它把自己看作一種最高的客觀性,這種客觀性把各個人聯合起來,強迫他們忘掉個人的特殊性……公眾就是一個特有的人群:它構成一個實在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不是建立在一種制度或代表制度的客觀性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作品的高度客觀性的基礎之上的。作品強迫我放棄我自己的差異性,迫使我變成我的同類人的同類人,像我的同類人那樣接受表演規則,去觀看或甚至去欣賞。”[注][法]米·杜夫海納:《審美經驗現象學》(上冊),韓樹站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頁。公眾的裁定因公允而權威,對話化的藝術交往在保證觀峰人裁定的權威,還涉及藝術作品魅力的被證實:在藝術家一端,藝術家的創作能力是藝術質量的保證;在欣賞者一端,公眾的“文藝能力”是藝術質量被證實的保證。文藝交往將兩端聯系起來,從而實現對藝術價值的展現:“藝術家的未來的交談者作為藝術家同自身的對話,作為自我交際——這種交際吸收了藝術家同人們交往的全部經驗,參與到創作過程中來……藝術作品結構考慮到未來的對話,因此,這種結構在其本質上是對話性的。”公眾的共同體性質保障了對話的自由進行,也保障了藝術價值的充分實現,因為“藝術不僅進入人類交往的過程,而且是這種交往的不可替代的手段,同時,它本身在其自我價值上也是一種交往。”[注][愛沙尼亞]斯托洛維奇:《藝術活動的功能》,凌繼堯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167頁。
三、“全面文化”與文藝高峰的甄別
無論從短時段看,還是從長時段看,筑就文藝高峰的五種主體力量都是辯證統一在文藝發展史中的。但每一主體參與文藝高峰的筑就方式、角度不同,所以需要考察其與文藝高峰關系所存在的差異。如,立峰人關涉文藝創造、造峰人關涉文藝創造的物質和精神支撐、測峰人關涉文藝批評、護峰人關涉文藝管理。文藝測峰人是直接面對文藝作品的欣賞者,其“文藝能力”在經由個體審美經驗的表達中不得不以自由對話式方式推動文藝作品“結構與意義”的最終完成,這無疑是欣賞者根據“文藝能力”對文藝杰作的裁定。“文藝作品具有兩極。我們可以稱之為藝術極和審美極。藝術極是作者寫出的本文,而審美極是讀者對本文的實現。從這兩種極化的觀點看來,十分清楚,作品本身即不能等同于本文也不能等同于具體化,而必須是處于兩者之間的某個地方。作品就其自身而言是虛的,因為它既不能還原為本文的現實,也不能還原為讀者的主體性,在這種虛空性中它衍生出自己的能動性。由于讀者經歷了本文所提供的各種透視角度,把不同的視點和模式相互聯結起來,所以他就使作品開始運動,從而也使自己開始運動。”[注][德]沃·伊瑟尓:《閱讀行為》,金惠敏等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6頁。文藝觀峰人對文藝杰作的鑒賞、甄別不是被動適應文藝作品的“藝術極”,也不是脫離文藝作品生硬地創造“審美極”。“藝術極”召喚“審美極”正如文藝作品召喚欣賞者。事實上兩者相互依賴,相互提升,共同促進文藝高峰的筑就。文藝立峰人離開觀峰人將文藝作品的“藝術極”能動性地還原為“審美極”的接受環節,文藝作品再偉大也沒人懂,文藝觀峰人拋開文藝立峰人通過文藝作品創造的“藝術極”,其能動性再強,“審美極”也必然落空。在文藝發展史上,文藝高峰的歷史累積,立峰人對已有的文藝杰作的批判性繼承,總是伴隨著一代又一代觀峰人的能動性參與和立峰人對其“文藝能力”的多方面照顧。如此循環往復螺旋上升,文藝高峰才峰峰相連地屹立于古今文藝史上。
法國文化理論家路易·多洛在《個體文化與大眾文化》一書中曾提出“全面文化”的概念,在他看來,全面文化是“唯一真正的文化”,它“在思維的主要領域里有著一整套的均衡知識,因而掌握全面文化的人,一方面警覺性高、進取性強,從而對周圍產生巨大影響;另一方面他本能地傾向于通過自己的創造性將全面文化顯示出來”。“全面文化表現出良好的素養,表現出判斷力、感受力、剛毅性格,但是沒有牢靠的知識就不能成其為全面文化,全面文化是超越任何專業知識的。”[注][法]路易·多洛:《個體文化與大眾文化》,黃建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75頁。多洛提出的“全面文化”和我們這里討論的“文藝能力”、文藝交往和文藝高峰的筑就存在某些重疊和一致的地方,如果說全面文化是“唯一真正的文化”,那么這一界定也適合文藝高峰對文藝觀峰人的召喚、文藝觀峰人對文藝高峰的甄別這一雙向的審美活動所代表的審美文化。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而言,文藝立峰人的創造性便是文藝杰作所表征的“全面文化”,無論在美學形式上還是思想內容上都將超越其他文藝作品,一覽眾山小,從而才有望突破時空限制,獲得相對的普遍性。柏拉圖就對天才式的文藝立峰人的貢獻有過高度禮贊:“我們必須尋找這樣一些藝人,憑著優良的天賦,他們能夠追隨真正的美和善的蹤跡,使我們的年輕人也能夠循此道理前進,進入健康之鄉,那里的美好作品能給他們帶來益處,他們的眼睛看到的和他們的耳朵聽到的都是美好的東西,這樣一來,就好比春風化雨,潛移默化,使他們不知不覺地受到熏陶,從童年起就與美好的理智融合為一。”[注][古希臘]柏拉圖:《國家篇》,《柏拉圖全集》(第2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頁。文藝杰作種類不同,形式千差萬別,在廣袤的文藝園圃中它們競相綻放各顯風姿,然而無不反映出立峰人對人生、社會意義的理解、對“真正的美和善”的理解。每一座文藝高峰都是完美體現“真正的美和善”的“全面文化”,所以一旦文藝高峰被筑就,它就不屬于某個時代和某個地域,它毋寧是屬于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地域。這也是人們愿意從一代又一代的觀峰人、跨地域的觀峰人那里來探究文藝高峰魅力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強調文藝高峰和觀峰人的召喚和被召喚人關系及其自由對話是一種“全面文化”的建立,不是說這一全面文化先表現在立峰人的主體作用上,然后被動地表現在觀峰人的欣賞和甄別活動中。每一個觀峰人其實都是帶著自己的獨特審美視野參與對文藝作品的理解,當這樣的理解越是融合于他對“真正的美和善”的認同時,我們才可稱藝術交往的真正完成。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巨著《文心雕龍》雖然提出“知音難求”說,但也肯定“良書盈篋,妙鑒乃訂”[注](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王運熙、周鋒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頁。,意思是只有真正的文藝鑒賞家才能領略“良書”之“良”,才能甄別出優秀的作品。唯其如此,我們才有必要認真對待魯迅對《紅樓夢》的閱讀方法的寶貴意見。魯迅說:“《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書。誰是作者和續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注]魯迅:《絳洞花主》小引,《魯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頁。在魯迅看來,所謂“經學家”“道學家”“才子”“革命家”“流言家”一類讀者都不是文藝高峰《紅樓夢》真正的欣賞者,他們將自己偏狹的經驗而非審美視野帶入閱讀,結果自然偏離了《紅樓夢》的旨趣、偏離了文藝立峰人曹雪芹的苦心經營。他們無法識別文藝高峰的本來面目,因為他們的偏狹經驗決定他們的閱讀不是一次實現文藝交往的“全面文化”的接受之旅。文藝高峰和觀峰人之間的文藝交往所實現的“全面文化”正如清人譚獻在《復堂詞話》中所言:“旁通其情,觸類以感,充類以盡;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注](清)周濟、譚獻、馮熙:《介存齋論詞雜著 復堂詞話 蒿庵論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頁。明乎此,我們才能說觀峰人有可能比莎士比亞更好地理解莎士比亞,才能說文藝高峰的筑就離不開觀峰人的能動性參與。顯然,這應該成為我們當下討論文藝高峰的筑就進程、觀峰人能動性作用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