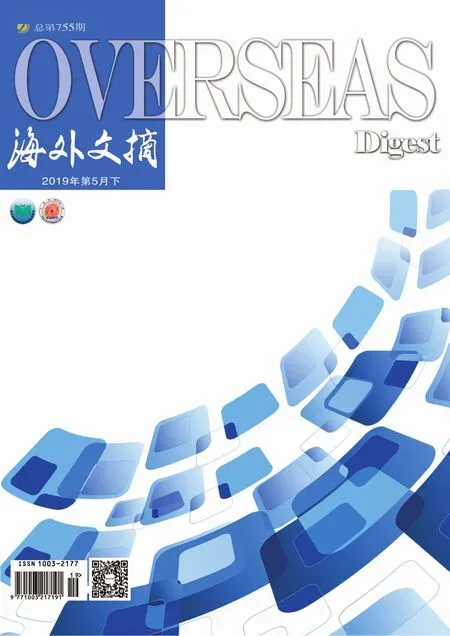從女性主義敘事學角度分析《溫柔之歌》
秦佳蔚
(西安外國語大學西方語言文化學院,陜西西安 710000)
0 引言
《溫柔之歌》(Chanson douce)是一部由摩洛哥裔法國女作家蕾拉·斯利瑪尼所著的小說,于2016年獲得法國最高文學獎項——龔古爾文學獎,2017年11月引入中國。這部小說講述了一個“仙女般的”保姆殺死雇主的兩個孩子的人性悲劇。小說在獲獎之前已經成為享譽法國的暢銷書,截至2017年法語版銷量已經超過60萬冊,版權已售37國。作者憑借此書名聲大躁,2017年11月被法國總統馬克龍任命為他的特別代表,擔任全球法語推廣大使。本書的中文譯者袁筱一教授也憑借譯作《溫柔之歌》獲得第十屆“傅雷翻譯出版獎”。可以說,《溫柔之歌》自問世以來,就受到了廣大學者及讀者的強烈關注與認同。
女性主義敘事學是女性主義文評與經典結構主義敘事學相結合的產物,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由美國學者蘇珊·S·蘭瑟開創。女性主義敘事學主要研究女作家筆下的作品,聚焦于敘事結構和敘述技巧所體現的性別政治。女性主義敘事學將敘事形式分析與性別視角融為一體,同時關注人物、作者、敘述者、讀者和性別因素,主要研究女性作家在創作時傾向于采用的敘事手法和敘事技巧,作品結構上的特征,社會語境對作者敘事的影響等等。女性主義敘事學與女性主義文評享有共同的政治目標:揭示和改變女性被客體化、邊緣化的局面,爭取男女平等,對于研究女性作家的作品和女性主義思想都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從女性主義敘事學的角度出發,探討《溫柔之歌》中的敘事形式和敘述聲音,分析作品中所體現出的女性煎熬、掙扎與反抗,以及作者字里行間所體現出的女性主義思想和為女性發聲的訴求。
1 敘事形式:凸顯女性特征的人物和情節模式
傳統的女性主義批評和女性主義敘事學都認為人物和情節是構成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二者的關注點有所不同:傳統的女性主義批評聚焦于女性人物的思想和行動是否能體現出女性意識,以及男性人物是通過什么行為和方式歧視女性人物的,而女性主義敘事學的關注點是故事中男女二元對立的情節模式體現出的性別政治。通過研究《溫柔之歌》中的人物與情節設置,可以看出蕾拉·斯利瑪尼在作品中所體現的女性主義敘事學特征。
1.1 人物類型:社會中的典型女性形象
1.1.1 新時代女性代表:米莉亞姆
米莉亞姆是一個很豐富的現代女性形象: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努力抗爭出身、經歷過作為家庭主婦的絕望、回歸職場后沉陷于對孩子和家庭的愧疚。自古以來,女性在社會中的位置都是被動的,有些人認為女性生來就是家庭、丈夫和兒女的附屬品,她們的價值只能依托于家庭而存在。她們不能享有和男性一樣的權利,卻被要求需盡到比男性更多的義務。雖然,女性主義思潮和女權主義運動自19世紀末以來蓬勃發展,女性經濟和社會狀況也有所改觀,但早已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還是在某種程度上將現代女性牢牢地束縛在家庭之中。女權主義運動使女性獲得了與男性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權利,但也造成了當代女性在投入職場之后家庭與事業難以平衡的困境。“女強人”一詞的貶義化就體現了如今社會對女性以事業為重這一現象的反對和不容。
米莉亞姆的困境與煎熬正是當今社會中千千萬萬女性的困境與煎熬。她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受到先進思想的熏陶,渴求在社會和事業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但往往伴隨著周圍反對的聲音和永不停息的非議:如自私利己,如不合格的母親。蕾拉·斯利瑪尼通過米莉亞姆這一生動的形象,將如今女性的生存困境表現地淋漓盡致。
1.1.2 孤獨的產物:路易斯
當路易斯一個人回到自己破舊的小屋時,孤獨就像毒癮一樣發作。與當保姆的她在外時沉著、謹慎、完美的形象不同,獨自時的她神經質、焦慮、孤獨、脆弱。路易斯代表的是生活在社會底層,飽受折磨又不斷掙扎的女性:經濟壓力使她透不過氣,壓迫自己的丈夫去世后留給自己的只有債務,女兒離家出走杳無音信,階級差異帶給她不斷的心理沖擊……
袁筱一教授在《溫柔之歌》的譯后記中提到:“或許,現代社會的一個標志性特征就是,當十九世紀戲劇化呈現的階級差異被漸漸抹平,社會分裂成規模更小的單位,甚至是干脆分裂成個體之后,人會異常孤獨。沒有人真正了解路易斯:她的雇主、她看顧過的孩子、她的房東、她的丈夫和女兒。”她的雇主只認識工作時作為保姆的她,她看顧過的孩子們不會想去理解生活的真實模樣,她的房東只關心她是否會按時交租,以及怎樣在趕她走時找借口扣下她的押金,而她的丈夫和女兒也并沒有扮演她他們應有的家人角色。人與人之間的無法溝通,矛盾的加劇,使絕境下的路易斯產生了心理質變,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路易斯這一形象的悲劇是社會中萬千底層女性的生活縮影。作者將路易斯作為小說的主要人物,帶大家慢慢走進她的生活,將社會中以路易斯為代表的女性弱勢群體的復雜地位與邊緣化赤裸裸地展現在大眾面前,通過一個普通保姆造成的悲劇來為女性發聲,為女性爭取關注與利益。
1.2 情節模式:不同階層女性生活中的掙扎與反抗
1.2.1 日常化寫作
作者蕾拉·斯利瑪尼在寫作時將目光聚焦于保姆和年輕夫妻的普通日常生活:路易斯照看孩子、保羅和米莉亞姆的相處、路易斯與雇主之間的關系、朋友聚會、外出旅游,諸如此類。這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生活,我們之中每個人都身處其中的生活。蕾拉并沒有為了情節上的戲劇沖突和跌宕起伏而刻意制造不可調合的矛盾,有的只是瑣碎的日常和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小小摩擦。
米莉亞姆夫妻的生活雖然比路易斯富裕一些,但卻連中產都算不上,雖然住在還算體面的街區里,但其實只是大樓里最小的一個戶型。米莉亞姆開始工作后,他們的收入將是“最為不利的那個層次”:緊急時不能求助政府救濟,請個保姆又捉襟見肘。米莉亞姆夫妻雖與路易斯分處不同的階級,但階級矛盾還沒有大到足以讓保姆產生殺人的邪惡念頭。米莉亞姆也不是一個挑剔刻薄的雇主,相反,她對路易斯百分之百的信任,尊重她,把她當作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員。她會時不時送路易斯小禮物,給她買她最喜歡吃的橘子蛋糕,買衣服用廉價的袋子包起來以免傷害到路易斯的自尊心。他們夫妻還會帶路易斯一起去希臘旅游。看起來,雇主與雇工之間沒有明顯的主流與邊緣、第一性與第二性、主觀上的侮辱與被侮辱的關系。甚或這里面連個愛情故事都沒有,保姆與雇主之間也沒有發生任何沖突,或者感情糾紛。
矛盾隱藏于平淡的生活之下,如影隨行,不可避免。當路易斯在這個家庭中的過度介入讓米莉亞姆夫妻無法繼續忍受,當雙方的生活方式與消費觀念的差異表現地愈加明顯,當兩個孩子陸續長大,這個家庭將不再需要路易斯的存在,他們之間的親密不再,沉默與誤會在不斷發酵。作者通過對生活中的一系列瑣碎日常進行細致描寫,讓讀者目睹著路易斯一步步地走向罪惡的深淵。日常越平凡越瑣碎,保姆殺掉兩個孩子的行為便越給人以沖擊。
1.2.2 米莉亞姆的覺醒與反抗
米莉亞姆在生完兩個孩子后,開始無法忍受家庭生活的瑣碎與繁雜,她在孩子和家庭中日漸暗淡。她嫉妒自己的丈夫,拒絕與朋友相處,“她覺得自己差不多就是一具行尸走肉”,她每天都沉浸在酸澀與悔恨之中。法律系同學帕斯卡的出現喚醒了她的女性意識,結束了她的封閉狀態,將她從“如同坐牢般的幸福”中解救出來。他給她工作,給予她新的社會角色——律師,從此,她不再只是一個精疲力竭的母親。
然而米莉亞姆需要抗爭才能進入職業生涯:丈夫的反對,婆婆的譴責;進入職場后她仍需抗爭,與因為不能照顧孩子而產生的罪惡感而抗爭。袁筱一教授在《路易斯為什么殺人》中總結道:“她一路都在反抗,用教育抗爭出身,用職業奮斗抗爭性別上的不平等,用公平——她是個律師——的信仰來抗爭社會身份的責任帶來的不適感。”
1.2.3 路易斯的掙扎與反抗
階級差異、男權壓迫與貧窮是壓在路易斯身上的三座大山,她在這三座大山下艱難生存。與雇主一家的階級差異是她一輩子都無法逾越的鴻溝,矛盾體現在生活質量、生活方式與內容和生活觀念等諸多方面。當米莉亞姆和保羅夫婦在聚會上將路易斯驕傲地介紹給朋友并邀請她一起慶祝時,她感到的只有尷尬和無所適從。“她就像個外國人、一個遭到流放的人一樣不自在,完全不懂周圍人的語言。”路易斯喜歡研究放在信箱上的各種宣傳小冊子,而年輕夫妻基本上看都不看就會扔掉。路易斯有扔食物恐懼癥,她喜歡刮罐頭底,還讓孩子們舔干凈酸奶盒。她把女主人已經扔掉的雞架又從垃圾桶撿回來讓孩子們吃掉,把吃干凈的雞架擺在桌子上以反抗和報復米莉亞姆的浪費。故事的轉折點發生在路易斯與米莉亞姆夫婦一起希臘度假之后,她看到了平生從未見過的美景,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于是她試圖越過階級的鴻溝,把這個家庭當作她的救命稻草來改變生活。結果自然是悲劇性的。
此外,男權的長期壓迫也是路易斯發生心理質變的一個重要因素。丈夫、房東、雇主,他們都在壓倒路易斯的過程中踩上了自己的一腳。路易斯的丈夫侮辱她,打罵她,她的男性雇主也并未把她當作一個平等的人來對待。她的前雇主弗蘭克先生在知道她懷孕后要求她打掉孩子,因為孩子是她繼續工作的阻礙。保羅雖然帶她一起去旅游,卻在她表示不會游泳之后感到尷尬,感到惱火。“他恨路易斯,非要把她的貧困、她的脆弱一并拖到這里來。一副殉道者的表情,毀了他們美好的一天。”當路易斯給保羅的女兒涂上指甲油,涂上胭脂、眼影和唇膏,把她打扮成自認為很美的樣子時,保羅卻認為這一幕污穢、不潔,他的女兒仿佛變成了小丑,夜場歌女,他大聲斥責路易斯“粗俗”。
貧窮是路易斯逃不開的宿命。她勤懇工作,總是喜歡幫雇主做一些分外的事情,因為這能討雇主歡心。她謹小慎微,從不放縱自己,也嚴格要求女兒,與雇主度假時從不讓別人覺得自己是在享受,因為她認為“如果你玩得太高興,他們會感覺不太好。”即便如此,她還是還不清丈夫留下的債務。住在一個破舊的小屋子里,還是會因為拖欠房租而被房東趕出來流落街頭。她一直在掙扎,一直在抗爭,但卻始終躲不過底層小人物的悲慘命運。
2 敘述聲音:全知視角的作者型敘述聲音
蘭瑟在《虛構的權威》一書中說道:“對于當代女性主義者,沒有任何哪個詞比‘聲音'這個術語更令人覺得如雷貫耳了。”“聲音”是指敘事中的講述者,蘭瑟在她的書中將女性作家的聲音分為作者型、個人型和集體型三種類型。其中,作者型聲音表示一種“異故事”的、集體的并具有潛在自我指稱意義的敘事狀態。敘述者不是虛構世界的參與者,它的敘述對象是讀者大眾。蘭瑟認為,作者型敘述聲音是最具權威的一種聲音,因為敘述者存在于敘述時間以外,而且不會被事件加以“人化”。
作者型敘述聲音因其全知視角而顯得具有可信度,避免了個人聲音的有限視角和觀點,以旁觀者的角度向我們講述故事的發展。《溫柔之歌》一書全部采用作者型敘述聲音,但敘述者僅表述行為,即僅僅敘述虛構人物的言辭和行動,不作深層次的思考與評價。敘述者慢慢講述著保姆的痛苦與孤獨,講述著她的困境,她的秘密,以及在與雇主產生矛盾后的壓抑和瘋狂,但米莉亞姆夫婦對此卻一無所知。他帶領著我們走進路易斯的生活和內心世界,讓我們隨他一起探尋路易斯殺人的秘密。他沒有站在道德的制高點評判在這場悲劇中誰對誰錯,沒有表示出對誰的同情或對誰的憤慨,只是平靜地將故事展現在讀者面前。通過這種方法,作者型敘述聲音激發的作者權威得到一定程度的消磨。
同時,《溫柔之歌》大量采用“拉開距離”的作者型敘事形式。直接對話場面于是變成以敘述者為媒介的敘事,人物的“對白”經過融化,凝練為間接引語。這樣小說的內容更簡潔,方式更間接,也最能拉開距離。如書中對路易斯在丈夫病發時的反應描寫:“她不停地說,自責地說在調味汁里放了過多的紅酒,所以菜味發酸,還愚蠢地說到了胃酸的理論。她不停地說啊,說啊,給出建議,自責,請求原諒。”這種情況下,敘述者事先得到允許,把小說中人物的話語加以凝練,并與自己的話融為一體,用自己的風格把一個對話場景當作一個事件來描繪解釋。這樣,小說人物都眾口一詞,說著敘述者的語言,那么這樣的敘事也建立了一種更高的、無法復制的權威。
此外,通過上述敘事形式,敘述者話語和小說人物話語之間的區別被模糊掉了,有時敘述者的話語表面上看起來是作者型敘述聲音,但不久后便又轉換成小說人物的話語。在《溫柔之歌》中,路易斯因為拖欠房租面臨著被房東趕走流落街頭的局面,在看到一個男人在街頭小便時,她徹底崩潰了。“躺在床上,她無法入睡。她不停地去想那個陰影里的男人。她無法想象,很快,在那兒的就會是她。她會在街頭游蕩。即便是這么一間非人的小房子,她也將迫不得已離開,她會像動物一樣,在街頭大小便。”這段話看似是作者型敘述聲音的講述,但通過“她不停地去想”、“她無法想象”等詞又回到了路易斯的敘事視角。
蕾拉·斯利瑪尼在寫作時選擇了一條對抗性的道路,一方面選擇作者型敘述聲音,摒棄個人型聲音,來構建當今女性作家的權威;另一方面卻又減弱作者型敘述聲音帶來的作者權威,不評判虛構世界中的是與非,將保姆殺人的原因交由讀者自己探尋。
3 結語
蕾拉·斯利瑪尼的《溫柔之歌》體現出明顯的女性主義敘事特征:首先,小說的主題和故事情節圍繞女性展開,塑造了路易斯、米莉亞姆等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她們在社會中的掙扎與反抗,反映出女性在當代社會中的復雜地位,表達出對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的反抗;其次,小說的敘事模式和敘述聲音的選擇體現出作者對女性主義敘事技巧的純熟運用,建立了女性作家權威,證明了女性可以從事文學寫作這一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