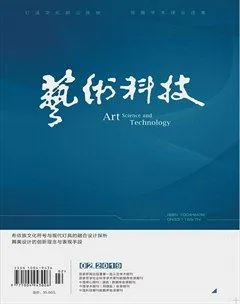當代民族藝術創作的生態美學向度
米華
摘 要:本文剖析少數民族作家生態寫作的現狀、題材、意象及文本形態,探究其立足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在回望大地、崇敬自然、反思現代文明的書寫中,在人與自然的對話中,以批判的向度反思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探尋引發生態危機的深層文化根源。這種獨具民族特色的生態書寫折射著少數民族作家對人類詩意棲居的美學思考,豐盈了少數民族文學的意義空間,豐富了民族文學的領域,在中國當代文壇具有獨特的價值。
關鍵詞:生態書寫;少數民族文學;生態救贖
1 生態危機語境下的生態書寫
20世紀是環境破壞的世紀。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后果》一書中指出現現代性的到來給人類引入一種新的風險景象。人類中心主義是工業革命和啟蒙時代的產物,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曾表現出相對的真理性,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隨著近代工業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它強調“人是萬物的尺度”,崇尚人的中心主體地位,導致人對自然掠奪性的開發、無限制的攫取,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出現了大量破壞自然自然和生態環境的事件。面對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1962年美國女生物學家瑞秋·卡森《寂靜的春天》的問世掀起了全球范圍內生態文學創作的熱潮。
“生態” (Ecological) 有 “生態學的、生態的、生態保護的”之意,而其詞頭(Eco) 則有 “生態的、家庭的、經濟的”之意,實際上是對主客二分的二元對立的解構。不同于人類中心主義或生態中心主義,生態美學力主一種將之調和的生態整體主義,或者是更加進一步的生態存在論,人與世界是一種 “此在與世界”須臾難離的關系,更加符合生態文明時代人與自然關系的實際與要求。[1]文學是人學,關注人的生存意義和價值,表現人的生存狀態,并體現對人類的終極關懷。生態寫作者及其研究者通過“生態”書寫要探索的核心問題是人類的文明和發展究竟出了什么問題。[2]
隨著20世紀90年代生態書寫實踐的豐富及理論研究的逐步深入,生態文學已經成為文學領域值得關注的一大亮點。有學者將新時代生態文學的特征概括為四點,即以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文學;是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的關系的文學;是探尋生態危機社會根源的文學;是表達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想的文學。[3]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曾多次強調生態保護和生態文明的重要性,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甚至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思想正在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作家的生態書寫。作家們從傳承五千多年的中華文化中,汲取豐富的生態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為易也”的哲學思想,“勸君莫打三春鳥,兒在巢中忘母歸”的詩文美句,“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的治家名言。此外,西方生態文學、生態哲學思想傳入中國,也影響到中國作家的生態寫作。特別是最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生態文學作品涌現出來,引起讀者的關注并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伴隨生態書寫一系列可喜變化同時出現的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在生態書寫的主流話語體系中,書寫的民族維度被模糊,忽視了對少數民族生態文學創作的民族性與獨特性的分析與研究。少數民族文學作為中國文學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擁有豐富多樣的民間神話,又有絢爛多彩的現當代文學創作;既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蘊,又迸發著鮮活的生命力,已成為中國文學家族中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特別是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們,立足于深厚的民族文學積淀的同時,緊緊抓住時代脈搏,用手中的筆有力地回應當下社會領域凸顯的各種生態問題,把文學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緊密結合,為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注入蓬勃生機。
2 深厚的少數民族文化積淀蘊含生態智慧
文化是一個龐大的體系。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露絲·本尼迪特克認為“一種文化就像是一個人,是思想和行為的一個或多或少貫一的模式。每一種文化中都會形成一種并不必然是其他社會形態都有的獨特意圖。”[4]文學作為一種文化樣式并不是自發生成、孤立存在的。各個民族的民族文學都會或多或少受到宗教的影響,與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學相比,回族文學受到宗教影響的特點特別鮮明。伊斯蘭教的典籍傳播廣泛,影響深遠,其中大量描述自然的語言,把抽象的宗教經典用具象的自然語言的符號來詮釋,在對教義潤物細無聲的傳播過程中,也讓美進入人的心靈,感受絢麗多彩的自然之美。[5]大量對動植物奇妙的、富有想象力的描繪,既帶有濃郁的伊斯蘭色彩,又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文學既是文化的產物,又是文化的組成部分。少數民族文學是少數民族在長期的文學創作實踐中創造出來的反映本民族文化傳統的藝術形式,經典文本已深入到作家內心,這種共同的民族基因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他們的文學創作,并以民族風格的形式外化為回族文學的基本美學特征。
3 回望大地的生態意象建構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文學領域涌現出的這批極具代表性的作家們既扎根民族文化傳統,又記錄時代,緊貼大地,直面生態危機這一社會問題,創作了一系列優秀的小說、詩歌、散文作品, 形成了獨具民族特性的生態文學寫作范式。少數民族文化底蘊的滋養及面對生態危機時強烈的人文情懷使他們的生態書寫成為一種生命書寫。在寫作中他們創造了不同的意象豐富了作品的內涵,張揚作品的藝術魅力。文學創作的自主性決定了文學意象具有極強的個體性,同時共同的民族背景及民族文化特質決定了從整體來看回族文學生態書寫的意象又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筆者擬以當代少數民族作家生態書寫中頻繁出現的“回望大地”這一意象為例,探究它們在少數民族生態書寫中所承載的獨特美學意涵,從而為更好地解讀民族生態文學作品提供全新的視角。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詩人何為》一書中將核心問題聚焦在技術時代的暗夜詩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他看來,人隨制造意愿而行的冒險,使人站立在世界的對立面,把物,把自然,把存在者整體,以至把人,都視作對象加以算計和制造,以致物面臨著消逝,存在者整體縮小,天地萬物共同的原始自然基礎被破壞,不僅物而且人神的存在都趨于一種“不在家”狀態。[6]他在《荷爾德林與詩的本質》一文中,曾說“人在大地上詩意地棲居”,他認為人的肉體性存在注定了人歸屬于自然大地,人與自然萬物共生。因而在本質上講,人不是大地的征服者,而是大地的看護者,特別是海德格爾后期哲學面對人類工具理性膨脹之下現實的生存狀態,他指出人與世界是須臾難離的,人類詩意地棲居于大地的過程就是真理從遮蔽到解蔽的自行顯現過程。當代回族作家的文學創作恰是堅守大地、回望大地的文字書寫。
寧夏回族作家石舒清20世紀60年代出生與寧夏西海固海原縣,立足西海固這一積淀厚重的邊塞大地獨特而深遠的背景。與他相仿,八十年代出生的寧夏回族女作家馬金蓮的文學創作也始終關注著她幼年時生活過的扇子灣。他們用筆下的文字動情地歌唱廣闊的大地,在回望大地的儀式中力圖解構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重構人與自然唇齒共生的和諧關系。石舒清的短篇小說《清水里的刀子》通過細膩的筆觸,冷靜的思考人與身邊的動植物的關系,重新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老人馬子善在妻子亡故后,開始思考個人的“生來死去”為題,迫切地想知道自己什么時候死,能夠了無牽掛地走向長眠之地。兒子舉意的牛,在四十日來臨前突然不吃不喝,老人在這頭牛身上獲得了對生命的了悟。這種豐盈生動又略帶感傷的體驗,因為回望大地,所以蘊含著一種別樣的美。
少數民族作家文字中的蝴蝶與落葉、風聲與水聲、大地的脈動與韻律無都迸發出一種詩意的審美力量,大地以一種鮮活的生命形態而存在。作家們聚焦于大地的祛魅,力圖重塑人心對大地的深深依戀與親近。
參考文獻:
[1] 曾繁仁.中西對話中的中國生態美學[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7(2):33-38.
[2] 李長中.生態批評與民族文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100-102.
[3] 王諾.歐美生態文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7-9.
[4] 露絲·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煒,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8:48-49.
[5] 穆罕默德·高特卜.伊斯蘭藝術風格[M].劉一虹,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111-112.
[6] 趙奎英.詩人天職與生態倫理[J].文藝理論研究,2017: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