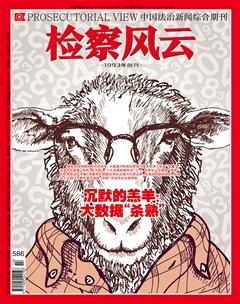運用法律完善 互聯(lián)網(wǎng)行業(yè)監(jiān)管
王樺宇 李想
大數(shù)據(jù)“殺熟”的出現(xiàn)有其深刻的市場原因和明顯的技術(shù)動機。
其一是算法技術(shù)的發(fā)展使得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擁有獲取消費者個人信息的可能性和廣泛度。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高速發(fā)展,大數(shù)據(jù)被廣泛應(yīng)用到生活的各個場景,使得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能夠收集用戶的海量信息,分析用戶的行為偏好、消費能力、對價格敏感度等,對用戶進行精準(zhǔn)定價。如果說算法技術(shù)的高速發(fā)展為大數(shù)據(jù)“殺熟”提供了客觀上的潛在可能,那么消費者自困于特定偏好的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效應(yīng)的存在,則為大數(shù)據(jù)應(yīng)用于“殺熟”創(chuàng)造了主觀上的便利可能。
其二是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和相關(guān)平臺受到利益驅(qū)動而產(chǎn)生獲取不當(dāng)利益的聯(lián)合需要。在較為傳統(tǒng)的市場環(huán)境模式下,經(jīng)營者為謀求競爭優(yōu)勢,獲得更大的利潤,往往會傾向于增強產(chǎn)品創(chuàng)新力度和提高服務(wù)質(zhì)量,如此,理性的市場主體和價格競爭能夠促進行業(yè)整體上向前發(fā)展。在大數(shù)據(jù)“殺熟”現(xiàn)象中,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受利益驅(qū)使,往往會利用用戶的使用習(xí)慣和對經(jīng)營者的信任,使其支付的價格超過其本來應(yīng)當(dāng)支付的價格。實施價格殺熟行為的市場主體為了占領(lǐng)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通過算法功能了解熟客的消費習(xí)慣而搶占市場支配地位,獲得不正當(dāng)競爭優(yōu)勢,也構(gòu)成一種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并損害其他經(jīng)營者的合法權(quán)益。同時,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的平臺利用使其在數(shù)據(jù)信息的獲取和支配方面占據(jù)優(yōu)勢,通過數(shù)據(jù)分析技術(shù),了解入駐商家的用戶的交易習(xí)慣和價格底線,也有可能不正當(dāng)?shù)孬@取市場份額,從而獲得超額的利潤。
其三是目前關(guān)于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保護和合理定價的法律法規(guī)還不夠健全和完備。從價格法上看,雖然可以將大數(shù)據(jù)“殺熟”的受害者定義為消費者,但是也很難將該行為納入《價格法》第14條第5項所規(guī)定的“價格歧視”行為,因為它針對的是“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務(wù),對具有同等交易條件的其他經(jīng)營者”的價格歧視行為。同樣《消費者權(quán)益保護法》第8條所規(guī)定的消費者知情權(quán)限于“購買、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務(wù)的真實情況”,包括價格、主要成分等,但似乎不包括經(jīng)營者的“差異化定價”。《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對違反商業(yè)道德的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提供了基本的評判標(biāo)準(zhǔn)并規(guī)定了相應(yīng)的行為類型,就個性化定價而言,用戶如果感到電商平臺區(qū)別定價的行為不公平,在市場競爭充分的條件下,就會轉(zhuǎn)向其他提供相似商品或服務(wù)的經(jīng)營者,使得實行個性化定價的電商平臺失去交易機會,單純的個性化定價行為尚不屬于違法的規(guī)制范疇。因此,大數(shù)據(jù)“殺熟”這個現(xiàn)象很難在現(xiàn)有的法律法規(guī)框架下得以很好地解決,法制監(jiān)管的疏漏更加容易放縱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大數(shù)據(jù)“殺熟”的行為。
表現(xiàn):大數(shù)據(jù)“殺熟”的價格濫用
大數(shù)據(jù)“殺熟”之所以引起了消費者的一致憤懣,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在信息不對稱環(huán)境中互聯(lián)網(wǎng)商家具有特別的優(yōu)勢地位。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作為商品及服務(wù)的提供者、消費者信息的獲取者具有雙重身份,讓它在消費者面前更加具有不同于以往傳統(tǒng)商家的比較優(yōu)勢。傳統(tǒng)商家雖然提供商品和服務(wù),在提供的過程中并不直接掌握消費的信息,盡管也可能出現(xiàn)“殺熟”的現(xiàn)象,但是只是依據(jù)其模糊記憶和對特定用戶的主觀判斷,并且往往以用戶個案的方式出現(xiàn),而在消費者口耳相傳的輿論監(jiān)督背景下具有高度的市場風(fēng)險。隨著大數(shù)據(jù)時代的到來,約束傳統(tǒng)商家的輿論防線開始潰散,消費者往往只對自己的消費行為進行認(rèn)知和評價,消費者之間的信息溝通變得更為分離,互聯(lián)網(wǎng)商家的數(shù)據(jù)優(yōu)勢地位使得他們會以更隱蔽的方式進行大數(shù)據(jù)“殺熟”的行為。
大數(shù)據(jù)“殺熟”中的價格濫用還表現(xiàn)為互聯(lián)網(wǎng)商家分別針對新客和熟客進行差異化的價格歧視。商家尤其是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在發(fā)展的初始階段尤其重視對客戶和市場的拓展,往往給予新客戶極大的優(yōu)惠甚至免費的商品和服務(wù)來培養(yǎng)其用戶習(xí)慣,并在后續(xù)消費過程中持續(xù)深化此種感受和認(rèn)知,讓客戶產(chǎn)生對特定商家和產(chǎn)品的相對依賴。隨著消費者開始對特定企業(yè)和產(chǎn)品產(chǎn)生依賴,其消費習(xí)慣開始受到過往消費經(jīng)驗和對商家在市場培育中建立的信任的影響,從而減少對其價格變化的關(guān)注,這就給了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極大的可乘之機。不同消費者的實際購買力和用戶黏性在新客和熟客階段往往是差異化的,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往往會在不同時機采取不同的定價方式,在確認(rèn)熟客的忠誠度后往往會采用相對更高的價格獲取不當(dāng)利潤。
大數(shù)據(jù)“殺熟”的價格濫用更體現(xiàn)在個別商家嚴(yán)重侵犯消費行為偏好隱私權(quán)的行為。在大數(shù)據(jù)利用方面,用戶消費畫像的實際情況是,客戶往往對自己是否被搜集了信息、被搜集了哪些信息、信息是否真實準(zhǔn)確并不非常清楚,算法分析模型常常被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作為商業(yè)秘密予以保護,客戶無法理解定價的機制和相關(guān)原理,信息的透明度不夠?qū)е录幢憧蛻舯磺謾?quán)也不自知,所以事后救濟也就顯得非常無力。就算公司提供客戶訪問被搜集數(shù)據(jù)的權(quán)利,客戶也無法實際了解這些數(shù)據(jù)的用途,更不會知曉如何控制這些數(shù)據(jù)的風(fēng)險。因而,“必要搜集”和“數(shù)據(jù)透明”原則顯得格外重要,其讓客戶理解商業(yè)運作及決策做出的方式,并給予客戶退出信息收集和使用的權(quán)利,有助于在線商業(yè)的建立發(fā)展和維護客戶的信任。
對策:大數(shù)據(jù)“殺熟”的法律規(guī)制
對大數(shù)據(jù)“殺熟”進行法律規(guī)制,首先要加大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的行為監(jiān)管和價格監(jiān)督。既然“殺熟”是大數(shù)據(jù)利用中的問題,屬于不合商業(yè)倫理的數(shù)據(jù)利用,因而個人信息保護立法重點關(guān)注,將這樣的行為定性為個人信息的不當(dāng)使用,并對這種不當(dāng)使用行為予以規(guī)范和約束。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在個人信息使用者告知義務(wù)中增加算法或算法用途說明,滿足消費者對個人信息使用及其可能的差異化定價的知情權(quán)。同時,對于利用大數(shù)據(jù)算法實行差異化定價的行為,一旦構(gòu)成《消費者權(quán)益保護法》規(guī)定的“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條件”,可視為消費者公平交易權(quán)被侵害,市場監(jiān)管機關(guān)可以加大電子商務(wù)企業(yè)價格監(jiān)督,對有關(guān)經(jīng)營者實施必要的行政處罰,打擊這種大數(shù)據(jù)技術(shù)的濫用行為。隨著一些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市場份額增大,面對政府監(jiān)管的博弈能力愈加強大,需要政府監(jiān)管這一把最重要的利劍切實進行管理,加強執(zhí)法力度,重點對大數(shù)據(jù)企業(yè)進行監(jiān)控,加大電子商務(wù)企業(yè)價格監(jiān)督。
第二要加強對消費數(shù)據(jù)隱私權(quán)和相關(guān)權(quán)益的保護。現(xiàn)有的商家尤其是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往往基于其提供商品和服務(wù)的優(yōu)勢地位,肆意侵犯消費者的隱私權(quán),甚至?xí)砸环N“看似”合法的方式強制獲取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如強制消費者必須同意APP收集消費者部分權(quán)限和強制訪問消費者手機的相關(guān)內(nèi)容,才可以使用企業(yè)提供的服務(wù)。因此,在我國只有隱私權(quán)保護的一般性規(guī)定是遠遠不夠的,還應(yīng)該制定專門的網(wǎng)絡(luò)隱私權(quán)法律來保護公民的網(wǎng)絡(luò)隱私權(quán)。其中,應(yīng)該特別規(guī)定出公民網(wǎng)絡(luò)隱私權(quán)的內(nèi)容,主要應(yīng)包括知悉權(quán)、選擇權(quán)、控制權(quán)、安全請求權(quán)等具體的權(quán)利性規(guī)定,明確商家對消費者信息數(shù)據(jù)獲取應(yīng)基于最小化原則,并規(guī)定侵害網(wǎng)絡(luò)隱私權(quán)行為的種類以及侵權(quán)行為的認(rèn)定,規(guī)定隱私權(quán)侵權(quán)責(zé)任的承擔(dān)以及各種補救措施。
第三是要明確不正當(dāng)合謀者影響競爭秩序的責(zé)任承擔(dān)問題。對于大數(shù)據(jù)“殺熟”等價格歧視行為,依據(jù)現(xiàn)有競爭法律法規(guī),除非企業(yè)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且區(qū)別定價沒有正當(dāng)理由,否則難以對相關(guān)企業(yè)進行相應(yīng)的處罰。但是,有關(guān)部門需要研究沒有正當(dāng)理由的歧視定價行為,可以明確不正當(dāng)合謀者影響競爭秩序的責(zé)任承擔(dān)問題。2015年,Topkins被美國司法部指控實施了“合謀修改在線銷售商品價格”的行為,違反了《謝爾曼法》關(guān)于定價的規(guī)定,2015年4月30日,Topkins與美國司法部達成認(rèn)罪協(xié)議。Topkins撰寫的定價算法幫助具有競爭關(guān)系的經(jīng)營者之間協(xié)調(diào)價格,這可以幫助我們明確不正當(dāng)合謀者影響競爭秩序的責(zé)任承擔(dān)。可以在未來競爭監(jiān)督和價格執(zhí)法過程中,對于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或平臺通過特定定價算法自動交換價格信息而協(xié)調(diào)價格變化的行為,補充和細化現(xiàn)有競爭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并予以嚴(yán)厲打擊。
(鳴謝:上海交通大學(xué)凱原法學(xué)院金耀輝教授、侯利陽教授對本策劃的支持)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