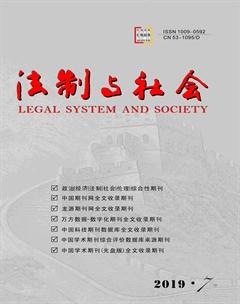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與假冒注冊商標罪司法界限問題研究
摘 要 涉外定牌加工行為的定性是個非常復雜的社會經濟問題,關于涉外定牌加工行為是否構成侵權,經過多年的爭論與研討,司法實踐以及理論界占主流觀點已形成,因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與涉外定牌加工行為之間的高度相似性,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與涉外定牌加工易發生混淆,特別是這種侵權行為涉嫌犯罪時,如何劃分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與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司法界限就成了問題。本文從涉外定牌加工行為出發,論證如何厘清涉外定牌加工行為與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并結合刑事司法實踐,提出具體如何界定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與假冒注冊商標罪,以期更好地維護民事主體的正當合法權益,維護健康有序的市場秩序。
關鍵詞 涉外定牌加工 對外貿易商標侵權 假冒注冊商標罪 司法界限
作者簡介:林靈芝,溫州市甌海區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部副主任,研究方向:經濟法。
中圖分類號:D92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7.153
改革開發至今,對外加工貿易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卓著貢獻,涉外定牌加工屬于對外加工貿易中的重要分類,我國素有“世界制造工廠”的別稱,曾以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及物資成本,吸引境外公司企業在我國境內進行投資或者委托我國境內企業生產,是涉外定牌加工大國。但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一些貌似涉外定牌加工行為但實為民事侵權,乃至構成犯罪的行為,混雜在涉外定牌加工隊伍之中難以甄別,進而導致涉外定牌加工、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假冒注冊商標罪三者之間的混同,擾亂了我國的對外貿易秩序,要明確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與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司法界限,不可避免地要界定涉外定牌加工行為。
一、涉外貼牌加工行為中的“侵權”與對外貿易商標“侵權”問題
產品所貼附的商標只要與我國境內已注冊商標有沖突,即使獲得境外企業合法授權或委托也會產生商標侵權的可能,這個問題非常復雜,困擾我國理論與實務界幾十年,也左右著我國境內的定牌加工企業生存環境。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浦江亞環鎖業有限公司與萊斯防盜產品國際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一案作出再審判決 ,最高院在該判決中表明了認定涉外定牌加工行為不構成侵權的立場,對之后的涉外定牌加工行為的定性具有重大影響,涉外定牌加工行為將不被判定為侵權。但是無可避免的需要討論另一種可能,那些不具有合法授權的或者聲稱涉外定牌加工的行為實為侵權甚至犯罪的行為要如何處理,他們披著“涉外定牌加工”外衣極具迷惑性,要辨別這些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就要判定哪些行為構成“涉外定牌加工”。按通說的觀點,構成涉外定牌加工主要條件有:
1.境外定作方應在境外法域享有相關的商標權利。
2.該商標在中國為另一民事主體所享有。
3.涉案產品所使用的商標標識,應與該境外商標標識,應與該境外商標標識完全一致。
4.涉案產品應屬于該境外商標的核定使用商品類別。
5.涉案產品應全部返銷到境外。
6.境外收貨人應為境外的商標權利人或經其合法授權或指定的第三方。
以上條件應該全部滿足才構成涉外定牌加工,任一條件不滿足則不構成,涉外定牌加工的范圍不能肆意擴大,否則容易滋生大量打著涉外定牌加工名頭實為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涉外定牌加工成為這類侵權行為庇護所的可能性極大,這顯然違背相關法律的本旨與原則,前文中也有述及這種打著涉外定牌加工名義的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那究竟什么是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基于以上對涉外定牌加工行為的分析,可以就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下個定義,即不符合涉外定牌加工行為條件的,且屬于《商標法》意義上的使用,全部符合相同的商品或服務、商標相同或近似、存在混淆的可能性等三條件,不存在抗辯事由 ,并包含“涉外”因素的對外加工貿易過程中貼附已被注冊商標行為。但因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本身也有涉外因素,且有涉外定牌加工行為的偽裝,在進行界定的過程中極易與涉外定牌加工行為混淆,甚至有可能借用涉外定牌加工的外衣規避法律,進而可能逃脫法律的制裁,因此明確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與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司法界限意義深遠。
二、對外貿易侵權行為與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司法界限
假冒注冊商標罪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另與該罪名界定相關的司法解釋有《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若干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等,該罪的客觀違法要件為行為人未經他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他人已經注冊的商標相同的商標,且情節嚴重。《意見》中列明哪些行為可被認定為“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依據《解釋》第八條第二款之規定,明確了刑法上“使用”的定義。但以上法條及解釋明確的是不含涉外因素的商標侵權行為因情節嚴重符合刑法構成要件的認定及處理,而對于含有“涉外”因素的對外貿易中的侵權行為法律及司法解釋并沒有明確。在一些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省,如浙江省出臺了《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浙江省公安廳關于辦理涉外定牌加工等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有關法律適用問題的會議紀要》(以下簡稱《浙江省會議紀要》)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部分說明:“合法授權范圍內的涉外定牌加工……行為人是受境外注冊商標權利人的委托生產使用該注冊商標的商品,沒有假冒注冊商標的主觀故意,也沒有假冒注冊商標的行為,……不宜以假冒注冊商標犯罪論處。”
《浙江省會議紀要》相當于是對涉外定牌加工司法實踐結果、《復函》精神及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38號再審判決結果的重申,涉外定牌加工行為不構成普通民事侵權,當然不可能構成犯罪,這也說明了只要剝離涉外定牌加工行為,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可按普通國內法律法規進行處理是非常明晰的。現以案例來對此進行說明。
案例:2016年某月以來,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浙江某市某區新河路幾處房屋內雇傭他人生產開關、插座等電器。期間,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未經注冊商標所有權人許可,在生產的電器等產品上貼附注冊商標標識Schneider、hager、MK、CLIPSAL。2017年某月,公安機關在上述地點現場查獲標注有商標標識 Schneider牌的開關插座成品、面框、面板、盒貼;hager牌的開關插座成品; MK牌的開關插座成品、模具、中板、盒貼;CLIPSAL牌底座、模具。經鑒定,被查獲的開關插座成品價值人民幣14余萬元,其余物品價值無法鑒定。
案件處理觀點1認為犯罪嫌疑人余某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浙江省會議紀要》雖然指出合法授權的涉外定牌加工不構成犯罪。未明確指未經合法授權的涉外定牌加工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而應該對此類行為加以區分。本案中,涉案產品由于系國外制式,相應正品沒有在境內銷售。根據上述紀要精神,涉案產品并未在境內市場發揮識別商品來源的功能,境內相關公眾對該商品來源不會產生混淆或誤認,境內商標注冊權人在境內的市場份額和競爭地位未受到影響,其相關權利并未受到實際侵害。本案中,涉案產品在境內不可能正常進行銷售,只不過是通過類似義烏市場這樣的出口渠道最終流入境外,而不會影響國內的注冊商標權利人。故客觀方面來看,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不符合構罪標準。
觀點2認為犯罪嫌疑人余某某的行為構成犯罪,會議紀要明確只有合法授權的涉外定牌加工才不認為是犯罪,本案中無任何證據證實存在合法授權的事實。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供述其在生產假冒的開關時并未授受任何人的委托,系其主動到義烏市場上尋找買家,體現了其具有假冒注冊商標的主觀故意。余某某具有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的故意在先,后期訂單只不過系其銷售渠道的一種方式。涉案產品雖系國外制式,由于被侵害單位在中國境內有生產、銷售其它制式的產品,雖然銷售渠道不同,但名稱相同,符合《意見》關于“同一種商品”的認定情形。另,雖涉案的國外制式產品在國內無法使用,但這種涉案產品事實上在義烏等市場上進行銷售。因此,余某某的行為在客觀上侵害了境內注冊商標權利人的合法權利,符合構罪標準。
三、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與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司法界限認定程序
結合前文所述,筆者認為可構建界定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與假冒注冊商標罪司法界限的導圖如下:
導圖說明:首先要區分對外加工貿易中貼附已在我國境內被注冊商標行為與涉外定牌加工行為;其次要判斷對外加工貿易中貼附已在我國境內被注冊商標行為是否構成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再次要判斷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是否符合假冒注冊商標罪的犯罪構成要件,構成則承擔刑事責任,否則承擔民事責任或者行政責任。
結合導圖,分析案例:案例中,筆者部分同意觀點2,首先區分余某某生產開關、插座等電器的行為是否屬于“涉外定牌加工”,如余某某生產開關、插座等電器成立“涉外定牌加工”行為,則不構成侵權,自然也不可能成立犯罪,但在本案中,余某某生產開關、插座等電器的行為顯然不成立“涉外定牌加工”,不符合成立“涉外定牌加工”的最基本要件,即“境外定作方應在境外法域享有相關的商標權利”,本案中余某某的行為模式是先非法進行多種注冊商標標識產品生產后再尋覓買家,無任何證據顯示余某某接受境外商標權利人或被許可人的定做委托,根據余某某的供述其未得到任何境外商標權利人的委托,涉案產品雖系國外制式,無法得出涉案產品一定出口至境外的結論,且余某某在國內義烏小商品市場有銷售本案所涉開關、插座等電器等行為,更遑論其他判定 “涉外定牌加工”行為成立的《商標法》意義上的 “使用”“返銷”等條件,因此余某某生產開關、插座等電器的行為不成立“涉外定牌加工”行為;其次余某某在生產開關、插座等電器上使用與多種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使公眾對該商品的來源產生混淆,是非常典型的對外貿易商標侵權行為,依據《解釋》第八條第二款之規定,余某某未經國內商標注冊權利人許可在這些電器上使用多種注冊商標標識的行為,符合“使用”的定義,依據《意見》第5條之規定,余某某所生產的開關、插座等電器與這些國內注冊商標權利人生產、銷售的電器,可以認定為“同一種商品”,因此本案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未經國內多家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多種與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且在國內義烏小商品市場上尋找買家進行銷售,情節嚴重,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
注釋:
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38號再審判決書。
俞則剛.亂花漸欲迷人眼——再論“涉外定牌加工”行為的構成要件.知產力公眾號.
喬平.商標侵權的認定和抗辯.《知產力清華大講堂——商標訴訟的現狀與趨勢》演講.
參考文獻:
[1]張偉君.《商標法》關于“商標的使用”定義條款由來、含義及其評價[J].中國知識產權,2016(5).
[2]朱冬.商標侵權中銷售商品行為的定性[J].法律科學,2013(4).
[3]劉維.商標權的救濟基礎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